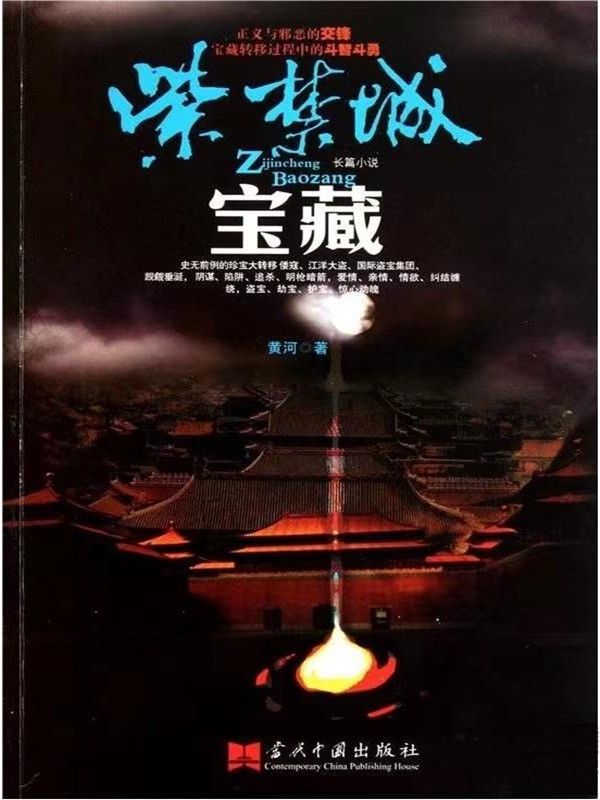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十二、起疑心鷹犬要拿人 細查訪警官尋蛛絲
這日上午,茂源錢莊掌櫃的龔長壽正坐櫃台後清理帳目,門口一暗,螳螂張帶著兩個隨從大模大樣搖了進來。龔長壽見是這瘟神,惹不起,躲不得,隻得笑臉相迎:“哈,是張隊長呀!今兒是啥黃道吉日,爺咋有空來這歇歇腿兒?嘿嘿!坐,裏頭客廳看茶!”
螳螂張今兒好像很不開心,要不就是成心找岔兒的,臉拉得老長,東瞧西望,對龔長壽的招呼不理不張。龔長壽京城裏混了大半輩子,官場商場黑道白道,啥沒見過?兩眼一瞄,就知這瘟神今兒來頭不善,心裏先裝了個勢兒,卻又裝懵懂,哈哈著小心將螳螂張等延進後院客廳。
落坐後,老媽子捧上茶來。龔長壽試探著道:“張隊長,這陣兒又忙啥哩?”
螳螂張托著茶盞兒,淺淺呷了口,陰著臉冷冷道:“二爺,咱爺兒倆老相識了是不?張某我夠朋友,你龔掌櫃龔二爺可不能不夠意思!忙啥?不知曉是不?你幹的好事呀!哼,是真不知還是裝作不知,拿咱爺們當猴耍?”
龔長壽:“這……隊長,這是從何說起?從何說起?”
螳螂張二郎腿一翹,冷哼一聲道:“實話說吧,張某我這趟是找你要人來了!”
龔長壽:“誰?不知張隊長要見誰?”
螳螂張:“馬家田!”
龔長壽一怔!隨即麵皮一鬆,嗬嗬笑:“原來是為龔某內侄子那事兒呀,嗬嗬!承蒙張爺你還掛在心上!隻怪他沒那福份兒,無緣到你手下做事,追隨張爺你左右了!唔,不是給爺你回過話了嗎,他……”
螳螂張不耐煩地打斷龔長壽的哆嗦道:“龔掌櫃的,我說你就別再逼細嗓兒唱假戲了!別以為有曹公公撐著,也別仗著有殷太太和殷參事這道鎮小鬼的符兒,就把咱這幫吃公差飯的看扁了!張某端啥飯碗,辦啥事兒,二爺你也別為難本人,幹幹脆脆把那姓馬的小子交出來就一好百好,咱爺們還是好兄弟,不然,哼!”
龔長壽:“內侄家有變故,早匆匆趕回東北去了,上次張爺來我已回過了呀!聽張爺意思,好像賤內侄闖了啥禍兒,龔某我把他藏起來了似的。俗話說,家有家規,國有國法,若真是這樣,張隊長,我這錢莊內外你隻管兜底兒翻找就是了!曹公公是龔某衣食主兒,恩重如山;殷參事本人雖無緣攀附,殷太太是小店顧主,到是認得的。隊長啥人物?手裏攥著槍把兒,身後頂著警局的牌兒,在這老京城裏跺跺腳地皮也要抖三抖呢!自是不把這些人放眼裏。若是曹公公、殷太太有啥得罪隊長的地方,趕明兒龔某瞅空走一趟,或捎個話兒過去,讓他們趁早給隊長你陪個小心就是。隊長,你看這樣行不?”
這話不軟不硬,綿裏藏針。把螳螂張噎得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怔了怔,惱羞成怒地將肚裏貨色兜底兒端了出來:“回了?哼!頭前天橋鬧事就有他的份兒呢!那可是張某親眼所見!龔二爺龔掌櫃的,實話告訴你吧,那小子不僅是禁宮竊案疑犯,前些日子的牛街血案、八寶胡同謀刺案,近日的石頭胡同和天橋擾亂治安案都同他有關連哩!這天大的案子,莫說是你,就是殷參事、曹公公恐怕都遮不住包不了吧?嘿嘿!你若識相,幹幹脆脆指個道兒,說句話兒,將那小子落腳之地在張某耳邊吹吹也就罷了。不然,嘿嘿,到時就莫怪我這老相好的不照顧你麵子了!”
龔長壽仍是不軟不硬地:“嗬,看來內侄惹下的亂子還真不少呢!照你這麼說那笨小子豈不成了飛簷走壁,千萬軍中取人首級如入無人之境的世外高人了?嗬嗬!他若真有那本事我這當叔的睡著都要笑醒了!再者,隊長既親眼見了,為何不當場拿下?隊長,該說的龔某都說了,其它就恕龔某愛莫能助了!”
螳螂張麵上變色,呼地立起來,冷哼一聲,抬腿就走。龔長壽卻哈哈著上前拉了:“也,咋啦?咱爺們是誰跟誰?給你鬥嘴玩兒呢,真就叫上勁兒啦?哈哈!真個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呀,哈哈!”扯了螳螂張坐下。
他這一會兒黑臉一全兒紅臉的,螳螂張就有些懵,不知他玩的啥把戲。
龔長壽打著哈哈朝螳螂張拱了拱手,樂嗬嗬道:“這就對了!有道是梁山弟兄,不打不親嘛!嗬嗬!剛才龔某言語多有得罪之處,還望張爺多多擔戴著點兒!張爺和兩位弟兄既然辛苦一趟,按曹公公的規矩,茶水錢照例是不能少的。來來來,捧上來呀!”
就有夥計隨聲捧了個托盤進來,盤裏端端地碼了三圈三十塊大洋。螳螂張見了繃緊的麵皮就化了凍,卻作態推拒道:“嗬,又來這套?使不得,使不得!”龔長壽抓起用紅低封好的大洋,一古腦塞螳螂張兜裏,嘿嘿著衝他的兩個隨從說二位兄弟的都在這兒了,他是你們的主子,就由他賞給二位吧。又衝螳螂張道,“龔某替曹公公守著這份產業,自是處處以曹公公的章程為綱繩。而今適逢亂世,立門開店處處難啦!全靠張隊長這樣的熱心朋友多方照看著,不圖發利,隻要能逢凶化吉,免禍消災就阿彌陀佛了!嗬嗬!”
螳螂張不陰不陽笑笑:“好說,好說……”
當日上午,石川交通團內套院一廂房裏,著便裝的歐陽遠崗坐廂房客廳,正同殷太太密談著什麼。
殷太太:“……事情就是這樣。茂源錢莊是曹公公的,曹公公是清庭大太監,不僅有好幾處錢莊、當鋪、古玩店,還有幾處房宅地產,同軍界政界各派係甚至黑道上人物都有瓜葛,是個財大氣粗,手眼通天的人物。這一節,想必歐陽警官不會不知道吧?”見歐陽點了點頭,又說,“前些日子龔長壽來找我,一是要我替他侄子弄個有前程的事兒,二是要向我討張我那當家的親筆推薦條兒,又好謀前程,又好當護身符兒呢!哼,他以為我那當家的是啥人物?兩錢鹽就放鹹了的呀?我自是沒去驚動我那當家的,不過礙著曹公公的麵子,也是念他平日會作人,我便傳了個話兒出去,讓你們局子裏照看些兒,龔長壽說螳螂張故意找他岔兒嘛!嗯,莫非那姓馬的小子真做下啥案子了?”
歐陽喉嚨裏悶悶應了聲,沉吟有頃,道:“眼下還沒弄清,不好說嗬。”又問,“這麼說,你沒見過那馬姓小子?”
殷太太:“一個關外來的鄉下佬,見他幹啥!”
歐陽遠崗忽然旁枝橫生,問:“石川團鬧刺客那晚,太太是幾時離開的?青龍教官在團裏嗎?”
殷太太:“九點多吧……那晚青龍一郎在呀,亮燈時上了樓一直就沒下來呢!咋的?審問來了?咯!”
歐陽站起來恭敬地說:“豈敢!豈敢!太太見諒,在下純屬職業習慣,例行公事,例行公事而已!”
見他那恭敬樣兒,殷太太開心地笑了:“何必如此多禮。咯咯!坐,坐呀!”
二人是在去年初夏的一次酒會上認識的,歐陽雖不是副官、秘書一類角色,在局裏裏頂了個副隊長的職務,不知咋唐仁和卻總把他當秘書、副官使喚,時時把他招在身邊。唐仁和要同太太去赴酒會,自然也沒忘把他喚上。那晚,殷太太是酒會上頂活躍的人兒。她隨丈夫去滬上赴任,聽不慣上海人鴨子樣呷呷呷的腔調兒,戀著京城的燈紅酒綠,就獨自跑了回來,趁著去而複返的新鮮勁和丈夫新得美差的喜興兒,大出風頭。端了酒杯這桌竄那桌,唧唧噥噥,咯咯吱吱。晃到歐陽他們落坐的酒桌旁,慧眼識珠,一下就盯住了英俊的歐陽遠崗。唐太太見她瞅著歐陽眼都發直了,就玩笑說咋啦?一見鐘情了?嘻!真要有意,念著姐妹交情,就白送你啦!嘻嘻!舞曲一起,大人先生、太太小姐們紛紛進入舞池。歐陽一直坐酒桌旁冷眼旁觀,他不是不會跳舞,甚至跳得很好,可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哪想殷太太同那些有頭有臉、大腹便便的老先生們周旋了會兒後卻朝他走來,不由分說挽了他步入舞池。此後,殷太太就把他當了自己的最佳舞伴。凡有舞會,總邀他陪著。隻是歐陽公務繁忙,又怕招來風言風語,有時便借故推托,因而讓她時常遺憾就是了。
歐陽重新坐下後,殷太太含笑將他瞅了,妖媚地扭扭腰肢嬌聲道:“哼!就知道公事呀!案子呀!多沒情調!我不管,今兒當姐的隻把你當小弟了,咯!”說著,腦袋那麼一偏,一對亮閃閃耳墜子就一蕩一蕩,一雙亮閃閃眼仁兒就定在了他臉上。
這一打岔,歐陽一時找不到話題兒,讓她這一瞅,臉上不禁泛起紅來。殷太太見了,愈發地心旌搖蕩。歎了口氣,幽幽怨怨說:“我那當家的一去不回,將我這苦命人兒獨自拋閃在這京城,冷冷清清,說不盡的寂寞嗬……小弟,你也是個沒心沒肺的,咋不常來陪你苦命的姐姐說說話兒?”說著,一隻玉手悄悄偷渡過來,抓住了歐陽的手。
一瞬間的失態後,歐陽已強自攝住了心神。就輕輕抽出手來,正色說:“歐陽公務繁忙,沒空陪太太消遣,實在對不起!此來隻為前些日子貴團謀刺未遂一案……”
殷太太柳眉一挑,不悅地打斷他道:“公務公務,又是公務!公務來找我幹啥?你以為這石川團的事兒我啥都清楚嗎?哼,告訴你也不妨,這兒當家的除了石川先生,就是八姨太!近來石川先生不在,人家可是入主正宮了呢!”
歐陽饒有興趣地:“嗬,是嗎?”
殷太太酸酸地:“不是咋的?人家又年輕又漂亮,男人又是了不得的人物,統領著千軍萬馬,又有青龍那家夥幫扶著,嘻嘻……最近我還見青龍送了對玉佩給她呢!”
歐陽:“玉佩?”
殷太太:“是呀,那可是上等貨!我見過的珍玩珠寶多啦,這樣好的玉器可是從沒見過,八成是皇宮裏流出來的!有情的男人,為了心愛的女人是最肯花錢的。誰像你,沒心沒肺的!”
打辛亥年後,皇帝廢了,禁宮裏就亂了套兒。樹倒猢猻散,高官顯爵,大小太監,宮娥彩女,趁機大撈一把,明拿暗竊,巧取豪奪,宮裏珍寶流失幾多,實在難以計數。這些古玩珍寶,總有一些流入市場。因此,若說青龍新得了宮裏流出來的玉佩什麼的,在當時也實在不足為奇。是故,歐陽見她越說越沒了譜兒,便立起來彬彬有禮地告辭。
恰在這時,室外響起了八姨太脆脆的嚷嚷聲:“好呀,殷太太!貓起來說啥好話兒呀?一說半天,將咱姐妹拋閃得,咯咯!這會兒我可要老著臉兒棒打鴛鴦了喲,咯咯!”
歐陽遠崗臉上騰地一紅,走道上側身讓過迎著他走來的八姨太,八姨太朝他哈腰行了個禮兒,歐陽也朝她點頭笑笑,便逃似的匆匆去了。
八姨太立廂房門口,注目歐陽背影。殷太太迎出來,八姨太朝歐陽背影努努嘴,笑道:“挺俊氣嘛!殷太太,你眼光不錯呀!”
殷太太:“沒影的事兒,瞎嚼舌根兒,看我饒不了你!嘻嘻!”
八姨太抬腿進屋,坐下說:“警局裏作事的吧?一表人才,又挺幹練的,可惜了!”
殷太太:“明知故問!以前酒會、舞廳裏你沒見過咋的?拿你大姐逗耍子呀?”又故作輕蔑的樣子,撇了撇嘴說,“哼,小小個警官兒,不念他是同鄉,舞又跳得好,誰理他呀!”
八姨太咂咂嘴,作態說:“啥時又成了同鄉了?嘖嘖,虧你舍得貶呢,整個一個糖哥兒,含嘴裏都怕化了的。你不要,我可要搶了!咯咯!真當誰沒眼仁兒呀?隻怕黃浦灘上那主兒知道了打破醋壇子呢!”
殷太太就佯作羞惱,作勢撲上去問罪。八姨太趕緊討饒。咯咯吱吱笑鬧了會兒,八姨太就說好了好了,談正事兒吧。便問殷太太那歐陽可是衝著團裏那樁謀刺案來的。殷太太弦外有音地酸溜溜說:“誰知他肚裏賣的啥藥,東拉西扯,一會兒是那姓馬的,一會兒是青龍那事兒。唉,人家又年輕,又俊俏,有的是人疼呀,哪是我這半老婆子比得的!”
八姨太臉一拉:“放肆!你可得記住你的身份!”
殷太太趕忙坐直了,垂頭應:“是!”
八姨太麵色慢慢緩和過來,緩緩道:“也不是我拿腔作勢,我是給你提個醒兒,以後你同他打交道可得當心!言多必有失,紀律無情嗬!咱姐妹是姐妹,正事是正事兒,嗬?”
殷太太點頭稱是。八姨太緩緩立起,麵色凝重地接著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眼下這京城正是風雨飄搖,大變在即嗬,你我重任在肩,萬不可稍有疏忽呢!在我大日本帝國地策動、促成下,形成了當今中國三強聯手,舉師討赤的大好局麵。今張、吳、閻大軍步步進逼,馮玉祥隻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呢!數日前,馮玉祥收集國民軍主力,在灤州、通州、黃村一帶擺下了同三強決一死戰之勢。眼下雙方激戰正酣,但我料馮玉祥難敵三強聯手,不出三五日定然敗北!那馮玉祥深受蘇俄影響,為北方赤色勢力的代表,帝國豈能容他!隻是趕走馮玉祥,三強進京後,段祺瑞政府必然崩潰,張、吳、閻為爭權奪利勢必又將吵起來。怎樣收拾這一局麵,保護我大日本帝國在華利益,擴充親日勢力,又將大費周旋了呢……”沉吟有頃,話鋒一轉,接著道,“殷太太,你在這京城裏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今又負有重大使命,那個歐陽遠崗,我看你還是少接觸的好,莫因小失大嗬!”
殷太太又點頭稱是。八姨太這才細細問起歐陽都說了些什麼,問了些什麼。殷太太一一如實說了。八姨太聽了,兩道柳眉糾纏到一塊兒,緩緩踱到窗前,瞅了庭院中太湖石旁那叢豔豔的花兒,心忖道:這麼說警局方麵眼下就已亂了套兒不成?段執政早已暗允不多插手本團諸事,那樁公案,亦讓我團自行了結,這歐陽遠崗卻又是奉誰的命令而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