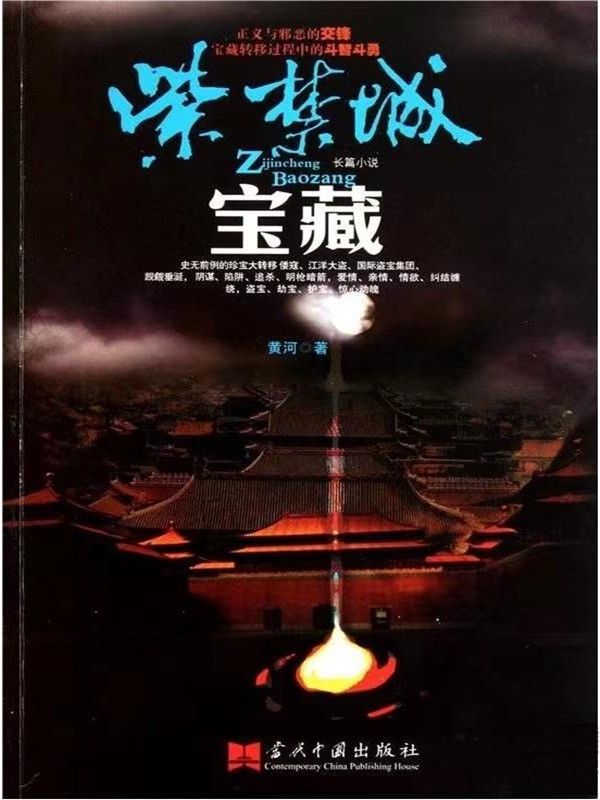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六、逢亂世自有亂中作樂人 愛寶藏終因寶藏丟小命
初夜時分,京城某豪華舞廳內,雲集了京城各界名流和一群珠光寶氣的太太、夫人、交際花。不管世道怎麼亂戰爭怎麼打,樂兒是照舊要取的。
舞會還沒開始,打扮得光光鮮鮮的男男女女呷著水酒,或坐或立,或在酒桌間人群裏遊走竄動,打著招呼打著哈哈營營嗡嗡交頭接耳寒喧著閑聊著調笑著,說著許多有趣的話兒。
一張酒桌邊,一個四十多歲的禿腦門胖子似要顯示他的消息靈通,沒遮沒攔地咋唬說:諸位,可靠消息,聽說美、英撮合直奉聯手對付馮玉祥革命的事兒近日弄成了呢!山西那個閻王已動作起來了,看來戰火馬上就要燒到咱們的門口了呢!
就有一片驚驚乍乍的聲音。
卻有一條喉嚨說,這事兒呀,老兄,可不是啥新聞了!說來姓馮的也太傾向赤色了,難怪人家美、英朋友都看不過去,沒見咱這京城裏讓共黨鬧得像啥話兒?
就有個女人的聲音接了,說你們這些男人呀,湊一塊兒不是政治就是軍事,一個個都啥人物似的!唉,真沒勁兒,這舞會都成政治軍事會了,還咋尋樂兒?
又有個男人打著哈哈說,密司李,親愛的,我看你呀還是趕緊收拾細軟早早躲黃浦灘去吧!不然槍炮一響驚得你花容失色丟了芳魂兒可咋辦?哈哈!
警察局長唐仁和的二房夫人唐太太是這兒的常客。局長大人多忙事,唐太太又年輕又時髦,咋耐得住寂寞?到舞廳和各種聚會消遣就自然成了她樂此不疲的喜好。這會兒唐太太正坐在舞廳一隅,同殷太太、八姨太有一句沒一句地拉著話兒。隻是今日她身旁少了個挺挺拔拔的青年男子,那是她表弟陸警官。以往這種場合總是她表弟陪她來的,今日表弟沒來,她總覺得少了點什麼,顯得有些心不在焉。
樂曲終於響了起來,殷太太、八姨太先後雙雙對對進入舞池。唐太太突然站起來,帶著侍立一旁的貼身丫頭燕兒匆匆走出舞廳。
旁邊,一個穿西裝、打蝴蝶結的青年男子呷著紅葡萄酒,斜眼盯著俏麗的唐太太滾圓的屁股一掀一掀出門而去,放下酒杯,站起來往舞池人多處鑽了鑽跟出門去。
舞池裏,八姨太忽然撇開她的舞伴,步出舞池,向靠牆的一張酒桌走去,原來坐那兒的一個不引人注目的男人就立起來,悄沒聲地跟了出去。
京城牛街,燈光昏暗,行人不多。逢亂世,人膽小,大大小小的商號都已關門。酒館飯店倒還熱鬧,街邊的一些小攤小販也正是做生意的時候,要謀生計,也就顧不了那許多。
“嗨!拐拐上,注意倒!”隨著一聲吆喝,一輛黃包車如飛而來。車上坐著唐太太和她的貼身丫頭燕兒。唐太太顯然有些興奮,不停地東張西望,不停地同燕兒說些什麼。燕兒卻顯得有些茫然,手上抱著一大堆大大小小的食品包兒、糖果盒兒。
黃包車在一巷口停下,唐太太跳下車來,打發走車夫,向燕兒吩咐了幾句,接過食品包兒、糖果盒兒獨自走進巷內。
唐太太在巷內一小院門前站下來,巷頭巷尾掃一眼,叩門輕喚:“表弟!表弟……”
院門吱呀開了個縫兒,身著便裝的陸警官露半邊身子探頭一看,驚喜地:“是你,哈!虧你還想著咱!”
這是一座獨家小院,院內有花有草有樹木,昏暗中也不知是啥名目。房子倒還寬敞,一正一偏兩排屋子,斜著那排屋子一律落了鎖,正屋大門開著,側屋裏有燈光,顯見著陸警官是住正屋了。
二人進了屋,穿過客廳,直奔陸警官住著的側屋。唐太太一坐下來,就甩著手帕兒直嚷:“呀,累死我啦!貓攆著的小鼠兒樣一溜煙顛來,又怕遇著啥人,火急急的,心顫顫的!”
陸警官嘻著臉湊上去:“咋到現在才想起來看看?唉,悶死我啦!真不知姐夫和你玩的啥把戲!瞧,這是人呆的地方嗎?關禁閉似的!這麼躲躲藏藏不是更讓人懷疑嗎?”
唐太太:“你姐夫還一再叮囑我別來看你呢,說是怕暴露,他那邊一直是說你正在關禁閉反省呢!”
陸警官:“他是怕咱倆親近,怕咱倆那個……那個,嘻嘻!”
唐太太拍開他探身上的手:“規矩點,都啥時候了還不老實!你不是急著要出來嗎?好歹總算離開看守所了呀!先在這兒委屈陣兒吧,你姐夫說外頭輿論還很大,警備司令部姓劉的還在抓著禁宮那事兒作文章,要裁你個勾結匪人,盜竊珍寶,眼下正找你把柄呢!放心,有你姐夫在,有我在,過了這風頭兒怕還回不去咋的!”
陸警官:“可是……要讓我在這鬼地方貓到啥年月才算完?要不,我先到天津衛那邊玩一圈去……”
唐太太:“哪行,劉司令正好問你個戴罪潛逃呢!住這兒,萬一上頭較起真來,你還可立馬回看守所去,你姐夫那兒也就好搪塞了。隻要你姐夫不倒誰還能把你咋樣?你知道姓劉的同你姐夫是冤家對頭,他弄你是表麵文章,抓住把柄把你姐夫搞垮才是真的呢!”
陸警官嘻皮笑臉攀住表姐雙肩,在椅子上掛了半邊屁股,拿指尖兒輕弄著她後脛窩兒,嘟著嘴道:“這麼說我是在替姐夫受洋罪了嗬,那你可得好好慰勞小弟一番才對,嘻嘻!”
唐太太轉過臉來丟了他一個媚眼:“猴急個啥?早晚都得喂飽你的,哪次不是讓你可著勁兒盡著興兒?”
陸警官趁勢攬著她腦勺,叼住她的紅唇,抱了女人向床上奔去。
事畢,唐太太穿好衣服坐床邊梳頭,陸警官赤裸裸躺床上肚飽心不飽地瞅著她說:“你這一走,又把我獨個兒撂下了。你可得常來看看我,喂喂你的饞貓。”
唐太太嬌嗔:“美死個你!我哪能常來?把你暴露了,或是讓你姐夫知道了,有你好瞧的!”說著,就立起來作勢要走。
陸警官就起來邊穿衣服邊說:“等等,讓我送送你吧。”打了個嗬欠,又說,“這兩天我眼皮總跳,媽的!好像……好像有人在盯我梢呢!”
唐太太:“你出去過了?”
陸警官:“哪能一步不挪窩兒?”
唐太太臉就拉下來:“哼,準是又去找夜來香那個婊子了!我就知道,狗改不了吃屎!”
陸警官就趕忙又哄又解釋,說是隻不過出去遛遛腿兒,買點煙卷小酒下酒菜什麼的。唐太太氣兒就漸漸消了,哼了一聲說沒良心的,誰給你較真兒呀?你們男人就那德性!陸警官就又說了許多好聽的,好歹總算把一場小小的風波平息了。唐太太就說該回了,陸警官卻纏上去要她再呆小會兒,說著重又將她摟了,手也忙嘴也忙。忙著忙著二人就又相摟著倒在了床上。男的又猴急起來,去剝女的衣裳,女的說別別,時辰兒不早啦!推拒著手一撥拉,就從枕下劃出一對晶瑩光潔的物件。女的眼睛一亮,推開男的,一把抓起,見是一對精美絕倫的碧玉佩,就說:“嘻,真美!給我買的?”
陸警官一把抓過去,說:“不,不是……不能給你。”
女的就變了臉:“不能給我……給誰?哼!準又是夜來香那個小娼婦!”
男的說:“不是,真的不是。”
女的就有了哭腔:“唉,想不到我在你心裏還不如一個臭婊子……”
男的就趕忙指天指地發誓,說他是如何如何愛她如何如何想她疼她。又說,“你知道這物事兒是哪來的嗎?是宮中的寶貝呢!在宮中失竊珍寶單兒上有號兒的,我是怕你拿去招惹麻煩呀!你實在喜愛就拿去玩吧,隻是別隨便在人前顯露就是了。”說著,抓過女的手來,將玉佩拍那粉嫩嫩掌心裏。
女的將玉佩瞄了兩眼,扔一邊,嗤地笑了,輕輕拍了男的臉作態說:“你呀你呀,死冤家,姐逗你玩兒呢!不就是塊破石頭嗎?誰真稀罕呀,留著討哪小妹妹歡心吧!”
男的就說:“你真好。姐,你要喜歡日後小弟重新給你弄些更好的。”說著,重又壓女的身上,猴急兮兮就要再做那事兒。忽聽院子裏哢啪一聲響,接著又是一聲重物落地的沉悶聲響,像是有人攀樹上不小心弄折了樹枝摔了下來。男的驚得跳起:“誰?誰在外頭?”枕下抓了槍竄出去,躲大門後靜靜觀察了會兒,又在院子裏四處小心查看了遍,什麼也沒發現,咕噥著回來,說奇怪……奇怪……
女的邊整衣理發邊吃吃地笑,說:“瞧你,魂兒都嚇飛了!沒事兒,夜貓子吧!”男的就說肯定不是貓兒狗兒,是人!有人來過了!女的仍不以為意,淡淡地說是人又咋樣?也不致嚇成這樣呀,那是來保護你的呢!男的不解。女的就說是我不放心,要你姐夫讓偵緝隊派幾個人暗中保護你的。可惜人家一片苦心全沒人理會呢!男的怔了怔,就笑說保護?嗬,該不是你不放心,怕我同別的女人鬼混吧嘻嘻!女的就使氣兒說你看你看,咋樣?好心全當了驢肝肺了!說著就使氣兒往外走,卻被男的攔腰抱了,哄著拍著說你讓螳螂張來,就不怕他將咱倆的事兒說給姐夫?女的沒好氣地哼了聲摔開他手,說他螳螂張敢不聽我的?他要敢在你姐夫麵前嚼舌根兒,看我咋收拾他!道罷出了門,男的依依不舍將她送到巷口,才獨自蔫蔫地晃了回來。
京城警備司令部,寬大的辦公室裏,劉司令雙手撐在辦公桌上伏身向前盯住站麵前的肖副官,問:“真的?你可看清了?”
仍穿著西服打著蝴蝶結的肖副官:“千真萬確,屬下親眼所見!”
劉司令仍嚴厲地盯著他:“親眼所見!……你是站床邊還是躲帳後?”
肖副官漲紅了臉”:“這……不……不,屬下是躲窗下偷偷……嘿嘿……”
劉司令仰麵大笑:“嗬嗬嗬嗬!想不到想不到,堂堂局長夫人還暗裏紅杏出牆!那小娘們還怪風流的嘛,嗬嗬!”
肖副官笑著湊趣兒道:“這是他二房太太,一個五十出頭,一個二十七八,姓唐的早年又四處尋花問柳,身子早淘空了,那小娘們能耐得住寂寞?嘻嘻!”
劉司令卻端起了司令架兒,不再聽他湊趣兒說些花花柳柳的,背了手在屋裏兜起圈兒來。
其實,這會兒劉司令心裏樂著呢!唐仁和同他向來不和,故宮禁衛的肥差兒下來,二人矛盾越發尖銳。他在牆外,姓唐的在牆內,若姓唐的知點趣兒,大家發財也就罷了。可那家夥就是死把住宮門,不讓他的人越雷池一步,這叫他怎麼不動氣兒?宮中鬧出那樁公案,據查唐仁和老婆的表弟有很大嫌疑。但那姓唐的手眼通天,也不知使了啥法兒,姓陸那小子關了沒幾天,就被批準保釋了。可姓唐的雖老奸圓滑,八麵玲瓏,也免不了有所疏漏,京城裏菩薩那麼多,他還能一一拜到?且事兒鬧那麼大,不查出個名堂咋以正視聽?是故,執政府迫於輿論就來了個麵鬆內緊,繞過有幹連的唐仁和,密令他暗中偵察。按說,他要敷衍也不是不可以,他明白執政府不是非要拿姓唐的怎麼樣,隨便捉兩個小毛賊宰了就可交差了事。可這大好機會他豈肯白白放過,誰教他姓唐的平日不給臉兒?這就怪不得他劉某公報私仇了!
更讓他興奮的是那姓唐的人精一個,卻管不了自己老婆,堂堂局長夫人偷人養漢,這事兒若捅出去,不把個京城鬧得沸沸揚揚才怪!唐仁和呀唐仁和,你這個老狐狸,姓吳的威風你得勢,姓馮的來了你得寵,端著段執政的飯碗兒,卻同張作霖、吳佩孚眉來眼去。你以為你會永遠左右逢源?你以為你是刮不倒的樹推不翻的山?哼,這回老子要叫你賠了夫人又折兵!
又想,定是那騷娘們央姓唐的將姓陸的小子從看守所弄出來的,一來好讓那小子有機會逍遙;二來方便二人幽會;其三可進可退,萬一大事不好,即可聞風而逃。想到二人在唐仁和庇護下,在那小院做那事兒,就陰陰地笑。合計若來他個拿奸拿雙,咋施個巧法兒將二人赤條條捉住,把那姓唐的羞死才好!忽又覺著不對勁兒:二人通奸定非一朝一夕,唐仁和老奸巨滑,生性多疑,能毫無查覺?就突地站定,回頭衝肖副官問:“你沒驚動他們吧?”
肖副官怔了怔,吞吞吐吐說方才他正在窗下偷聽當兒,院角樹上突然跌下個人來。奇怪的是那人一露相就同他一樣趕緊溜了。估摸是暗中盯那騷娘們梢兒的,或者……是姓唐的暗裏派來保護那小子的。”
劉司令眉頭驟地殺緊,沉吟道:“保護?不,不對!若姓陸的真同珍寶失竊案有關,姓唐的必受牽連。何況姓唐的是不是幕後主使都還難說……鑒於此,姓唐的必恨不能將其置之死地,以斷禍根,此其一;二人通奸已久,姓唐的不會毫無查覺,這亦可令姓唐的暗起殺心!此其二。姓唐的耳目眾多,我們暗中查訪此樁公案的事兒,他不會不知,故可斷定保護是假,防我們突然下手,掏走姓陸的是真!一但發覺我們有何不利之動作,他還極可能殺人滅口!你這一驚動,我料定姓唐的不下殺手也會立即將那小子轉移了!”
肖副官:“有理!有理!司令高明!”
劉司令大步走過來,猛一揮手命令道:“立即行動!把那小子給我抓來!”
肖副官:“是!”又顧慮重重地,“司令,這一來,咱可就同姓唐的撕破臉了……”
劉司令果決地:“快去!記住,要活的,有半點差池,我拿你是問!”
是夜,警察局長唐仁和家。偵緝隊長螳螂張正咬著耳朵向閉目靠沙發上的局座彙報情況。唐仁和聽著聽著臉上的隨意肌就痙攣起來,突地暴起,一把抓了螳螂張:“啥?你他媽說啥?”又突地鬆開了手跌坐沙發裏,喘著粗氣問,“可是瞧真切了……這回你可是……瞧真切了?”
螳螂張戰戰兢兢地:“當然……當然,不是我……雖說不是在下……卻是手下弟兄親眼所見……”
“奶奶個熊!老子早瞅那小子賊眉鼠眼不是玩藝兒,這回那小子算是活到頭了!去!你立即帶幾個弟兄去把他給我做了!”
螳螂張說:“可是……夫人麵前……”
唐仁和暴怒地:“奶奶個熊!你他媽聽我的還是聽她的?”
螳螂張:“是!是是!”轉身走。快出門時,唐仁和又抬手把他叫住,咽了口氣兒說:“得得得,別弄死了,弄廢,弄傻,讓他說不得話做不得那事兒就是了!”
螳螂張笑著心領神會地說:“局座放心,保證辦得妥妥貼貼,滴水不漏!嘻嘻!”
當晚,送走表姐後陸警官陡覺分外的寂寞,就找出瓶酒,就了表姐帶來的下酒菜和點心,獨酌獨飲起來。
這些日子他實在悶得慌,雖說隔三岔五可溜出去逛一遭,青樓妓院裏快活陣兒,卻總像作賊似的,不敢過份招搖,他本是個年輕又風流的主兒,平日裏威風八麵,京城裏橫著來豎著去,哪受過這份洋罪?可宮中那樁公案確實把他嚇了身冷汗,哪想到事兒會鬧那麼大,要不是有姐夫兜著,還不早將他鬧了個人仰馬翻?是故,他才肯接受表姐的安排,委委屈屈貓這兒來。
說來這事兒全怪那個叫青龍一郎的日本人,若不是那家夥軟硬兼施,慫恿恐嚇,他就是再貪頂天也隻是順手牽羊撈點兒,哪敢將宮中珍寶大包大包往外順?青龍那家夥先隻說要找張什麼畫兒,後來卻啥物兒都要了。讓他作內應,邊找那畫兒邊將宮中珍寶往外順。幹了兩三回,他就路兒也熟了,膽兒也大了,還暗裏歡喜,覺著實在是個不錯的發財門道。如今可好,鬧出事兒了日本人躲得連他媽個鬼影兒也不見,啥罪名兒啥洋罪全由他獨自頂著。他娘的!
還有表姐,其實他從沒真正喜歡過她,他喜歡的是她的小妹。好久以來,他一直暗戀著小表妹亞婷。亞婷還在上海念書,一副時代驕子樣兒,思想又激進,沒正眼瞧他,當麵撇嘴兒說他是花花公子、衙役。就是為了接近亞婷,他才時常出入表姐家,哪想無心插柳柳成行。他也明裏暗裏向表姐表示過,要表姐說合這好事兒。可表姐對她小妹珍惜得不行,一提這事兒就變臉。這態度讓他惱火氣恨得不行,可他知道他還離不了她,特別是眼下,沒表姐撐著在外頭張羅著更不成。再說,他同日本人那樁交易表姐是知道的,若把她惹惱了,將那事兒說出去,別說其他,姐夫跟前那關他就不好過!唉,罷罷罷,想這些煩心事兒幹嗎?喝酒喝酒!
他狠呷了口酒,吃了兩口菜,為趕走那些煩心事兒,就咿咿呀呀哼起小曲兒來。看見床上那淩亂的樣子,卻又想起剛才的歡暢,就想表姐那女人還是不錯,處處護著他,不圖名不圖利的。鬧出那樁公案她可是急壞了,姐夫麵前自不必說,還四處替他打點。好歹將他保出來,又怕他飲食起居不便了,從局子裏找了個可靠的老頭兒來這兒侍候他;又怕讓人暗算了,讓姐夫派人暗裏護著;又怕他寂寞,他剛貓這兒三、五天,她就趕來慰問了,明知姐夫多著心眼兒她也不管不顧的。想著就不禁得意起來,就滿滿幹了一大杯。覺著自己實在福氣不淺,有女人寵著,有門道發財。等老子撈足了大發了,還愁亞婷那妮子不答應!等老子熬過這一關,再穩紮穩打撈他幾把就走人。到那時候榮華富貴可就他媽享也享不完了!哈哈!
想得歡喜了就又幹了一杯。又從身上摸出那對玉佩把玩起來:嗬,乖乖,無價的小寶貝兒啦,才舍不得離身呢!據說這可是乾隆皇帝老頭兒曾佩用的!瞧,這兒還刻著“弘曆”二字呢!嘻,亞婷,哥的小親親呀,瞧,這寶貝兒配你才是真個兒相映生輝呢!嘻嘻!
這麼哼哼喝喝,胡思亂想喝了陣,一瓶酒早下去多半,不覺就暈暈然了。又點了根煙卷兒抽了,這才收好玉佩,跌跌撞撞晃床前,倒樹杆樣倒下,隨手滅了燈。
燈一滅,黑暗中就有一柄雪亮的尖刀從窗縫兒伸進來,去撥那窗栓兒。不料那姓陸的並沒睡死,聽到響動就懶懶問:“老頭兒,是你嗎?咋一去這陣功夫才回來?”
傍黑時分,表姐找來侍候他飲食起居的老曾頭就回了,一去就不見回來。他猜定是表姐嫌老曾頭礙眼,有意將他支開了。
沒見應答,姓陸的就翻了個身,大著舌頭嚷:“螳螂張,你他媽少給老子裝神弄鬼!老子知……你他媽敢把我倆的事兒漏出半個字,老子斃……斃了你!”
正唔嚕唔嚕,窗戶開處,一條黑影飛撲進來!姓陸的這才覺著不對勁兒,驚起,一個“誰”字剛出口,一柄尖刀已猛紮進了胸膛。
院外胡同內,已換了軍裝的肖副官帶著幾名士兵,分坐三輛電驢子飛馳而來。
肖副官一馬當先,帶人撲進陸警官藏身的小院。
正屋窗口人影一閃,一個黑衣蒙麵人越窗而出,同肖副官等人撞個正著。蒙麵人揮刀便劈,一士兵猝不及防,腦袋被劈瓜似地劈飛半拉轟然倒地。
蒙麵人一縱一躍,避到院牆邊樹木暗影裏。肖副官等人這才回過神來,一齊朝那兒胡亂開槍。豈料此時屋頂又悄然落下個蒙麵人來,從幾個身後揮刀攻來,一陣劈磕眨眼間已將身邊幾個士兵手中家夥劈飛磕掉,又扭腰翻腕飛削肖副官腦袋。肖副官突見一柄雪亮亮長刀削來,哇呀一縮脖子,腦袋好歹保住了頭上帽子卻帶著一絡頭發遠遠飛出院牆外去了!肖副官嚇得魂飛魄散,慌忙率眾退到院門外去。
胡同口,螳螂張率著幾個便衣匆匆趕來。
螳螂張扯住一個疤拉眼隊員邊走邊道:“你把那事兒再給哥幾個說說,嘻嘻,你可是瞅真切了,那對男女作那好事兒也瞅了個一清二楚是嗎?”
疤拉眼:“咋沒?小弟先在窗下貓著哩,聽到胡同裏來人了才慌忙閃院角樹上的!嘻,那女人白嫩嫩的嘖嘖……”
螳螂張卻又故作正經,吒:“媽的!你知那女人是誰嗎?亂嚼舌根老子斃了你!”
疤拉眼慌忙吞著口水點頭哈腰道:“小的明白小的明白!咱可沒漏半絲口風兒……那女人是誰,這樣大威風?”
螳螂張厲聲喝:“不該知道的少打聽,免得腦袋搬家了還不知為啥!”
正說著,猛聽胡同裏槍聲大作,螳螂張一跺腳:“糟,快快!都給我扯抻溝子跑哇!”
螳螂張領人飛跑而至,遠遠瞅見院門處影影綽綽幾條人影在向院內開槍,以為是有人在同陸警官交火,舉槍就打,那邊立即有人哇呀號叫,顯然是中彈了。
肖副官等人腹背受敵,慌忙貓院門台階後舉槍還擊。
院內,兩個黑衣蒙麵人相互點點頭,飛身上房,轉瞬遁去。
院外胡同裏槍戰仍在繼續。肖副官這邊人少漸漸不支,邊打邊退,偵緝隊後來居上,步步進逼。
螳螂張貼著牆根兒向前竄了幾步,就地趴下,扭頭招呼:“弟兄們,別都打死球,留個活口!”道罷,覺著身下壓著個啥物事好不得勁,摸出湊眼前一看,卻見是警備部隊的官帽兒,大驚,心說糟了!這他媽到底唱的啥糊塗戲?燙了手樣趕緊扔了帽兒,罵著娘縮回去悄聲招呼幾個嘍羅:“別打了,快走!都他媽快悄悄兒溜吧!”
幾個嘍羅見大勝在即,不甘心,又乒乒砰砰開了幾槍,見頭兒老鼠遇貓樣前頭溜了,才跟著退去。到了胡同口外街道,螳螂張領頭撒腿兒飛跑,跑入一岔街後,一個嘍羅就喘喘地叫:“別跑了,隊長,遇見活閻王了呀?沒見你嚇得這樣過!”
螳螂張這才收住腿兒,道:“媽的,這回比撞見活閻王還糟!你們道剛才咱朝誰開火來著?警備司令部的人!這事兒誰他媽都不準露半絲兒口風!要不猴兒們一個個吃飯家夥都得掉球!”
眾嘍羅一齊乍舌。
小院前,肖副官提了槍立進院門的台階上,莫名其妙地望了胡同外:“媽的!這是……咋回事兒?”
肖副官儼然以勝利者自居,領著人氣昂昂穿過院子,破門而入,卻見滿床鮮血,陸警官已暴死在床上。肖副官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