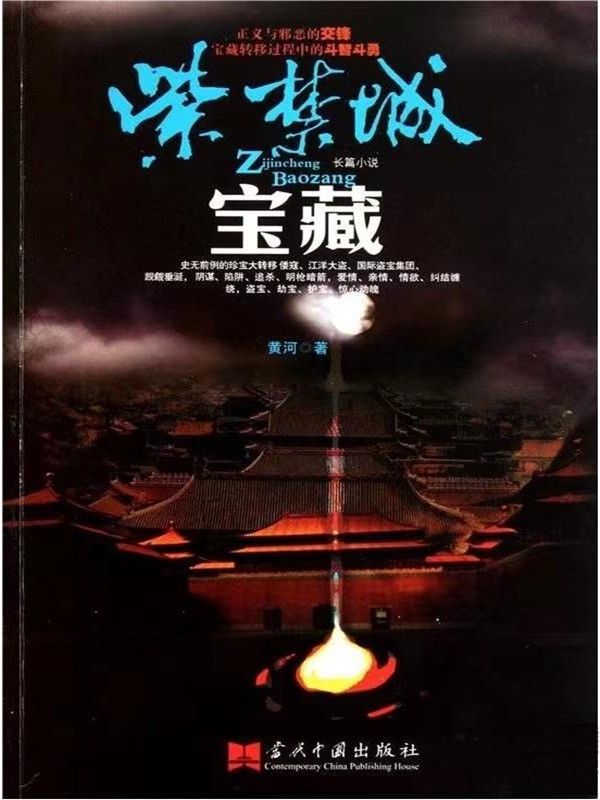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五、假查實庇大貪護大盜 父命如山情急闖情窩
這是座青磚高牆、古色古香的宅院,早年不知是哪家富戶家祠,而今卻充了京城警局的看守所。一些不幹緊要卻又讓當局和軍警政要們看不順眼的人,就關在左右兩排略加改造過的屋子裏。當首那原是拜祭祖先的地方,如今成了看守所頭兒們辦公兼起居之所。剛進陽春三月,庭院中已有雜花開樹,祠堂高高的石級兩邊,幾棵老槐亦早已懷春吐綠。自然不管人間事,以一種超拔的胸懷,恒定的意誌,將花朵和陽光一視同仁地賜給這個與之不協調、不和諧的地方,卻讓院內持槍掖炮、四處走動的看守警衛和偶爾響起的鞭打聲、慘叫聲破壞殆盡。
歐陽遠崗大步走進看守所。聽到在押人犯痛苦的號叫和看守的叱罵,歐陽皺了皺眉頭,心說還是老作派嗬!看守所暴虐人犯已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特別是那批鬧學潮的學生關進這兒,讓看守揍壞幾個後,抗議之聲更高。可今天看來還是老樣兒,看守隨便打罵拘押者,甚至拿人犯散氣取樂兒的事仍然有,令他這從馮玉祥的革命軍中過來的看不慣,反感。
歐陽遠崗輕捷地踏著碎石鋪就的甬道向所長辦公之處的正首祠堂走去。脫下了厚笨的冬裝,腰紮寬皮帶,足蹬高筒馬靴的青年警官更顯英氣勃勃。
看守所長秦歪嘴這會兒心情正好,兩腿搭在辦公桌上,叼著煙卷咿咿呀呀正哼小曲兒呢!猛見門口一暗,一個著裝整齊的警官站到麵前,慌忙跳起行禮。待認出是歐陽警官,才定下神來,親熱地招呼:“嗬哈,是你老弟呀!咋不打個招呼,成心嚇掉兄弟魂兒呀?……噫,今兒個咋想起到咱這倒黴地方轉轉?”
歐陽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是奉局坐之命來讓你放人的。秦所長就哈哈道是姓陸的吧?我早料到了,還不是做做樣兒,堵人嘴巴!放心,局長夫人親親的表弟,咱哪敢有半點委屈?還不是當祖宗供著呀!歐陽問人呢?所長說大屋裏同弟兄們玩骰子散悶兒去了,這會兒該正上勁兒呢!歐陽回頭便走。
院角看守們困覺的大屋內,陸警官正同幾個看守圍桌賭錢,咋咋唬唬,正在興頭上。歐陽遠崗背了手走進來,幾個全然不覺。歐陽站陸警官身後看了會兒,拍拍他肩膀道:“陸兄,沒想你倒會隨時取樂,就地發財哦!手氣不錯嘛,嗬嗬!”
陸警官回頭看看:“歐陽兄,虧你還想得起來看看我這倒黴蛋!來,玩幾把,小來來!”
歐陽搖搖頭,含笑說:“看來外邊人替你著急你反不著急,還樂不思蜀了呢!”
陸警官一楞怔:“噫,是來放我的吧?”歐陽點頭。陸警官扭頭抓起搖骰子的茶碗兒:“哈哈!老子今天走大運,不進財有鬼!哈哈哈哈!接著來!接著來!歐陽兄,莫慌,看我的!”嚷著,就雙手將搖骰子的茶碗兒高舉過頭,猛搖。邊搖邊念念有詞:“來來來,來來來,天牌地牌霸王牌,屙屎揀金混來財呀……開!”
歐陽笑笑,轉身走。
陸警官大聲嚷嚷:“哈!贏啦!老子贏啦!”回頭見歐陽已經出屋,抓起桌上錢往口袋裏亂塞,喊:“等等!等等!一起走呀!”
陸警官追上歐陽,罵罵咧咧地說:“媽的,不明不白在這兒圈了這麼久,快把人都逼瘋了!歐陽兄,這次多虧你幫忙,走,我兩弟兄去喝幾杯兒,我請客!”
歐陽遠崗:“這就見外了!說來我也不過是傳了個話兒,有你表姐在那兒用得著我費神嗎?嗬嗬!”
陸警官:“話不是這樣說的,你看,今兒還不是你老兄在為我跑腿兒。唉,患難見真情啦!老兄你放心,咱也不是沒心沒肺的角色,日後……”
正說著,秦所長整頓衣冠跑了過來,嘿嘿著直向陸警官道賀,又為這段時間照顧不周說了不少要陸警官多多擔戴的話兒。陸警官愛理不理,皺著眉頭說行啦行啦,我明白你也兩難,去吧去吧!管自攜了歐陽的手走出門去。
出了看守所大門,歐陽遠崗將陸警官扯街邊,叮囑道:“局坐的意思,你雖然出來了,但暫時還不能公開拋頭露麵。你表姐在背靜地方給你找了套屋子,”說著,將一張紙片兒塞陸警手裏。“幹咱這行的難得有個清閑,你就好好調養陣兒吧!此外,秦所長那兒,你還得再去看看,盡量把事兒弄得妥貼些,莫留啥尾巴才好。兄弟我還有事在身,就不陪了!”道罷,拱拱手,大步而去。
大柵欄清茗茶樓。樓上,一張臨街靠窗的桌邊,馬家田同龔長壽正品著茶小聲交談。
龔長壽:“家田啦,這京城裏怕是差不多讓你翻了個遍吧?這樣梳來梳去的都不見個影兒,我看十有八九小月同你關伯是離開京城了。”
馬家田:“他們會到哪兒去呢?回山東老家了嗎?不……不會吧,既然……”
龔長壽:“也難說嗬!剛開始那陣兒,肅親王一走,革命黨這麵炸了窩,到處嚷嚷著要拿奸細,風聲那麼緊你關伯也沒走,隻是隱姓埋名在這京城裏東躲西藏。不過事隔多年,這世道變戲法兒樣鬧哄哄地變,就難說了!”
馬家田愣愣神兒,擰眉思索著道:“縱是回老家了吧,關伯臨行咋也該來向你辭個行兒,丟個話兒呀!咋就無聲無息走了?且這麼多年沒一點消息……唉,伯呀,我看再呆這兒也沒啥意思,我還是先回蓋縣吧,我爹近年舊創常犯……”
龔長壽忽冒出個念頭,眼一亮,抬手切斷他話道:“等等,哈,我咋先沒想到……”複又敲敲自己腦袋,“該死!該死!咋能往那臟地方想?不……不會……”
馬家田讓他鬧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問他是咋了?啥臟地方會不會的?龔長壽搖搖頭說:“我尋思這京城裏我們還有哪些地方你沒去找過,就一下子想到了花街柳巷和青樓。該死!這不是汙損你關伯和小月姑娘嗎?想你關伯何等剛直英雄,再怎麼也不會走到那一步呀!”
馬家田沉吟了會兒,剛想說什麼,樓梯一陣緊響就見兩三個肩挎炮匣兒,外披黑色對襟短衫的主兒闖上樓來。龔長壽桌子底下碰碰馬家田,悄聲道:“偵緝隊來啦!瞧,領頭那個手上托著鳥籠的就是偵緝隊長螳螂張,小心了!”
螳螂張立樓梯口將眾茶客掃了幾眼,慢慢走到旁邊一張桌子坐下來,夥計趕緊上前招呼:“呀!張隊長,這陣兒忙啥哩?咋好久不來光顧了?嘿嘿,你老這回可得多坐陣兒!”
螳螂張斜眼打量著樓上茶客:“擎鷹牽狗逮強盜呀!媽的,人模人樣的飛賊大盜不讓咱爺們安生哇!”說著,目光逐個瞅來,很快就咬住了窗下埋頭喝茶、虎背熊腰的馬家田,向兩個手下丟了個眼色。兩個家夥就搖過去,一個繞到馬家田對麵,抬起大腳踏在凳子上伸脖瞪眼地將馬家田死死盯了;一個走到馬家身後,在他肩上拍了掌,喝:“好呀個你!膽大包天!這回看你往哪跑!”
馬家田頭也不回,冷冷道:“咋唬誰?耍這套把戲也不看看地方!”
腳踏在凳子上那家夥在桌子上猛拍一巴掌,吼:“說!哪來的,幹啥營生的?”
龔長壽慌忙立起,打躬作揖陪笑臉:“哎呀,是二位仁兄呀!這是我內侄子,鄉下來的,剛從鄉下來的……”
站馬家田身後那家夥一把撥開龔長壽:“誰讓你說話啦?一邊去!”
龔長壽瞪了眼馬家田,揚揚下巴道:“二虎呀,還不快起來向二位爺行禮認錯兒!鄉下人就是少見識,兩位爺逗耍一下就嚇懵了,禮數兒也不知曉了!”
馬家田冷臉端坐,悶悶道:“伯,我沒錯。”
龔長壽一急,上去扯了他胳膊剛想要教訓教訓他,扭頭一瞧,又像發現了啥寶貝樣丟開他驚喜地朝螳螂張奔過去:“哈!張隊長,你老啥時來的?這才叫有緣呢,我正找你老呢!”
螳螂張喉嚨裏唔了聲,說那小子哪來的,你龔掌櫃的啥時認了這麼個親戚?龔長壽說人有三親六戚,皇上還有幾個窮老鄉呢!哪能自尋麻煩認幹親兒!那是我內侄,東北蓋縣鄉下來的。螳螂張冷冷瞅著穩坐那邊的馬家田,說關東來的,該不是奉軍派來的探子吧?龔長壽說你老玩笑了,瞅他那木頭疙瘩樣兒,能幹那差事?嗬嗬!年景不好,來京城謀事兒混碗飯吃哩。唉,煩人啦,張隊長,這些鄉下人瞅著咱京城石板縫兒裏都長金子呢!
螳螂張也不答理龔長壽的叨叨,托了鳥籠搖過去。龔長壽趕緊顛顛地跟上,幹笑著湊他耳邊輕聲說我這幾天正找張爺你呢!我這侄子沒別的本事,就一身蠻力氣,原想替他謀個守家護院的事兒,後來一合計,還不如到張爺你手下當個差兒,跟著你老又威風又出息。若是你老肯給這個麵子的話嘿嘿……說著,將一包用紙封好的大洋偷偷塞螳螂張口袋裏。
衣袋裏沉甸甸地墜了包大洋,螳螂張麵上立馬好看多了,走到窗下立了,將馬家田細細看了會兒,問了來龍去脈,馬家田一一答了。又問可會功夫,說瞅你這身坯兒像個練家子呢!馬家田木訥訥搖頭說不會。龔長壽一旁打哈哈說我這侄子心眼少點,可也不笨,鄉下剛出來,怯生呢。日後隊長多調教調教,少則半年,多則年半,保準是你老手下一把好手哩!嘿嘿!又讓馬家田快叫張爺。馬家田就立起欠身行了一禮,叫了聲張爺。螳螂張就嘻開臉說這就對了,想跟我做事兒,可不是光有一身力氣就成的哩,嗬嗬!笑著過去拍拍馬家田肩頭,突然腳下一勾肩膀一撞,馬家田哇呀一聲仰麵便倒。
龔長壽驚慌地嚷嚷:“這……這是從何說起?這是從何說起?”
馬家田躺樓板上直哎喲。螳螂張哈哈大笑,說沒別的意思,試試他本事罷了!道罷,朝兩個手下一揮手,拎起桌上鳥籠大步下樓而去。龔長壽衝著幾個脊背道:“張隊長,我剛托你的事兒呢……”螳螂張頭也不回:“再說吧!”
幾個下了樓,龔長壽又趕回窗前,從窗口瞅著幾個走遠了,才回過頭來重重喘了口氣,一屁股坐下直擦冷汗。
當日下午,馬家田穿戴得整整齊齊單獨出現在前門石頭胡同。
那會兒這石頭胡同可是京城有名的花街,是青樓春館蝕骨銷金的所在。隻是那都是比較上檔兒的妓院,是有錢有權的老少爺們尋開心的地方,下等人是玩不起的。
馬家田搖著折扇不緊不慢從胡同口走來,身上光鮮,神態悠閑,活像個家產殷實的浪蕩子錢多了燒得慌,跑這兒來銷金消魂兒了。
隻見他見了青樓妓院就進,裏頭打一轉很快又鑽出來,好像個特別挑剔的玩主,也不管鴇婆和大茶壺咋糾纏,一不中意就管自抽腿走人。出了這處青樓,又鑽進別處春館。
馬家田鎖著眉繃著臉,大步闖入張燈結彩的夜來香妓院。他是來找關小月的,可跑了一家又一家蹤影全無,禁不住心頭煩躁。龔長壽讓他別來瞎闖,說你關伯他們咋也不會淪落到那種臟地方。馬家田不死心,隻要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他都不放過。世態炎涼,隔了這麼些年,誰知道呢?何況經了辛亥年那場天翻地覆的變故,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破落後,妻妾女子被賣到娼寮為妓的,也不是絕無僅有嗬。
馬家田剛進門,大茶壺就顛顛地迎上來,打躬作揖笑嗬嗬招呼:“這位爺,你可算是走對門了,咱這兒可是名花競豔,佳人如雲哩!不到咱這兒來樂樂,哪顯得你爺的氣派?嘿嘿!”
馬家田懶得理他,徑直朝裏走去。闖了幾處,他已看出來,這種看家狗兒最煩到這來找人的,你要向他打聽,沒一個肯說真話的。你要找人,就隻有自己瞪大眼睛看。
妓院內嫖客盈門,有紈褲子弟、富商大賈,也有流氓政客、社會名流。一個個抱紅擁翠,調笑作樂,汙言穢語和浪笑聲不絕於耳。又有一縷清新曼妙的絲竹之聲從院內樓上傳來,如潺潺清泉,空穀鬆風。
馬家田想這家青樓的錢罐兒、壓軸兒的角色定在那上頭了,就穿過回廊過廳直上木樓。
大茶壺顛顛地追上樓來,攔了馬家田說:“噫噫噫,這位爺,咋隻管蒙頭往裏鑽,東瞧西望啥呢?不是我掃爺你的興,嘿嘿,不知你是哪位姐妹的舊相好呢還是……”
馬家田冷冷說:“我沒舊相好,也不是來找樂兒的,是來找個人罷了。”
大茶壺立馬變了臉,冷哼一聲說:“找人?我看你是來找亂兒的吧!找誰?我早瞅你賊眉賊眼的,該不是來踩盤子行打劫的吧?”說著就來扯馬家田。馬家田手腕一翻抓住他手脖兒,不動聲色地輕輕一握,大茶壺即疼得殺豬般號。
鴇婆聞聲趕來:“喲,是哪位官爺駕到啦!大張,是你衝撞咱的財神爺了吧?還不快跟官爺行禮賠罪!”鴇婆扭著腰擺著屁股忙不迭地打圓場賠禮兒,又回頭招呼,“春花、碧桃,還不快出來,貴人來啦!”
就有兩個濃塗豔抹的女了脆脆地應著飄來,一左一右將馬家田纏了,吃吃咯咯說:“喲,好俊氣的少爺哥呀!莫動氣兒莫動氣兒,把咱姐妹心疼死啦!來,讓咱姐妹倆好好伺候你,嘻嘻!”
馬家田雙臂一振,將兩個女子振了幾個趔趄,朝老鴇拱手一揖,說:“老媽媽,對不住,馬某今天沒空閑尋樂兒,我是來……”
老鴇詫道:“到這來不尋樂兒來幹吧?”
大茶壺躲鴇婆身後甩著餘痛未消的手說:“哼,別瞧他穿得光鮮,馬屎皮麵光,玩得起嗎……”
馬家田聽了,掏出兩塊大洋手心裏掂掂。老鴇一見錢臉上立時笑得燦爛,顛顛地湊上來。馬家田卻轉身輕輕一抖手,銀洋便帶著風聲貼著大茶壺耳旁飛過,一一嵌入他身後木柱。大茶壺嚇癱,嘴巴亂抖語不成聲。
馬家田也不理他和嚇得屁滾尿流鑽回屋子的兩個煙花女子,朝驚呆了的老鴇道:“老媽媽,你開這院兒隻為一個財字,當然不想有啥意外之災,飛來橫禍是嗎?”
老鴇:“是。是。”
馬家田指了柱子上大洋說:“在下隻想向你打聽個人,你隻要照實說來,那些大洋就是你的了;如有半句虛言,哼哼!”
老鴇:“一定一定,不敢不敢。不知……”
馬家田:“你這兒有沒有個叫關小月的?”
老鴇:“沒……沒有。”
馬家田猛地跨前一步,瞪眼悶哼一聲:“嗯?真話?”
老鴇一屁股跌坐下去,聲兒顫顫地說:“真……真話!真話!如有半句不實,任你剝了剮了都成。”
馬家田又問這石頭胡同另外幾家可有,老鴇說沒有,這胡同裏幹這營生沒她不熟的,哪家有幾個搖錢樹,哪家有多少姐妹,後台是誰常客有哪些,她都了如指掌,就是沒有叫那名兒的。老身知道小爺你定是隱性埋名的義士大俠,老身在這風月場中混了大半輩子,沒想今日有眼無珠冒犯了小爺,還請小爺多多包涵。而今世道亂得不成樣子,無法無天,誰把幹咱這營生的當人?有錢有勢的來咱這裏消遣作樂兒,擺威擺闊,盡管咱百般曲意迎合,小心伺候,稍不如意還不是張口就罵,抬手就打。弄不好飯碗兒也砸了,小命也丟了!求小爺念老身苦苦撐持這個院兒不容易,抬抬手讓過咱這一遭吧。老鴇婆隻管趴地上絮絮叨叨,半天見沒回應,抬眼偷偷一瞄,才見那個功夫驚人的年輕漢子不知啥時已去了。
馬家田走出夜來香妓院,在大門口同身著便裝、公子哥兒打扮的陸警官擦肩而過。
陸警官身後七八步樣子,著漢服的青龍一郎大搖大擺走來,隨陸警官之後步入夜來香妓院。在進門的當兒,青龍一郎像聞到了什麼,回頭掀起壓得低低的禮帽,狠狠剜了馬家田一眼。
馬家田坦然穿過街巷,向斜對麵的紅袖樓妓院走去。
離夜來香大門十餘米處的街巷邊,一小賣店內,偵緝隊長螳螂張同一便衣正瞅著夜來香大門口咬耳朵。便衣偵緝隊員:“媽的,瞧,那主兒多會尋樂兒!這會兒還有心思爬奶頭山,倒把你我閃得沒勁兒了,嘻嘻!”
螳螂張淫邪地咧嘴笑笑:“禁了這麼久的葷腥他受得了?這一進去,老子估摸他不把骨油溜幹不會出來!嗬嗬!”忽覺不對勁兒,朝手下便衣,“噫,注意到沒?他身後好像跟著進去了個人!”
便衣:“是嗬,可這有啥驚怪的,這夜來香可不是他包了的呀!想尋歡作樂的主兒多啦!”
螳螂張拉了臉壓低嗓門罵:“操你媽!敢跟老子油嘴滑舌!局長讓咱來幹啥吃的?他要是出了半點差錯,局長拿老子出氣,老子就拿你開刀!哼!”
又等了會兒,螳螂張熬禁不住,說要進去看看,叮囑了身邊的便衣幾句,就顛顛跑進夜來香去了。
螳螂張找到院裏的大茶壺打聽,大茶壺抬手往樓上一指,咬著耳朵跟他嘀咕了幾句,螳螂張就饞兮兮淫笑起來。大茶壺就說隊長,你今兒個是要嘗個新鮮呢,還是要找你的老相好白姑娘?螳螂張就連連搖手說不要不要,今兒個大爺是七仙女都不敢要呀!公務在身呢!正說著,鴇婆就鴨子下河樣擺著屁股過來了,受人欺負的小女兒見了老爹樣欣喜又委屈地說:“呀,張隊長呀,人家正要找你呢!你再若不來,我這老命兒就該沒啦!”
螳螂張以為樓上出啥事兒了,擔心著局長交下的差事兒,頭皮就一炸,急巴巴地問:“咋了?咋了?”作勢要拔腿衝上樓去樣兒。老鴇就說早跑啦,準是知道張隊長你要來,嚇得車溝子溜啦!螳螂張一顆心才重又落回肚裏,細問原委,老鴇一五一十說了。又纏了螳螂張要他給她作主,將那個挨千刀的找出來,打斷他腿兒,剝了他皮兒,替她出氣。螳螂張將眉頭皺得稀爛,煩煩地揮揮手說:“得得得,爺們今兒沒心思聽你嘮叨!”道罷,抽身出門。老鴇和大茶壺送出來。
大茶壺走到門口,一眼瞟見從紅袖樓出來的馬家田,揚手朝螳螂張喊:“就是他!就是他!張隊長,那個鬧事的小子在那兒!在那兒!”
馬家田聞聲掉頭朝這麵望了望,覺著不對勁兒,趕緊轉身疾行而去。
螳螂張一時沒明白過來,問:“啥?又他媽嚷嚷個啥?”老鴇也瞅見了,就指了疾疾行去的馬家田嚷:“快!快呀!就是那小子!大鬧咱夜來香的就是他呀!”螳螂張這才弄明白與保護姓陸那小子爬女人是兩碼事兒,趕緊拔腿追去。待他追到胡同底,馬家田早沒了影兒。
螳螂張回到夜來香,找了老鴇和大茶壺細問那鬧事後生長相。兩個就描繪了番,免不了又顛三倒四把事兒重說了遍。螳螂張就讓兩個領了上到樓頭,來到那讓大洋射過的廊柱前。大洋已被取走,木柱上留了兩個嘴巴樣口子,入木過半。螳螂張拿手摸了摸,不禁打了個冷噤:好家夥,這手段用在人身上還不射幾個透明窟窿!
下得樓來,老鴇就屁顛顛追上去問張爺可戡出了個眉目?瞅他那樣兒定是哪處深山老林裏下來的巨盜慣匪!螳螂張卻尋思著自言自語:怪道……瞅背影兒好像是……那小子,可那小子咋會這一手……莫非他……
老鴇就說:“張爺,你心裏準定是有譜兒了嘻嘻,老身麵前還神神道道保密呀?說說,他是誰。”螳螂張厭煩地斜了她眼,說:“說來你也不知道。”
這一折騰,又是呼又是喊的,免不了驚動院裏嫖客,樓上樓下的遠遠立了看熱鬧。螳螂張拿眼將旁邊交頭接耳的紅男綠女掃了幾回,猛地一拍腦袋,叫聲糟!媽的!咋把正事兒忘了!轉身飛奔上樓,咚咚咚衝先前陸警官消魂那間香巢挑簾兒一看,哪還有人?找了陪他的姑娘一問,那女子飛他個媚眼,擺擺腰肢嘻嘻說走了呀,火上房子似的。爺你要有興致,正好……
螳螂張一把掀開蹭上來的賤女子,罵了聲騷貨!滾你八輩兒祖宗的蛋!就狗攆著樣慌慌地去了。
白紙坊,醜街陋巷裏,破落的大戶子弟打扮的馬家田悠悠搖來。
白紙坊是京城下等妓院和境娼集聚之地,他不肯放過任何機會,狠著心腸要把這老北京翻它個遍。要再找不到關伯、小月他們,他還準備去山東找找呢!龔伯伯說得對,這樣沒頭沒尾地回去,咋向老爹交待?再說,爹爹讓他來京,主要是想讓他在京城謀個出身。如今莫說立身揚名,連個立腳之地都沒了,回去爹又該抱怨他不懂事,給龔伯闖亂兒,又該慪氣不完了。
自那天在大柵欄茶樓撞上偵緝隊那個螳螂張後,龔伯就叨叨不對勁兒,要他千萬小心。哪想前日又在石頭胡同同螳螂張打了個照麵,那家夥當時雖沒認出他來,可過後定是查覺了什麼,當日就到龔伯的錢莊來查戶口,找碴兒了。虧他警覺,聽響動不對勁兒,一個狸貓跳牆上了房頂。他趴房頂聽龔伯在下頭打著哈哈說張隊長你怕是看花眼了吧?我那內侄哪有那本事?再說,我兩三天前就打發他去通衢州辦事兒了呢!經了這番變故,他咋好再在那兒替龔伯添亂兒?堅辭要走,卻讓龔伯苦苦留了下來。龔伯想了個折中法兒,讓他先到背街一座荒廢的前清顯宦的府弟內躲躲風頭兒。他還是替龔伯擔心,龔伯說他小小一個偵緝隊長,在這京城算個屁!這錢莊可是曹公公開的,當今權貴誰見了曹公公不客氣三分?沒事兒的,十天半月,我保準你就可以在這京城裏大搖大擺走來走去了!
馬家田沿白紙坊街巷慢慢行來,一會鑽進妓院,一會兒站下來向傍門而立的暗娼打聽什麼,可每次都是失望。
馬家田從一家妓院蔫蔫出來,頹喪地立街心發楞。一個暗娼搖過來挽了他胳膊,扭腰送胯地賣弄風情,又拿一對小山樣奶子往他肩頭蹭:“喲,這位小哥,人家嫌你錢少是吧?嘻,沒事兒,我這是最便宜的。來,咱倆玩玩,保準讓你骨頭兒酥八輩子都忘不了呢!嘻嘻!”
馬家田一揮胳膊將那暗娼甩得一屁股跌坐街邊,眉頭一擰,扭身大步而去。
他既想在這兒找到小月,又怕在這兒找到小月。最終他還是否定了自己執拗堅持的主意,忽然覺到了自己的荒唐。跑這種臟地方來瞎闖個啥?小月是這種人?是剛才那個拿大奶子蹭他的暗娼一下子刺醒了他。那是個四十多歲臃腫虛胖的老娼婦,又老又醜的臉上厚厚塗了廉價的脂粉,參差不齊的大黃牙從抹得鮮紅如猴腚的血盆大口裏露出來,讓人看了渾身起雞皮疙瘩。他眼睛瞟向老娼婦那一瞬,小月清純如水的麵影一閃而過。他心裏突地針刺錐紮般地一疼:小月咋會這樣?她咋能同小月相提並論?再窮再窘迫再走投無路小月她也不會走這條路的!
馬家田大步向白紙坊外走去,如釋重負,渾身輕鬆。雖然仍無半點小月的消息,可他心裏卻好是熨貼,甚至有些兒欣然。身後,那個讓他摔跌在地的暗娼仍在哭哭嘰嘰罵著臟話兒,可馬家田卻一句也沒有往耳裏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