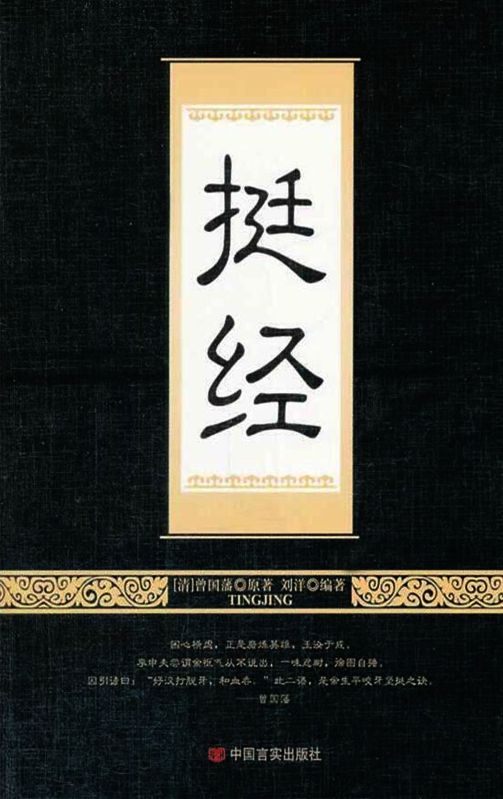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礪誌礪誌
堅誌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眾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積善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東晉]葛洪《抱樸子·廣譬》
君子施仁,堅卓其誌;帥以之氣,貞之以恒。
《礪誌》乃《挺經》二章,言砥礪精進、崢嶸雄快之道。
一 君子要樹立遠大誌向
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君子建立遠大的誌向,應當有以民眾為同胞,並奉獻出他們的所需的胸襟氣度,應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為國家與民族的振興建立功績的雄心壯誌,隻有這樣,才無愧於父母的生養恩情,才有可能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所以他們的憂慮,是以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憂慮,以自己不專修德行、不精通學業而憂慮。於是就會憂慮百姓強悍的民風沒有受到教化,憂慮邊遠地方的人沒有完全歸服於華夏,憂慮小人當道,賢人失意,憂慮還有人得不到自己的幫助,關注時運昌盛與天下百姓安居樂業,這就是君子憂慮的事情。至於自己的成敗,一家的溫飽,世俗的榮辱得失、地位名譽等,君子是沒時間為這些事去憂慮傷神的。
人的成功與否,與他對自己的期許和定位高下有著密切關係。一個自視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個誌向高遠並能踏實肯幹的人,無疑會有更大的成功機遇。若一個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淺,無疑則會成為失敗的凡夫俗子。換句話說,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製訂一個目標、一個方向。王陽明說得好:“誌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就是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
曾國藩常說:“誌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但真正的立誌卻是從他21歲那年“欲求變化”開始的。這一年,他的父親曾麟書讓曾國藩離開家鄉到衡陽汪覺庵所辦的唐氏家塾念書,後來又回本縣蓮溟學院學習。經名師指點,曾國藩懂得了要向自己進攻,在內在修煉上下足功夫,方能有造就、有前途,於是立誌法古今賢聖,做天地完人。他給自己起了個別號叫“滌生”,表示滌舊生新,日新月異,從頭做起。自此麵貌一新。
曾國藩有一次在給家人的書信中說道:
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麼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了啊!
從中能看到,曾國藩也有斤斤計較的時候,有見識淺短的時候,有心浮氣躁的時候,但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是,他敢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黑暗的部分,無情地加以拷問。韓非子說:“立誌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曾國藩正是在戰勝了自己,才得以確立誌向。
古人認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有德”的人,關鍵就在於能否進行道德修養;而“修身”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因此古人把“德量涵養,躬行踐履”本身視為一種重要的美德。“礪誌自強”是道德修養的起點,也是其內在目標和精神動力之所在。這裏講的“誌”,也就是一種道德理想。古人指出:“誌高則品高,誌下則品下。”這說明,並不是所有的道德之“誌”,價值都是一樣的。同時,即使是高遠之誌,若隻講不做,徒托空言,並不能成為德行。隻有躬行踐履,高遠之誌才是一種美德。這種美德所體現的是一種對理想人格的不倦追求。所以從道德上講,“礪誌”實質上是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一種自我超越的品性。
說到礪誌修德,誌向高遠,出身低微的陳勝是個典型的人物。
陳勝,字涉,陽城(今河南登封縣)人。他和吳廣一起,揭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序幕。他既是傑出的農民起義領袖,也是誌向遠大、機智聰慧的政治謀略家。
據《史記》記載,陳勝出身農民,家境很窮,少年時代就以幫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窮誌大,很想有所作為。他常常感歎人世,有時惆悵,有時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勞動休息時,坐在田埂上默默長思,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倘若有朝一日我發了,成為富貴的人,我將不忘記窮兄弟們。”與他一起勞作的佃農們聽後都不以為然,並笑話他說:“你一個幫人幹活的農夫,何來富貴之談?無非是說大話而已。”陳勝對於大家的取笑十分遺憾,深有所感地說道:“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
有誌者終成大事。不久,陳勝便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向人們證實了他的豪言壯語,不是癡人說大話,而是他的宏願和決心的表達。
一個人的誌向並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後天的生活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平庸、瑣細、放縱的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社會發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還會固步自封,與世隔絕,過著一種洋洋自得於個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變成一個窮居陋巷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儒家的優秀傳統,培養了中國人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起來的自覺。治國平天下的追求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箴言,已經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規範。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立誌,或立誌德業驚人,或立誌出人頭地,或立誌掃平“洪楊”。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卻有兩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國藩在任翰林後,寫下《五箴》自勉;另一件則是官拜幫辦團練大臣後,卻受同僚之辱,因而憤走衡陽,練成了湘軍。
道光十八年,曾國藩借錢入京趕考,得中第38名進士。接著複試、殿試、朝考成績都很優異。引見皇帝之後,年僅28歲的曾國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舉時代的翰林,號稱“清要詞臣”,前途最是遠大。內則大學士、尚書、侍郎,外則總督、巡撫,絕大多數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地位,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功夫,隻消鑽鑽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十餘年來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為此,他將名字從“子誠”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立誌報效國家。
立誌從哪裏立起?從“沒有”立起。自己沒有的,家庭沒有的,社會沒有的,國家沒有的,都可以成為自立目標。曾國藩所處的時代,內憂外患,民生困苦,吏治腐敗,人心離散。社會上缺的是直臣,是廉吏,是聖賢。因此曾國藩立的就是“直臣之誌、廉吏之誌,作聖賢之誌”。他的成功,正是看準了社會所需而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進去,把自己的潛質發揮得淋漓盡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