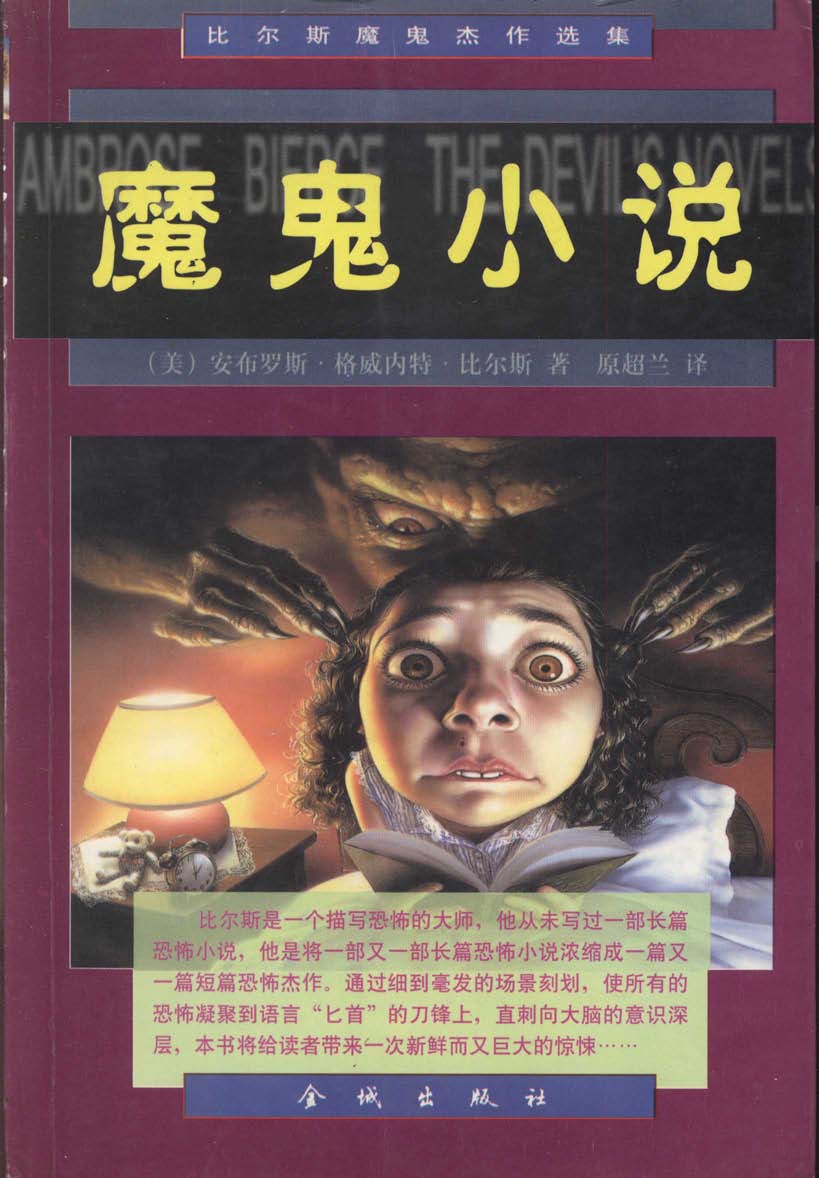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床下,有一條大蛇
根據真實的報導,並被許多最聰慧的人士所證實,這種大蛇的眼睛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使其能隨心所欲地引誘遭難者,並且很淒慘地將他咬死。
哈克·布雷頓安逸地躺在沙發上,披著長袍,趿著拖鞋,當他讀到老莫裏斯特的《科學的奇跡》的上述詞句時,他微微笑了起來,“這些事物的奇跡,”他自語道,“在莫裏斯特的年代,那些聰明博學的人要是都相信這些蠢話。照這樣我們大家就更愚不可及了。”
一連串感想接踵而來——因為布雷頓是個愛思索的人——他下意識地放低書本而不用調節視線的方向,這書一低於視線,這房間一個陰暗的牆角就喚醒了他對四周的關注。他所看見的他床下的陰暗處,是兩個小光點,明顯地相距有一英寸遠,它們或許是懸掛在他頭頂上的汽燈金屬噴嘴的兩個投影。他隻對這想了一會就又重去閱讀了。過了一會兒,某件東西——某種他未加分析的衝動——驅使他又放低書本去尋找他先前看到的東西,這兩個光點仍在原處,它們似乎比以前變得更亮,發出他第一次未察覺的綠熒熒的光澤,他想它們可能移動了點——稍微更靠近些。然而它們仍在陰暗處,向這懶散的眼光顯示著它們的原始的野性。他重新又去閱讀,突然,書上的某件事致使他驚動並第三次放低書來,拿著書的手擱到沙發邊,書從手上掉到了地板上。布雷頓欠起身來,專注地盯著床下的陰暗處,那耀眼的光點,似乎象增強的火光,他注意力高度集中,目光渴求而急切。它顯露著直接就在床腳邊,一條盤蜷的大蛇——那光點是它的眼睛,它可怕的頭,從最裏的圈中平著刺出露在最外圈,徑直朝向他,寬闊的、殘忍的下頜象白癡一樣的前額,眼神很惡毒,這雙眼不再隻是明亮的光點,而是帶有一點意圖,一個惡毒的意圖。
一條蛇突現於一間臥室裏,臥室擁有現代化城市較好的居住條件,恰好其份地說,是一件不需要解釋的非常事件,哈克·布雷頓,一個35歲的單身漢,一個學者,懶漢,具有運動員的體魄,富有、普通、看起來很健壯,從一個遙遠陌生的鄉間來到舊金山,他的嗜好通常是很奢華的,經受長時間的貧困後變得富有,因為酒店的招待不盡人意,他因此樂意接受了他朋友朱林博士——一個著名科學家的盛情款待。朱林博士的別墅麵積很大,古老的建築風格,座落在城市的一個很陰森的地方,驕傲地保留著怪誕的外觀特色,它顯然很難同已經改變了的周圍環境融洽起來,顯露出與世隔絕的古怪模樣。整個建築有一個部分象“伸出的翅膀”連在那裏,整個別墅集圖書館、動物園、博物館的功用於一體,但這一部分與整個建築的特點毫無相似之處,不過一點也不難看。
在這個部分,這位博士以他科學家的天賦沉醉於他非常感興趣的動物生活方式的研究之中,以滿足自己的嗜好——這種嗜好或許應當懺悔,因為允許低級動物頗為自由地出入。對於更高等的一種動物,需要動作敏捷和模樣討人喜歡,並毛遂自薦到他友善的官感中,它至少得保留某種退化器官特征,這種特征得與諸如癩哈蟆和蛇之類的“最早的龍”相關聯。很顯然,他對爬蟲類動物具有極大的同情心,他熱愛自然的粗俗一麵,希望用法國作家左拉的自然主義方式來描繪這一切。他的妻子和女兒們,並沒有利用她們的優勢去分享他對我們不雅的可愛動物的好奇心,而是用不必要的嚴肅排斥他所稱的蛇類,以自身的恐懼去摧毀這“友誼”,盡管她們嚴厲的態度已軟化了很多。他已對她們承諾,在他龐大的財富中,她們比奢華境遇中的爬蟲更勝一籌,更有資格沐浴在顯赫的陽光下。
在建築學上,就“陳設品”而言,蛇類具有適宜於卑微境況的嚴格而樸素的一麵,它們的許多同類,確實又因具有令人厭惡的一麵,而不能放心大膽地被委以充分享受奢侈的自由。然而在它們的館舍中,它們極少受到限製,以保護它們免於互相吞食習性的危害。布雷頓被關切地告知,它們已不止一次地在房間裏突現,令人十分困窘。盡管蛇類和對它們的神秘離奇的聯想——確實,布雷頓幾乎從未關注這點——布雷頓一下想起來,在朱林別墅裏曾發現有許多種動物。
除了猛烈的驚撼和令人厭惡的戰栗,布雷頓沒有受到更大的侵害。他閃念間就是想去搖響信號鈴,好招個仆人進來解危,盡管鈴繩懸擺著能輕易拉住,但他仍僵在那兒不動,恐懼的疑慮已使他的意誌屈服,他當然無所作為。他更多地意識到處境的非常不適宜,而更少想到這蛇的侵襲。它正令人充滿厭惡,但並不讓人覺得有點荒謬。
這爬蟲屬於布雷頓一點都不熟悉的一個種類,它的身長隻能憑推測,明顯可見的最大部位有他的前臂般粗,它在什麼方麵最危險,如果各個方麵呢?它會有毒嗎?它是個蜷縮的大蟒嗎?自然知識發出的危險信號使他說不出什麼,他再也不能破譯這個密碼。
如果不具有危險性,這畜生至少令人生厭,它是“不受歡迎的”——除非地點適宜——肯定有點非禮。這“寶石”不值得鑲嵌,甚至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國家,都崇尚粗俗的趣味——房間的牆上載滿圖畫,房間的地板載滿家具,家具上載滿小古玩,而不很適應叢林中的荒野生活,除此之外——它散發的氣息與他自己的呼吸竟然在空氣中交合著!
這些思索在布雷頓的腦海裏形成了忽明忽暗的輪廓,並導致了如下舉動,這個步驟就是我們所稱謂的思考和決定。
它因此昭示著我們的舉手投足明智或不明智,就好比說秋天一片凋萎的樹葉,它散發的氣息比它的同伴飽含著更豐富的含義,它的同伴或飄落於地,或沉墜於江湖之中。人類舉止的奧秘是公之於眾的,那就是——某種事物在牽引著我們的肌體。如果我們能麵對預知的事物變化,那遺囑的內容還會重要嗎?
布雷頓站起來,準備從這蛇的後麵輕鬆繞過去,不去驚擾它,如果可能,就跳出窗外。人們就常這樣從偉大的現場撤退,因為偉大就是力量,而力量就是威脅。他意識到可以沒有妨礙地從背後繞過,窗子沒有任何缺陷。如果這怪物緊追在後,在牆上飾滿油畫的嗜好正好能始終供給他一架子東方式的謀殺武器,他順手就能操起一件來派上用場。這其間那蛇的雙眼燃著比先前更加無情的毒焰。
布雷頓從地板上抬起右腳準備繞過蛇背後,這一刻他感到十分羞愧。
“我必須表現得勇敢些,”他喃喃地自語道。
“這是勇敢,還是僅僅隻是自豪?因為現場沒有任何人見證我撤出的恥辱。”
他現在穩在躺椅上,右手緊扶著躺椅背後,右腳懸空。
“笨蛋!”他大聲說道,“我不是這樣的懦夫,好象自己害怕自己。”
他稍稍彎著膝蓋把右腳抬得更高了一點,接著把右腳猛地跺到地板上,距後麵的左腳一英寸遠,他不能去回味這個動作,左腳進行了同樣的嘗試,又跺在了右腳前麵。躺椅背後的右手緊緊抓著靠背,胳膊也伸得直直地緊挨著,或許有人已經看見他不情願地失去了自製力。這蛇惡意的頭仍從裏圈衝出在外,蛇頭平伸著,它一動不動,但它的雙眼如電火花般閃爍,放射出無數根刺眼的尖針。
這人臉色已死灰般慘白。他朝前邁了一步,又邁出一步時勾動了椅子,轟地一聲絆倒在地板上,這人痛得呻吟著。大蛇死寂無聲,一動不動,但它的雙眼象眩耀的無數個太陽,完全地將它整個身軀掩藏在其中,放射出色彩斑斕的耀眼光環,光環連續地擴張到極限,象肥皂泡樣忽地消逝而去,光環似乎離他的臉很近,但這厭煩的距離卻似深不可測。他聽見某個地方,一麵大鼓連續擂響著,伴著雜亂的遙遠樂聲,這樂聲無可言傳的甜美動聽,象風神的豎琴正在演奏,他知道這是古埃及王梅良的巨像日出時發出的音樂聲,他正佇立在尼羅河畔的蘆葦叢中聆聽,以讚頌的情感,不朽的聖歌穿過無數個世紀的寂靜。
樂聲停止了,頗似遠方雷雨行將告退的轟鳴聲。
一幅場景,映照著陽光和雨滴的熠熠光輝,在他眼前徐徐展開,伴著一道鮮豔的彩虹,架在它巨大的彎曲的一百個隱現的城市之上,在景色正中一條巨大的蟒蛇,頭頂王冠,從它龐大的震撼中立起頭來,直勾勾地望著他,象他死去母親的眼神。突然。這蠱惑的景色似乎迅速升起,象劇場的帷幕一樣消失在空白中。他的臉上和胸膛深感某個東西的劇烈喘息。他跌倒在地板上,鮮血從他撞傷的鼻子和瘀腫的嘴唇流淌出來,一會兒他變得暈眩和遲鈍,躺著睜不開雙眼,他的臉貼著地板。不大一會,他蘇醒過來,定定眼神,然後意識到這摔跌打破了束縛的咒語。他的眼睛回避著那蛇,他感到現在能夠逃避了。但想到這蛇距他頭部幾英尺之遙,可以預見——可能朝他直射過來,纏住他的咽喉——太可怕了。他抬起頭呆望著那致命的眼睛,他又被束縛住了。
這蛇沒有動彈,顯得稍稍失去了他想象的威力,頗為華麗的幻覺未能再現。在它平坦無知的頭頂下,象第一次一樣它黑黑的小而又亮的眼睛閃耀著,伴著不可言狀的惡毒印象。
這畜生好象本來就知道它確信的勝利,已決定不再實踐它誘惑的詭計了。
結果是一幅可怕的場景:這人趴在地板上,距他的敵人一碼之遙,身體上部墊在肘部上,頭垂伏著,雙腿伸得挺直,他的臉慘白地浸泡在一淌血中,他的雙眼已經睜到最大。他的唇邊沾著唾沫,雙唇象飄落的薄薄雪片,強烈的驚懼貫穿了他的全身,他的身軀象蛇樣起伏著,他的腰部彎曲左右來回移動著兩腿,每一次移動都使他向蛇更靠近一點,他的雙手伏地支撐著他,不斷地靠肘部向前移動著。
朱林和他的妻子坐在圖書館裏,這位科學家這會兒興致挺高。“我剛剛得到一個好消息,與另外一個收集者交換——一個絕好的ophiophagus的標本。”
“那又是一種什麼東西?”這位女士無精打彩地詢問道。
“我的天哪!多麼深奧的無知!”
“親愛的,一個男人在婚後才弄清楚他妻子呆頭呆腦,居然不懂得希臘是什麼,那他最好離婚算了,這ophiophagus是一種蛇,它能吞吃其他的蛇。
“我希望它把你們都吞吃了,”她說道,離開座位移動著燈。“但它是怎樣吞吃其他的蛇的呢?通過千方百計地誘惑,我敢肯定地說。”
“真是蠢極了,親愛的,”這個博士氣惱得急忙說道,“你要知道,誰要提到關於蛇的誘惑力的粗俗迷信,都會讓我十分惱火。”
這交談被一聲強烈的尖叫所打斷,信號鈴聲響徹了整個寂靜的別墅,這鈴聲象惡魔在墓穴中哀嚎,鈴聲響了一遍又一遍,非常可怕的清晰,他們一躍而起,男的被搞得暈頭轉向,女的也麵無血色,驚嚇得說不出話來。幾乎就在最後一聲尖叫停頓的同時,這醫生衝出房間,三步並作兩步地衝上樓梯。在布雷頓臥室門前的走廓,他碰到從樓上趕下來的仆人,門並未關住,還露出一絲縫隙,他們不用敲門就都衝了進去,布雷頓正趴在地板上,他死了。他的頭和臂有部分被掩藏在床下,他們將他的身體拉出翻過麵來,他滿臉都被血汙和唾沫弄得臟亂不堪,兩眼睜得大大的,直盯著——多麼可怕的目光。
“死得有點蹊蹺,”這位科學家說著蹲下來把手捂在胸口,同時就在這個位置,他碰巧瞥了床下一眼,“我的天哪!”他喊了起來,“這東西怎麼會在這兒?”
他手伸到床下把蛇一把拖了出來,猛力一摔,它仍盤成一卷,隨著刺耳的尖叫和忙亂的奔跑聲,它滑到光滑的地板上,直到停在牆邊,它仍是一動不動地盤著。
它就是那條蛇的標本。
它的雙眼是兩個鞋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