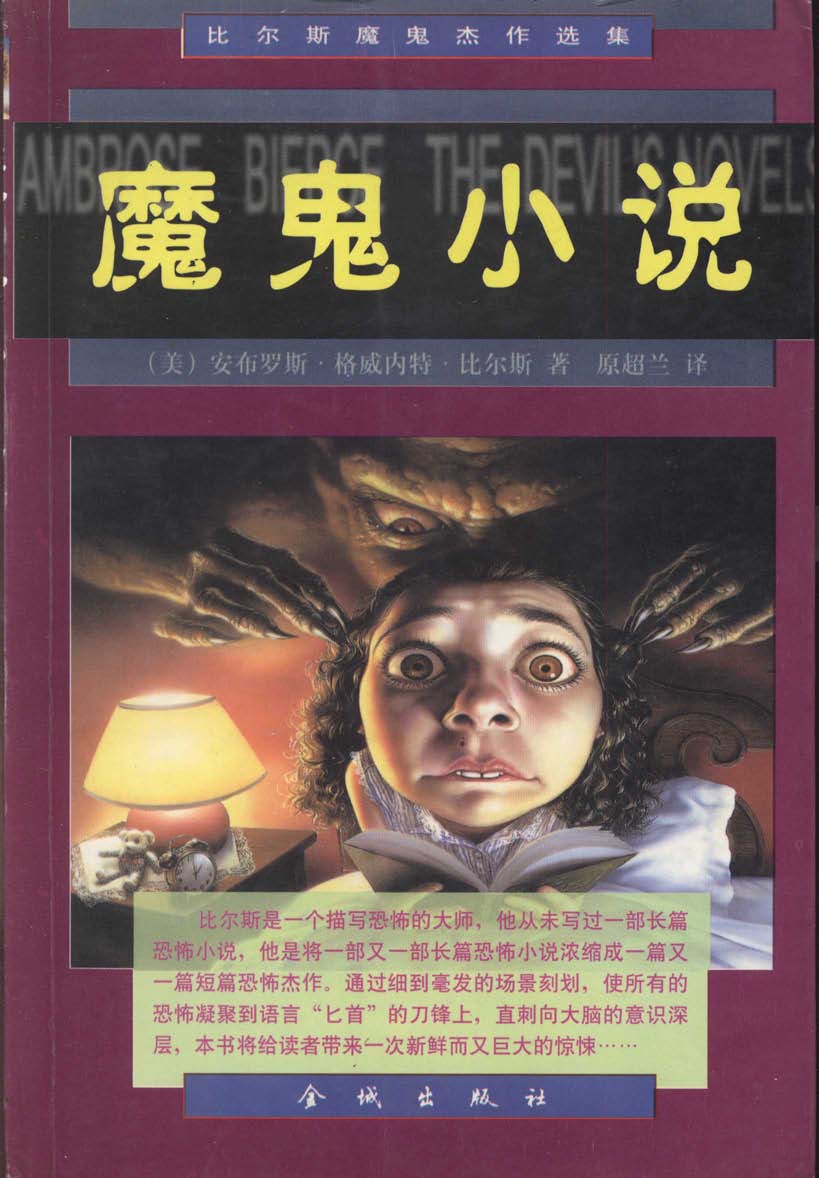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窗戶釘死的深林木屋
故事發生在一八三○年,就在如今已是繁華的大都市的辛辛那提市,距離市郊幾英裏遠的偏僻地區,生長著一片無邊無際的、幾乎十分原始的森林。整個這一帶,城市邊緣居住著為數不多的人,他們的靈魂,被來自天性中的某種神秘衝動所驅使,變得永不安分,不知歇息。他們一旦在曠野中砍伐倒樹木,搭蓋起一個個十分適於家居的小木屋,得到了那種程度的滿足,這種滿足我們現在稱之為貧乏單調,他們就會拋棄現有的一切收獲,繼續向西推進,寧可遭遇新的危險,重新忍受生活必需品的匱乏,也要奮不顧身地去重新得到他們先前自願放棄的一切東西。他們中的許多人為了更偏遠的居所,而先後離開了這個地區,但他們之中有個人最早來到這裏,現在仍然沒有離開。他獨自一個住在木屋裏,木屋的四周被大森林所包圍著,他似乎是個鬱鬱寡歡和沉默不語的劇中角色,因為認識他的任何一個人從未見他微笑或者多說一句不必要的話。他簡單的生活必需品靠在沿河小鎮販賣野生動物的皮毛,或在那兒的集市上用它們與人交換來獲取,因為,在他生存的這片森林裏,除了動物的皮毛,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用買賣來交換。或許,如果有可能,他可以利用這片不受人幹擾的森林,與人進行一番交易。
有跡象表明他對森林作了“充分利用”——木屋周圍方圓幾英畝的土地上,茂密的樹林被利斧砍伐一空,隻剩下光禿禿的樹樁,過了些許日子,腐爛的樹樁上長出了新的枝葉,將樹樁掩蔽了大半。顯而易見,這人用帶有缺損的火焰燃起了對農業的熱情,又在懺悔的灰燼中終止了這種熱情。
這小小的木屋,有個煙囪,它的屋頂是用彎曲的木板鋪壓在橫梁上,木板之間的縫隙用泥土塞得嚴嚴實實,木屋隻有一扇門,與門相對的牆上,開了一扇窗子。然而,窗子現在已被木板釘了起來——沒人會想起它什麼時候不是這副樣子,也沒人知道它為什麼會被木板釘得嚴實無縫,當然不是因為它的居住人不喜歡亮光和新鮮空氣的緣故,因為僅有的幾次,一個獵人路過這個孤寂的地方,這位遁世而居的人正如常人一樣在門邊曬著太陽,這時天堂恰好提供了他必需的陽光。我能想象得出,今天在世的幾乎沒有誰曾經打探到這扇窗子的秘密,但我就是一個,在下文敘述中你就會知道。
這人的名字據說叫麥羅克。他的相貌看上去有七十歲了,實際上隻有近五十歲的年紀,除了歲月的流逝,還有一隻無形之手加速了他的衰老。他披著一頭長發,耳鬢長著銀白色胡須,他灰色而近渾濁的雙眼深陷入眼眶,布滿皺紋的臉上,有一道奇異的傷痕,皺紋和傷痕如兩個體係在互相交錯。從體形上看,他高高的個子,顯得十分削瘦,勾肩駝背——像背負沉重的東西。我從未親眼見過他本人一麵,他的這些相貌特征,還是我孩提時代,我爺爺給我講述有關的故事時告訴我的。我爺爺在他活著時老早就認識他了。
有一天,麥羅克在他的小木屋裏被人發現時,他已經死了。那個時間,那個地點,沒有詳察的驗屍官們和蜂湧而來的記者,我認為他的死沒什麼異常因素,否則,爺爺就會告訴我,我也應該想得起來。我隻知道,憑我適當的直覺,他的遺體應當埋在離小木屋不遠的地方,與他妻子的墓挨在一起,他的妻子比他先死,這麼多年了,受本地條件的製約,我幾乎對他妻子的生活狀況無從知曉。這個真實的故事的最後章節就此結束了——隻是還有一點需要交待一下,在麥羅克死去了許多年後,我鼓起巨大的勇氣,艱難地穿過茂密的樹林,來到麥羅克生前隱居的這片土地,冒著相當大的勇氣走近廢棄的小木屋,朝它扔去了一塊石頭,馬上我就跑開了,以免有鬼突然出現——那附近每個生性活潑的小夥子都知道這個地點常常有鬼出沒。當這種傳聞自然而然地產生時,我對傳聞的細節並不太關注,倒是對引起鬧鬼傳聞的環境,產生了濃厚興趣。這個真實的故事還有前麵的一個章節——它是由我爺爺講述的。
麥羅克先生造好了他的小木屋後,他就堅決地將來福槍——他強大的支持手段擱置在一旁,手拿一把利斧去伐倒了一片樹木,開辟了一片農田——此時他還是位青年人,身體十分魁梧強壯,對生活充滿了希望。他來自東部的一個鄉村,他在那兒結了婚,妻子是位時髦的年輕姑娘,值得他全身心地去好好愛護,她心甘情願地和他分享各種各樣的危險,共渡著貧窮的日子。沒有關於她芳名的記載,對她溫柔可人的性情和容貌身材也沒留下任何描述,讓遐想者盡情遐想吧,但上帝卻在阻止這種遐想,我是多麼傷感失落啊!在他日複一日的獨身生活中,對他們愛情和幸福生活的回憶,該是他豐富的精神支柱吧。但是這種好似來自天堂般的回憶,是否倒成了他冒險勇氣的精神枷鎖呢?
某一天,麥羅克從森林中很遠的地方打獵回到家中,發現他妻子正發著高燒,神誌有點不清了。幾英裏內找不到一個醫生,既沒有一個鄰居,也沒有條件離開這兒去尋求幫助。他因此擔當起護士的職責,期待她早日康複,但到了第三天的深夜,她變得不省人事,就這樣離開了人世,沒有一點複活的跡象。
從我們聽說的有關他的秉性中,我們可以大膽地對我爺爺粗略講敘的情形,作出更細致的剖析。當確信妻子已經病故後,麥羅克強烈地意識到應該為亡妻準備葬禮了。為了履行這神聖的職責,他變得異常焦躁不安,卻又不知所措。平常對他來說十分簡單的動作,現在做起來卻一再失誤,他自己都覺得十分驚奇,就像一個喝得醉醺醺的酒鬼,到處遊蕩,已完全失卻了常態。他盡管十分震驚,但沒掉下一滴眼淚——震驚中自覺羞愧,麵對死者卻不哭泣,確實顯得十分冷酷。“到了明天,”他大聲說道。“我非得自己做口棺材,再挖好一個墓穴,從今以後,我會十分想念她的,我再也看不到活生生的她了,現在——她先走一步了,當然,沒有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應該沒什麼關係。事情並不像別人想象的那樣糟糕。”
他站在遺體旁,邊上閃著暗淡的火苗,他將她的頭發整理好,又簡單地給她梳洗打扮了一下,他的動作十分僵硬,好像已經魂不附體了。他從僅存的意識中,確信自己做得很對——他應該使她與生前沒什麼兩樣,這樣一切就無憾了。他從沒有經曆過悲傷的場麵,他對悲傷的容納能力因從未利用而一點也沒有增大,他的心胸既不能容納這一切,他的想象力也無從正確地觸及這一切。他不知道他受了如此重重的一擊,這些知識來遲了一步,但決不會再棄他而去了。悲傷是一位具有強烈感染力的藝術家,它用各種各樣的樂器為亡靈彈奏著挽歌,那些最猛烈的、尖銳刺耳的音符,被悲傷從最深處喚醒,低沉的、肅殺的和弦在心跳般悸動,如同遙遠的鼓聲,緩慢敲擊著。他整個身心都在顫栗著,知覺開始變得遲鈍麻木。妻子的突然病故,就像一支利箭,射向了他熱愛的生活,他的所有感覺都劇疼難忍,或者像遭到棍棒的狠命一擊,頓時昏死過去,毫無知覺。我們能夠想象得到麥羅克正處於上述的狀態之中,沒有比這種想象更值得確信的了,因為他剛對遺體履行完虔誠的整容手續,整個身軀就癱進桌邊的椅子裏,他妻子的遺體就擱置在這張桌子上,他的臉在深深的黑影中顯得無比蒼白,然後他將手臂擱在桌邊,將臉埋在上麵,欲哭無淚,有種說不出的疲倦。就在這一刻,通過打開的窗子,傳來長長的一聲悲鳴,就像在遙遠漆黑的森林中迷路的孩子的啼哭聲?但他一動沒動。這異乎尋常的啼哭聲又傳過來,顯得更近了,他似乎沒有聽到。或許,這啼哭聲來自於一隻野獸,或許它隻是一個夢,因為麥羅克睡著了。
幾個小時之後,啼哭聲再次響起時,不盡職的守屍者被驚醒了,他從手臂上抬起頭來,凝視傾聽——他弄不明白。在遺體旁邊的黑暗之中,他又恢複了知覺,不帶一點激動,他定神看看——他沒發現什麼異常。現在,他的所有感覺都在警戒之中,他屏住了呼吸他的血液好像為了協助這沉默而停止了流動。誰——什麼東西驚醒了他,它在哪兒?
突然,這桌子在他的手臂下搖晃起來,同時,他聽見,或者想像他聽見,一個輕輕的、柔軟的腳步聲——不同於啼哭的另一種聲音——赤腳走在地板上的聲音!
在可怕的力量之下,他驚恐得叫不出聲來,一動不動。他僵硬地等待著——在黑暗中等在那兒,就像一個人經曆了數個世紀的如此可怕情景,仍活著向你傾訴一切。他呼喚著亡妻的名字,他想朝前伸出雙手,在桌子上摸摸她是否還躺在那兒,可是,他的喉嚨無力發出聲音,他的手臂如同灌了鉛一般,難以聽從使喚。這時,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某個龐然大物朝著桌子用力猛撞將桌子狠狠地撞到了他的胸口,他一下被撞倒在地,同時他聽見和感覺到了某件東西轟地一聲重重落在地板上,整個小木屋立刻晃動了幾下,隨即一陣難以描述的雜亂不堪的響動。麥羅克掙紮著站立起來,恐怖已過度地剝奪了他的一身本領。他用手在桌子上亂抓一氣。桌上的屍體沒有了!
這是由恐怖膽怯變成大膽瘋狂的轉折點:大膽瘋狂即刻付諸行動。他幾乎沒多加思索,婦人多舛的命運令他衝動不已,麥羅克跳到牆邊,彈指之間就從牆上一把抓住了裝滿彈藥的獵槍,沒找目標就扣動了扳機。火光一閃,整個房間霎時被照亮了,他看見一頭身軀龐大的美洲豹正將死去的婦人拖向窗外,它的利齒咬住她的脖子。黑暗刹那間又降臨了,比原來黑得更加深邃。然後,一切歸於沉寂。
當他蘇醒過來時,太陽已高高掛在天上,森林中鳥兒在盡情歌唱。
婦人的遺體就躺在窗子邊上,那頭野獸在火光一閃的獵槍聲中,驚恐地丟下屍體逃掉了。她身上的衣服已被撕扯得稀亂,長長的頭發亂七八糟,四肢隨意攤在地上。她的咽喉被可怕地撕襲開來,一團血還沒有完全凝固。他係在她手腕上的絲帶已被撕破了,她的手攥緊了拳頭,牙齒之間是一片豹子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