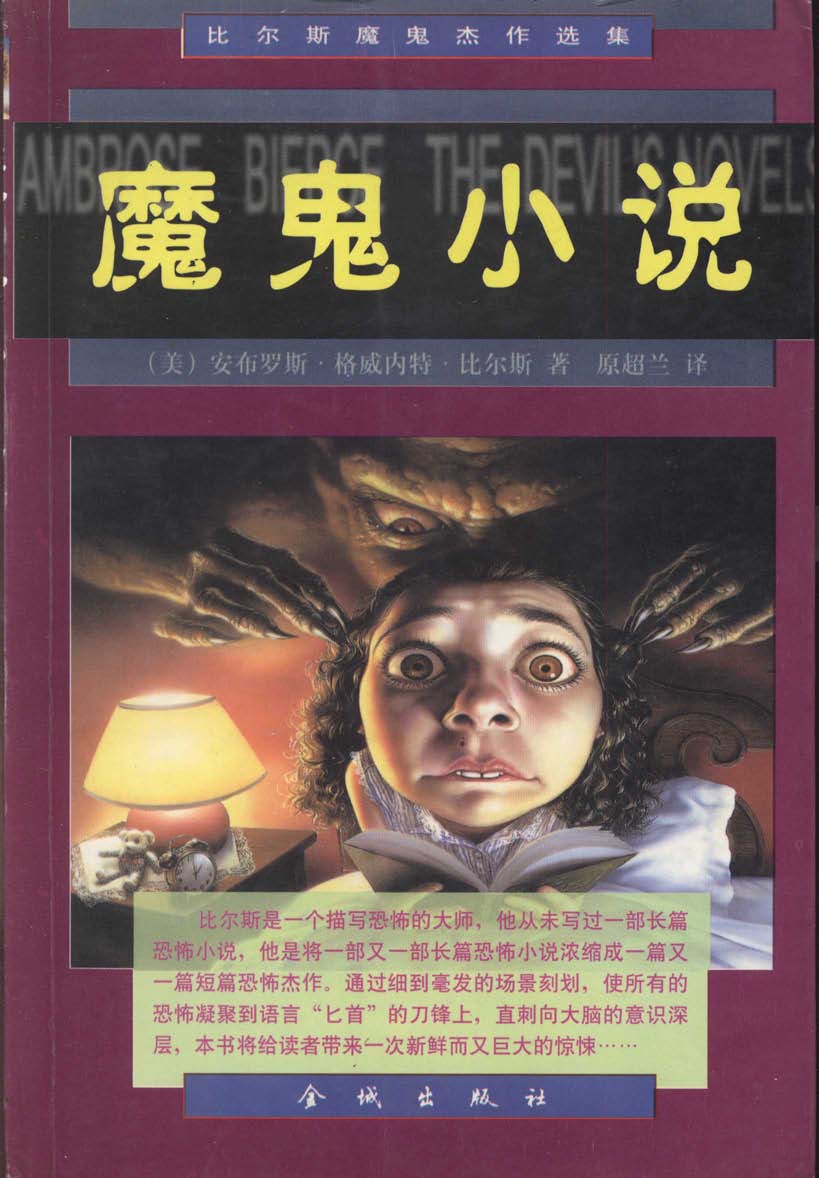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空屋裏的死亡賭注
一
在舊金山被稱為北灘的地區,一座空房子樓上的房間裏躺著一個死人,用床單覆蓋著,時間是晚上將近九點鐘,房間被一個蠟燭照射得有些模糊不清,盡管天氣很暖和,依照舊風俗應給死者通通風,但恰恰相反,兩個窗子都緊閉著,房內的家具隻包括了僅有的三件——一把扶手椅、一個擱著蠟燭台的小書架,一個廚房用的長桌,桌上躺著這一具男人的屍體,所有這些家俱也和這屍體一樣,看著像剛剛才搬進來似的,如果裏麵有人,將會看見這幾樣東西都一塵不染,與此相反,房裏其他樣樣東西都蒙著厚厚的灰塵,每個牆角裏盡是蜘蛛網。
在床單下這屍體的輪廓能凸現出來,甚至它的特征,這些都不太自然地顯得十分清晰,似乎最清晰的還是死者的臉麵,其他特征好像都因久病而被毀掉了。從這房間的寂靜,你可以準確推斷出它不在這棟房子麵街的前部,它真正的朝向隻是麵對著高高的山腹,這整座建築就依山而建。
當鄰近教堂的鐘聲敲了九下,它似乎意味著對時間的溜走漠不關心,以至於你幾乎不用去幫助想想為什麼時間確實給敲鐘帶來了麻煩。房內唯一的門開了,一個男人進來,徑直走向這屍體,這時這扇門悄悄關上了,顯然是門自己關上的,它發出刺耳的聲音就像鑰匙在開一把壞鎖,接著又是鎖舌落進鎖孔的聲音。一個輕輕離去的腳步聲在走道回響,很顯然,這個來人是個被囚禁者。來到這廚桌邊,他停了一會看看這具屍體,然後,輕輕地聳聳肩,走到一扇窗前,拉起百葉窗,室內很黑,窗玻璃都沾滿灰塵,但是擦亮一塊,他能看見外麵離窗玻璃幾寸處是很粗的鐵柵,鐵柵兩端牢牢嵌在牆裏。他又走過去看另一扇窗子,也同樣如此,他對這事沒有顯出太多的好奇,甚至沒有碰一下窗子,如果說他是個囚犯,也顯然是個性情溫馴的囚犯。四麵八方察看完這房間,他坐在扶手椅上,從口袋裏拿出一本書,拖過書架借著蠟光開始讀起來。
這人很年輕,決不超過三十歲,膚色黝黑,胡子刮得很幹淨,長著棕褐色頭發,他的臉上長著高高的鼻子,寬寬的前額,一個據說是顯示其“堅毅”的下巴,他的雙眼灰色,眼神堅定不移像在下最後的決心,現在他的雙眼更多的時間盯著書本,但不時轉過來瞧瞧這桌上的屍體。很顯然,在如此情形之下,從任何沉悶的迷戀中,誰都可想而知,與其說是鍛煉一個人的勇氣,不如說是,麵對著會主宰一個膽怯的人的影響進行反抗。他讀書時好像一些事物迫使他回到對這四周景物的感受中,很顯然這死者邊的守護者正履行著他的職責,憑他的智力和無比的鎮定,這些正適宜於他。
在讀了約半個小時後,他似乎讀到了最後一章,於是輕輕放下書,然後,他站起,把書架拖到靠窗的牆角邊,舉起書架上的蠟燭回到空空的壁爐前,坐在那兒,過了一會,他來到桌上的屍體邊,從頭前掀起床單,下麵露出一團黑發和一塊薄薄的蒙臉布,這人的特征比先前顯得更加分明。他用雙手遮住耀眼的燭光,站著凝視他一動不動的夥伴,以一種嚴肅和寧靜的神情,看夠之後,他拉下床單重新罩在這死者的臉上,回到扶手椅之前,從蠟台上拿起幾根火柴放進他粗布外衣的大口袋裏,才又坐下來,然後他舉起蠟燭鑒賞般地看著,好象計算著它究竟能燒多久,它僅隻2英寸長,再過一個小時他將陷入黑暗之中。他把蠟燭放回蠟台,幹脆將它吹滅了。
在柯尼大街的一個內科診所裏,三個人正坐在一張桌邊喝著潘趣酒,抽著煙。已經很晚了,幾乎是午夜了,不過潘趣酒一點都不缺。三人中最年長的,赫伯遜醫生,是這裏的主人,這是他的辦公室,他約莫三十開外,其餘二人都更年輕些,他們全都是醫生。
二
“這生者對死者的迷信的恐懼,”赫伯遜醫生說道,“是世代相傳,已經不可救藥。人們不應覺得對遺留下來的東西感到羞愧,比如說,天賦不行或者喜歡撒謊。
其他倆人都笑了起來。
“那麼一個人不必為撒謊而羞愧,是嗎?”三人中最年輕的問道,事實上,他還是一個未畢業的醫科大學生。
“我親愛的哈柏,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喜歡撒謊是一碼事,撒謊是另一碼事。”
“但你想想,”第三個人說道,“這迷信的感覺,對死人的恐懼,我們知道沒什麼理由,但具有普遍性嗎?我自身就沒有意識到這點。”
“噢,但這一點已浸透了你的全身,”赫伯遜重複道:“這隻需要適宜的條件——就是莎士比亞所說的同謀的季節,——它以某種令人討厭的方式出現,令你大開眼界。當然,醫生和士兵比其他人迷信意識要很少一點——”
“醫生和士兵——為什麼你不再加上絞刑吏和劊子手,讓我們來談談這個殺人階層。”
“不,我親愛的曼切,大陪審團不會讓這大眾劊子手獲得足夠的親近,因為殺人的緣故,他們被人們冷漠對待。”
年輕的哈柏,一直在餐具櫃邊吸著一支新鮮的雪茄,現在又回到原處,“那麼什麼才是你提出的這個條件呢,在這個條件下任何一個女人生出的男人都難堪地開始覺察到,他其實在這一點上分享了大家共同的嗜好或者弱點?”他反問道,顯得有點太囉嗦了點。
“那麼,我該這樣說——”赫伯遜答道,“如果一個人在整個深夜和一具屍體關在一起……孤單地……在一個黑房間裏……屬於一個空曠的房屋……屍體的頭沒有東西遮蓋……這人自始自終和屍體住在一起不會發瘋——他或許能自我吹噓說不是女人生的,但是沒有誰能夠做到。”
“我想你從來不會湊齊這些條件,”哈柏說道:“但我知道一個人,他既不是一個醫生也不是一個士兵,但他卻和他們一樣,和你隨便怎樣打賭都行。
“他是誰?”
“他名叫傑利特——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奇人,來自紐約我住的一個小鎮上,我沒有錢去和他打賭,但他打賭連性命都敢押上。”
“你是怎樣知道這些事情的?”
“他寧可挨餓也要賭錢,至於害怕,——我敢說他認為這是皮膚患有某種小毛病,或者也可能是一種特殊的異端邪說。”
“他看起來像誰?”赫伯遜顯然來了興趣。
“像曼切,真是湊巧——或許是他的雙胞胎兄弟。”
“我接受這個挑戰,”赫迫遜急不可待地說道, “我同意打賭。”
“感謝你的恭維,我確信你會同他一賭輸贏的。”
曼切在一旁慢吞吞地說道,他正感覺睡意襲來,“難道我不能參加嗎?”
“我不反對,”赫伯遜說,“我不會要你出錢。”
其他二人都笑了起來。
“好吧,”曼切說:“我來裝成屍體。”這個荒唐的會談結局如何我們已經在上一節裏看見了。
熄滅了配給他的貧乏的蠟燭,傑利特先生得把蠟燭放在身邊以應不測之需,他能全部想到,或者想到一半,這黑暗不會一次比另一次更糟,如果事情變得有些無奈,那麼這剩下的蠟燭將是一個擁有的更好的解決手段,無論如何,留下很少蠟燭是一個明智之舉,即使僅僅隻能使他看清手表。
他一吹滅了這蠟燭,把它擱在身邊的地板上,就舒服地背靠著扶手椅並合上雙眼,希望能漸漸入睡。他感到有些失望了,在平時他從不感到難以入睡,幾分鐘後,他放棄了入眠的嘗試,但他能做什麼?他不能在絕對的黑暗中摸索,冒著被撞傷的風險,否則會因疏忽被桌子撞上,無禮地打擾死者,我們都認識到死者應擁有休息的權利,如果廢除這權利,那將是苛刻而嚴厲的。傑利特幾乎成功地使他自己相信這種顧慮使他免遭挨撞的風險,而使他固定在扶手椅上。
當他想這些事情時,他隱約聽到一種模糊的聲音就從這桌子的方向發出,何種聲音他不能理解,他不能轉過他的頭,他為什麼要轉頭去看呢?他應與黑暗獨處,但他忍不住還是聆聽——他為什麼不聽聽呢,他聽得兩眼直冒金星,一把緊緊抓住椅子的扶手,他身邊有一種奇特的鐘聲,他的頭似乎在爆裂,他的胸部被衣服所束縛著,他很迷惑為什麼情況會變成這樣,是否這就是恐懼的征兆。突然,隨著一陣長長而強烈的呼氣,他的胸膛變得塌陷,伴隨著眩暈導致的肺部渴燥而大口喘息,他知道,這是因為聽得入迷而使自己幾乎窒息,這是煩惱的凸現,他站起來,用腳蹬開椅子,跨步走向房中間,但在黑暗中走不太遠,他開始摸索,摸到了牆,摸著牆到了牆角,轉彎,摸著牆過了兩扇窗子,在另一個牆角猛地觸到了書架,一下把它撞翻了,轟的一聲,他驚得跳了起來,他被弄煩了,咕嚕道:“我怎麼忘記了這是魔鬼呆的地方!”他摸索到了第三麵牆來到壁爐前,“我必須把東西重新放好。”傑利特說著,摸到了地板上的蠟燭。
拿起了蠟燭,他點燃了之後,立即轉過眼神去看桌子,很自然,那裏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書架不顯眼地倒在地板上,他忘記了去把它扶起來。他瞧瞧整個房間,更深的陰影被他手中的燭光所驅散,最後,他大步走到門邊,用盡全力拉轉門把手,但是門動也不動,這似乎帶給他某種滿意。確實,他還看見原先沒有看到的門閂,幹脆把它閂上了,這樣更保險些。然後他又回到扶手椅上,看看手表,指針才指向9點半鐘,他大吃一驚,把手表放在耳邊聽見奇怪的響動聲,聲響未停,蠟燭現在顯然又變短了,他又吹熄了它,象先前一樣把它擱在地板上。
傑利特一點也不自在,他顯然對環境不太滿意,對自己的狀況同樣不滿。“我究竟害怕什麼?”他思考著,“這太可笑太可恥了。我決不能成為一個十足的笨蛋!”但是膽量既不是說來就來!“我要有膽量!”也不能提供一個就有膽量的恰好時機,傑利特越是責備自己,責備自己的理由就越多,他想到的死人無害的簡單形式變化越多,他雜亂的頭緒就更加恐怖。“什麼!”他因極度的精神痛苦而喊出聲來, “什麼!對我來說,我天生就沒有迷信——對我來說,我就不相信靈魂不死——對我來說,我知道(從來沒有的現在)所謂死後的生命是一個希望的夢想——我竟然要馬上賭輸了,我的誠實,我的自尊心或者我的理性,都會統統輸掉,隻因為我們居住在洞穴之中的蠻荒時代的祖先,竟然會產生一種荒誕的想法,認為死人會在夜裏出現,走來走去嗎?……我……”
那麼——很顯然,沒有聽錯,傑利特先生聽到了他身後的輕輕的、柔和的腳步聲,不緊不慢,踢嗒踢嗒,連續不斷地越逼越近!
就在第二天的拂曉,赫伯遜先生和他年輕的朋友哈柏正駕駛著四輪雙排馬車慢慢地穿過街道。“你還對你朋友的膽量或沉著深信不疑嗎?”年長的說道:“你相信我輸掉了賭注嗎?”
“我肯定你已經輸定了,”另一個人說道,但也隻是低聲地強調著。
“那麼,憑心而論,我希望如此。”
話說得很真摯,幾乎一本正經,接著沉默了一會,“哈柏,”這個醫生又開始說道,在他們經過忽明忽暗的路燈時,他神情很嚴肅,“我對這次打賭並不感到很舒服。如果你的朋友對我懷疑他的忍受力——純粹的身體素質而采用輕蔑的態度,粗魯地建議要用一個醫生的屍體,因此使我大為惱火的話,我是決不會奉陪的,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就全完了,我害怕我們會自作自受。”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即使事情弄砸了——我一點也不害怕,——曼切僅僅隻需複活,解釋發生的一切,也就沒事了。又不是你的解剖室的屍體或者你哪一位死去的病人,如果是,那才麻煩呢。”
曼切醫生,那時,正如同他應承的一樣,他是這具“屍體”。
赫伯遜醫生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馬車不知不覺地在同一條街道慢慢行進了二個或三個來回,他立即說道:“好吧,我們希望曼切,如果他從屍桌上爬起來,但願他會謹慎地對待一切。一個小的過錯隻會使事情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那倒是的,”哈柏說道: “傑利特會殺了他。但是,醫生……”當馬車經過一盞路燈時他看看手表——“將近淩晨4點鐘了。”
一會兒之後,這兩人跳下馬車,輕快地向那醫生長長的空房子走去,那裏麵按照打賭的期限囚禁了傑利特先生。當他們接近時,他們遇見一個人正跑過來,“你能告訴我嗎?”那人喊道,突然放慢他的速度,“上哪去找個醫生?”
“有什麼要事?”赫伯遜含糊其辭地問道。
“你自己親自去看看吧。”這人說著又重新跑開了。
他們急忙朝前趕到了這房子前,他們看見幾個人正匆忙進入,神情很亢奮的樣子。
旁邊和對門的一些居民,將他們的臥室窗子推開,伸出頭好奇地觀看,所有人都在納悶,卻沒有問與之相關的問題。少數關著窗的房間也亮起了燈光,這些鄰居們都穿好衣服要下樓來。在這大家都關注的這座房子的門對麵,一盞路燈發著昏黃的光芒照亮這景象,似乎想盡可能多地泄露更多情節。哈柏,現在臉色死一樣蒼白,停立在門前,一隻手搭在同伴的手臂上,“一切都結束了,醫生!”他相當激動地說道,同他使用的簡單的詞句形成奇怪的對照,“與我們相關的遊戲已經結束了,我們不用進去了我隻想躲起來。”“我是個醫生,”赫伯遜醫生很鎮靜地說道,“這裏可能正需要醫生。”他們登上門口的台階打算進去,門是開著的,對麵的路燈照亮著進去的走道,裏麵擠滿了人,一些人站在更低的台階下進不去,隻有等機會再說。人們在互相談論,無人細聽。突然,上麵樓梯口發生了一陣騷動,一個人從樓上的一扇門裏跳出門外,正從竭力抓他的人身邊逃掉。他穿過一群驚恐的圍觀者衝下來,將他們推開,把他們撞倒在牆的一邊,又迫使他們緊貼住欄杆,掐住他們的脖子,殘酷地毆打他們,將他們推到樓梯下邊接著從倒地的人身上踏過。他衣衫不整,頭上沒戴帽子,他的眼神,狂躁不安,這流露的眼神比他明顯的超常力氣更加恐怖,他刮得光光的臉上,慘無血色,他的頭發蒼白如雪。
當這群人在樓梯的最下層時,有了較大的回旋餘地,他們閃開一邊讓他通過。哈柏跳上前去,“傑利特!傑利特!傑利特!”他大聲喊道,赫伯遜醫生抓住了他的衣領把他拽了回來,這人掃視了一下他們的臉龐裝作沒看見的樣子,衝出門口,衝下樓梯,消逝在大街上。
一個肥胖的警察挪動他自身比他征服樓梯稍微更成功點,緊跟在後開始追趕,伸出窗外的腦袋——特別是女人和孩子的腦袋現在帶頭尖叫起來。
樓梯現在比較空了,大多數人都擁到街上,去看這前逃後追的把戲,赫伯遜醫生於是上樓,哈柏緊隨其後,在樓上走廊的頭一扇門邊一個警官阻止他進入,“我們是醫生”這醫生說道,他們被準許進去了。
房間裏擠滿了人,看不清楚什麼,人們都擠在一張桌子邊,新來的二人側身擠進前麵,從站在第一排的人的肩頭上向下望去。
在桌子上麵,那死人的下半身被床單蓋住,一個警察站在屍體腳頭提著牛眼燈,燈光將這具男人的屍體照得亮堂,其他人,除了頭上的鼻子——連警察自己都在暗處,屍體的臉蠟黃,令人惡心,太恐怖了,眼睛半睜眼珠向上翻,下巴低垂,泡沫的痕跡弄臟了嘴唇、下巴和麵頰。一個高個男人,顯然是個醫生,正彎下腰把手伸進襯衫裏摸死人的胸口。他縮回手把二指放在張開的嘴邊說:“這人已經死了6個小時了,現在是驗屍官的事了。”他從口袋抽出一張名片,把它遞給警官,然後走向門外。
“打掃房間——出去,所有人。”警官叫道,聲音很嚴厲,他舉起牛眼燈對著人群的臉照來照去,那死人就象被抓走似的一下消失不見了。這效果令人驚異!這些人,失去了判斷,弄得迷糊,幾乎被嚇唬住了,騷亂起來向門口猛衝,人推人,人擠人,就象逃命一樣,在太陽出來前,他們是黑夜的主人。警官把光束傾瀉在這些互相擠壓、踐踏的一群人身上,沒有一絲憐憫。了解了現場情形,赫伯遜和哈柏出了房間奔下樓梯到了街上。
“我的上帝,醫生!我不是說過嗎,傑利特會殺了他?”哈柏從人群中分開馬上就說道。
“我相信你說過。”另一個人沒有什麼激情地說道。
他們默默無語地走著,一條街接著又一條街,麵對著越來越灰白的東方,那幢山腳邊的住宅顯出黑暗的輪廓,熟悉的牛奶車已經在街上走動,麵包師過不多久也會起床勞作了,送報人也同樣如此。
“年輕人,這情景觸動了我。”赫伯遜說道:“我和你已經呼吸了這早晨太多的空氣,這很有害健康,我們需要一個變化。我們為什麼不去歐洲一遊呢?”
“什麼時間?”
“我不太挑剔,我想今天下午4點就足夠早了。”
“我在船上同你碰麵。”哈柏說道。
七年後的某天,這兩人坐在紐約麥迪遜廣場的一條長凳上正親密交談,另一個人,不知什麼時候就在觀察他們,慢慢走過來,很有禮貌地從那蒼白如雪的頭發上脫帽致意道:“對不起,先生們,當您殺了一個人,而這人又複活了,最好的辦法是和他互換衣服,一有機會就溜之大吉。”哈柏和赫伯遜交換了一下會意的目光,他們顯然逗樂了,赫伯遜友善地看著這個陌生人,說道:
“那一直就是我的計劃,我完全讚同你關於它的——”
他突然停下來,臉色慘白,他直盯著這人,張大嘴巴,他顯然在渾身打顫。
“啊!”這個陌生人說:“我看得出來你不太舒服,醫生,如果你不能給自己看病,夏柏醫生可以為你幫點忙,我確信。”“你這魔鬼是誰?”哈柏愣愣地說。
這個人靠過來,彎下腰在他們耳邊輕輕說:“有時,我叫自己傑利特,但我不介意告訴你,為了老交情,我就是威廉·曼切。”
這個揭底差點使他倆癱倒在地。
“曼切,”他們倒吸一口涼氣,赫伯遜說道:“這是真的,我的上帝!”“是的,”這個陌生人說,曖昧地微笑著,“這是千真萬確的,一點不用懷疑。”他躊躇了一下,似乎想起什麼事情,然後開始哼唱著一支流行小曲,他顯然忘記了他們的存在。
“看著這裏,曼切,”年長的一個說道:“快告訴我們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對傑利特,你知道的。”
“噢,是的,關於傑利特,”對方插言道:“真奇怪,我竟會忘了告訴你們——我經常講起的。”
“你們想得到,通過偷聽他的自言自語,就知道他是相當害怕的,所以我不能忍受這複活的誘惑就去對他開個玩笑——我實在忍不住了。這本來沒什麼關係,卻一點也沒料到他會那麼當真。說實話,我完全沒有料到。後來,跟他調換衣服可是件棘手的活,後來——天哪!你們竟不讓我出去!”
他說最後二句話時樣子十分凶殘,這兩個人都驚呆了,“我們?——為什麼——為什麼——?”赫伯遜結結巴巴地說道,完全失去了自製力,“我們什麼也沒做。”
“難道我沒說你是赫伯和夏柏醫生嗎?”這個人神經質地笑了起來。
“我的名字是赫伯遜,是的,這位先生是哈柏。”他重新保證地說:“但我們現在不是醫生,我們是……嗯,忘了吧,老朋友,我們是賭徒。”
這倒是實話。
“一個非常好的職業——非常好,確實,順便說一下,我希望夏柏像誠實的賭金保管人那樣把傑利特輸掉的錢付清。誠實的賭金保管人,這是一個非常好而光榮的職業。”他關切地說道,無憂無慮地準備離開。
“但我對年長的順帶說一句:我現在是布魯明登精神病院的首席醫生,我的職責是專門治療領頭的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