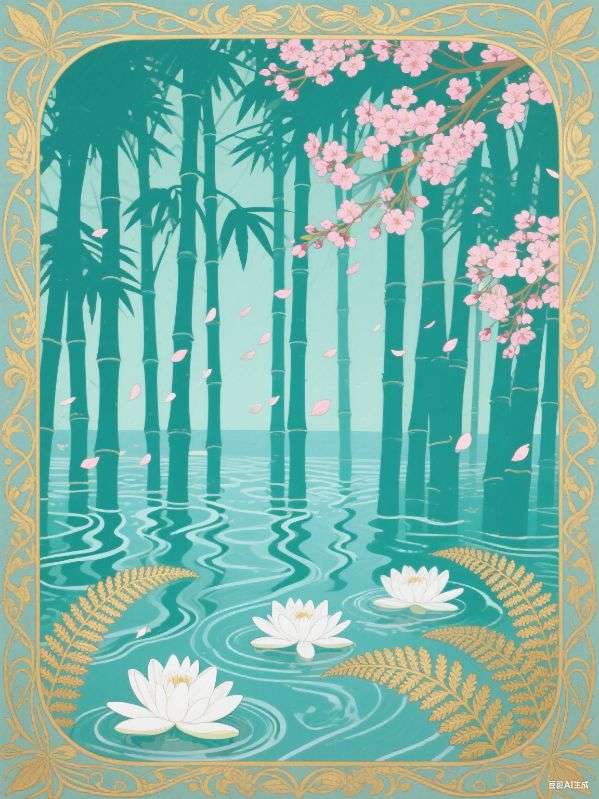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4章
接到秦菲電話的時候,我正在參加思思的幼兒園畢業典禮。
顧家原本想讓思思去那種一年學費上百萬的頂級國際幼兒園,但在我的堅持下,最後選了一家口碑不錯的公立幼兒園。
這是我嫁入顧家後,唯一一次明確向顧延洲提要求。看在我多年來安分守己的份上,他同意了,隻是提前跟園長打了招呼。
所以,思思雖然名義上隻是個普通家庭的孩子,但幼兒園的老師們對我總是有著格外的熱情和關照。
這和我最初的設想有些出入,但好在,脫離豪門的第一步,總算是邁出去了。
從我答應做顧延洲女人的那天起,我就知道,這場關係無關愛情,不過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這也意味著,它隨時都可能結束。
所以,我希望我和我的孩子在離開顧家之後,能夠從容地回歸普通人的生活。
但想和顧延洲離婚,並不容易。
在他對我徹底失去興趣之前,我不能主動撕破臉。這不僅關係到我穩定的經濟來源,更重要的是,顧延洲在海城的勢力,遠比外人看到的要深。
這些年,我親眼看著那些得罪過他的人,如何從風光無限變得一無所有。顧延洲能穩坐星雲科技的頭把交椅,不動聲色地掃除所有障礙,就足以證明,他絕不是一個沉迷美色的草包。
他挑選女人的眼光,也有一套固定的標準:聰明、識趣、知進退。
當然,偶爾也有例外。比如今天來我工作室逼宮的那位。總有些被物欲衝昏頭腦的小姑娘,天真地以為自己對顧延洲而言是與眾不同的,從而做出愚蠢的舉動。
「晚晚,老顧最近,好像迷上了一個新來的實習生。」秦菲在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平靜。作為跟在顧延洲身邊最久的女人之一,她很樂意向我提供一些「敵情」。
「是嗎?哪兒的?」
「就是你們海城大學的,大三,聽說成績很好,人也機靈漂亮......而且,跟你年輕的時候,有點像。」秦菲的語氣裏帶著幾分欲言又止。
「是嗎?那倒是有意思了。」
我的目光落在舞台上,思思穿著我用黑色垃圾袋和舊報紙做的「環保禮服」,正準備上台表演。我連忙從座位上站起來,激動地朝她揮手。
思思在台上看見我,酷酷地挑了下眉毛,算是回應。
「晚晚,我覺得老顧這次可能有點認真,你最好早做打算......我微信發了些照片給你。」
掛了電話,我沒急著看微信,而是打開相機,對著台上的女兒一頓狂拍。
等畢業典禮結束,我才慢悠悠地點開微信。
照片裏,顧延洲和一個年輕女孩手牽手走在校園裏,兩人穿著同款的白色T恤,笑得一臉燦爛。顧延洲的臉上,是我從未見過的、如同少年般青澀的笑容。
最讓我驚訝的是,那個女孩,除了發型不同,五官和神態竟與七年前的我有著七八分相似。
畢業典禮後,我帶思思去拍了一套寫真,作為她童年時代的紀念。
化妝的時候,我問思思,以後想不想換個城市生活。
思思是個非常敏感的孩子,她透過鏡子看著我,平靜地問:「媽媽,是我的生日願望要實現了嗎?」
「嗯,差不多吧,實現一半。」我歪著頭,想了想回答。
「媽媽去哪兒,我就去哪兒。」
那晚,等思思睡著後,我悄悄查了下自己的銀行賬戶。
結婚這些年,顧延洲雷打不動地每月給我轉八萬生活費。
最初照顧思思那幾年,我沒什麼額外收入,每個月能攢下五六萬。等思思上了幼兒園,我重拾舊業,開了這家小小的私人烘焙工作室,生意還不錯,現在每個月也能有三四萬的進賬。
顧延洲在過節和紀念日時也很大方,紅包和禮物從不吝嗇。
如今,結婚第七年,我的個人賬戶裏已經有了近四百萬的存款。
這對顧延洲來說,可能還不夠買一塊限量版的手表。但對我來說,這筆錢,足夠我和思思下半輩子衣食無憂。
這也是支撐我,戴了七年綠帽子,依然能保持情緒穩定的根本原因。
我知道,如果我能熬到顧延洲老去,我和思思或許能分到上百億的家產。但我更確定,思思不想要那樣的生活。
她就像一隻生活在堅硬外殼下的蝸牛,表麵上什麼都不在乎,內心卻柔軟又敏感。在她還很小的時候,也曾眼巴巴地渴望過父愛。但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過後,她徹底關上了那扇門。
想到這些,我總會感到一絲愧疚。
我曾經也幻想過,如果嫁給一個普通人,我的孩子是不是就能擁有一個完整而溫暖的家。
但秦菲一句話就點醒了我:「姐姐,你以為嫁個普通男人,他就不會缺席孩子的成長嗎?大多數男人,回到家就是個甩手掌櫃,攤在沙發上刷手機,你抱怨兩句,他就說自己掙錢養家多辛苦,反過來指責你不夠體貼,沒把家和孩子照顧好。」
當時,我看著她那張畫著精致妝容卻透著一絲疲憊的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或許這世上真有那種愛老婆愛孩子的好男人吧......隻是,我們這種人,注定遇不到。」
思緒回到現實,我打開了保險箱,把裏麵除了顧家祖傳的那枚戒指和手鐲之外的所有珠寶首飾,都拿了出來,準備找個時間處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