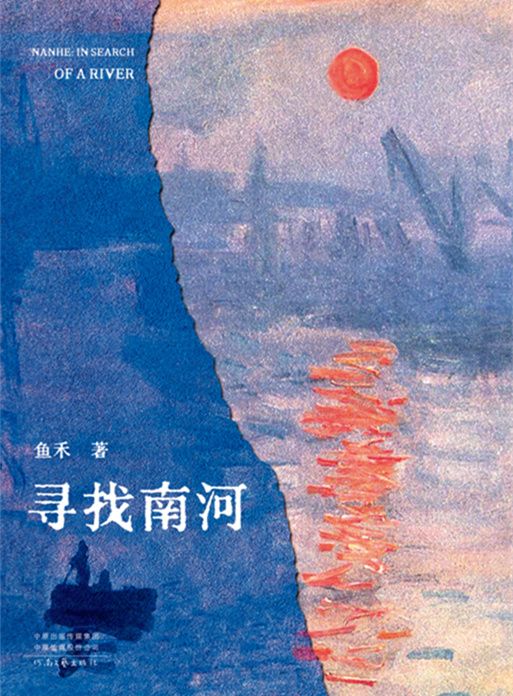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8
當梁奚一直掛在嘴邊的攀登雪峰成為一件對我而言再也不可能的事,當不得不說出“你自己去吧”的話,我正窩在沙發上進食。梁奚開始很驚訝,因為我很少說這種打退堂鼓的話。我又說,我爬不了山了,再爬腿就廢了。他看了一眼我正在揉著的膝蓋,無所事事地環顧四周,隻是搖了搖頭,仿佛是對我那句話的回答。
身體之內的漸變正在顯現它必然的形狀。身體變得沉重,又或並非更沉重,而是身體的“勢”改換了方向——它正在沉墜,與攀登反向。身體正在降落,它對所有的高飛便不再產生同情。這由衷的不認同,這對於當初的背叛,與骨肉的衰竭相伴生,完全不受意誌的左右。
沒有什麼比身體的局限更能讓人嘗到拘束於牢籠的滋味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我已經沒有氣力再跟從梁奚他們那樣的生活。準確地說那是一種“反生活”——在沒有目的地的長路上,在宿營地,在籌備中或者休整期,破釜沉舟,義無反顧,永遠不會消停。我不得不試圖和這副動不動就出故障的軀殼妥協。我摸著彎曲一下都會疼痛的左膝。我的確跟不上那些行動迅如疾風的“野人”了。
那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麵前這個野人也有屬於他的局限,我不知道某個海拔高度和氣溫刻度,將成為他的圍牆。那時的梁奚隻是搖頭,沒有說去還是不去,沒有說一個人去還是一群人去,更沒有說他要跑到自己的極限外麵去。
我曾對精神或靈魂之類的玄虛之物堅信不疑,以為人的判別力和意誌力即便不能穿透一切,至少也是可靠的盾甲,足以抵擋一切對於自我的侵襲。隻是,當身體在時間之中慢慢淪陷,那些被高舉的附著物竟也隨同沉落。毋庸置疑,人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和認識,人對他人的好惡,都在隨同身體轉變。橘生淮南則為枳。正在衰敗的身體之內,生長出來的是退守與防備。被我們企圖一分為二的東西原是榮枯一體。它們甚至不是同一個體的內外麵,而隻是我們對同一個體的不同稱呼。所謂精神或靈魂,就窩藏在體內的每一枚細胞之內,在肉眼不可見的分裂或收縮之中,猶如疼痛或饑餓,不是身體的衍生物,而是身體本身,是身體的枝葉上泛出的顏色。
人生到此,我才真的認清了那個被戴在我頭上的“勢強”。
那個亦貶亦褒的評語,從來就不是指稱我的力量,它指稱的是另一種東西,一種由身體的蓬勃旺盛而自然形成的膽氣和執意,一種由內而外的衝擊,一種澎湃不可阻擋的生長,猶如火山灰衝天而起,猶如洪水決堤而下,建設,也毀壞,澆灌,也淹沒。這箭在弦上的“勢”,從一個健康皮實的孩子身上生發而出,一定曾讓大人們暗暗感到某種含著醋意的歡喜,哦,這不知死活的孩子,好奇,生猛,什麼都想試試,什麼都敢招惹,磕破了頭也滿不在乎,嚇破了膽也咬牙不認。這讓他們的談論充滿了驚歎:哈,這孩子,歪著呢!
奔流浩蕩,泥沙俱下。那一往無前的猛勢終於在輾轉跌宕的長路上慢慢耗盡了力量。湖池澄淨,水草蔓延,魚蝦滋生。一個少年,一個混賬放肆的孩子,很快成為世事洞明的成人,再成為盤根錯節的老者。
說出告別的一刻牽腸掛肚。難以確知是什麼導致了他和我的不同,但梁奚的確和我不同。他依然混沌,流勢還在。很難想象這樣的人也會顫巍巍地手拄拐杖昏然老去。這奇異的氣勢令人迷戀又驚恐。而我終被自己的力竭所困。看著這個野人,我也有一種含著醋意的歡喜。那時我想起一位俄羅斯的詩人。她耀眼的才華也終被喂養身體的力竭所困。她說,肉體是一堵牆。最後,她親手推倒了那堵牆。
而與我們一起走過許多遠路、似乎無所不能的梁奚,他在海拔6753米、零下21攝氏度的雪山上推倒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