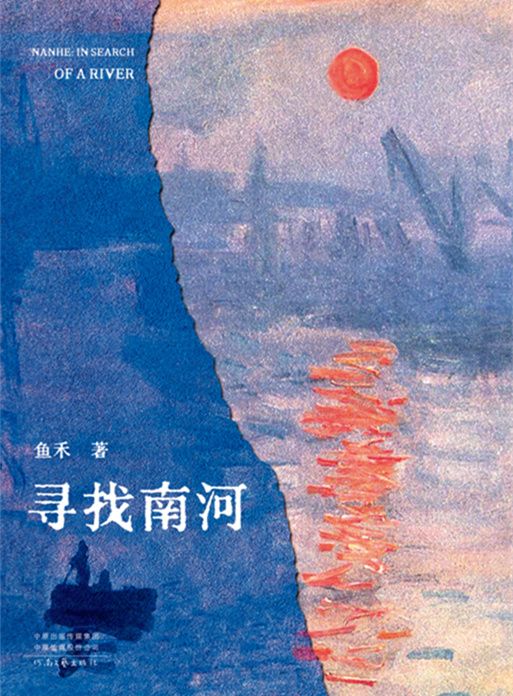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5
相片上的黑白小人兒已經變得模糊,醒目的唯有那兩道筆直上挑的濃眉。威儀棣棣。這個來自《詩經·邶風》的句子多年以前曾讓我心中驚喜。從知道它的含義時起,這句子便參與了我對自己的想象: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虛構中的這個人命勢強勁,靈智銳利,旁若無人,百毒不侵。但是這個人啊,她卻敗逃過許多次。
20世紀90年代,我曾經在一所高校從教七年。因為要求板書,而那所高校當時還沒有升降黑板,我必須穿著足夠高的高跟鞋才能對付。我不認為給大學生上課還需要板書,但當時沒有別的輔助,板書於課程大綱是規定。我個子太小,即便穿上高跟鞋我的手也夠不到黑板頂端。我隻得踮起腳,把第一行字寫得盡量靠上。90年代初的高跟鞋簡直就是刑具,細跟,尖頭,鞋底和鞋幫有一種冰質的冷硬。腳很累,太累,課時連續的時候它們酸脹得似乎隨時都會爆裂。筋骨的緊張從腳心一直蔓延到後腦,令人幾乎難以正常思考。我隻得向教務處申請,我的課程不要連排——腳踏刑具似的高跟鞋連續堅持兩個課時,對我而言已經達到忍受極限。
緊張還不止於此。每逢有課的前一天晚上,我都會反複檢查鬧鈴。上課遲到超過一分鐘,便是教學事故。而我太貪睡,容易睡過頭。所以要定兩遍鬧鈴。但是有一次,兩遍鬧鈴也沒有鬧醒我。我至今記得突然從深睡中驚醒蓬頭垢麵衝向教室的情形。那一次,我遲到了五十多秒。
更要命的是,我的秉性裏似乎有一種自我折磨的特質——對於正在做的事,我受不了一處不完美。我受不了自己的講述論據不確,受不了講述呆板或板書零亂,受不了我的課堂上有學生走神兒或露出絲毫的不耐煩。備課完成之後,我常常靠在沙發上,把幾個小時的課程默默“預演”一遍。
“預演”常常會在一些細枝末節處反複打轉,黏滯許久。沙發上的人閉目塞聽,心思專注,仿佛麵壁參禪。直到兩個課時的講解在“預演”中被打磨得渾圓平滑。
第二天,我在講台上一邊踱步一邊東拉西扯聊大天的樣子,騙過了許多人的眼睛。就連前去聽公開課的老教師也覺得我的狀態很放鬆,說,這貨在講台上大模大樣,跟個收租子的老地主似的。
事實上我隻是忍住從腳底蔓延上來的脹痛,把默默預演過的過場——那些層層疊疊的一二三四,那些銜接和轉換,那些典故,引述,以及為著逗樂的裝傻,又過了一遍而已。很好,我感覺到了,台下的每個人都被我帶著,沒有一個開小差。他們專注而且愜意。隨時會有人扔出問題。這些或呆傻或刁鑽的問題,都被我預料到了。
這外強中幹、自欺欺人的狀態弄得我苦不堪言。後來,當我突然提出離開高校跳槽到一家機關單位的時候,許多人大惑不解。高校收入尚可,穩定,清閑,被認為是最適合女人的職業。離開高校到一個並不顯赫的機關單位,貌似腦子進了水。誰也不知道,自幼以來偽裝的勢強,那硬撐的虛榮和難以言表的力竭,讓我有一種恐高般的致幻感。我需要的隻是想象中的機關工作的閑散——可以坐下來工作,不必穿刑具似的高跟鞋,不必連續幾個小時把自己擺在講台上被眾人注目,不必在上班前一天晚上反反複複預演,不會一不留神就釀成責任事故。就是這些幾乎不能構成理由的理由,讓我毫不猶豫地跳了槽。
所有的撐持和逃脫,都印證著看到相片的第一眼所獲得的直覺:我跟我的幻象。一組疊影。兩個互不認賬或互相抵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