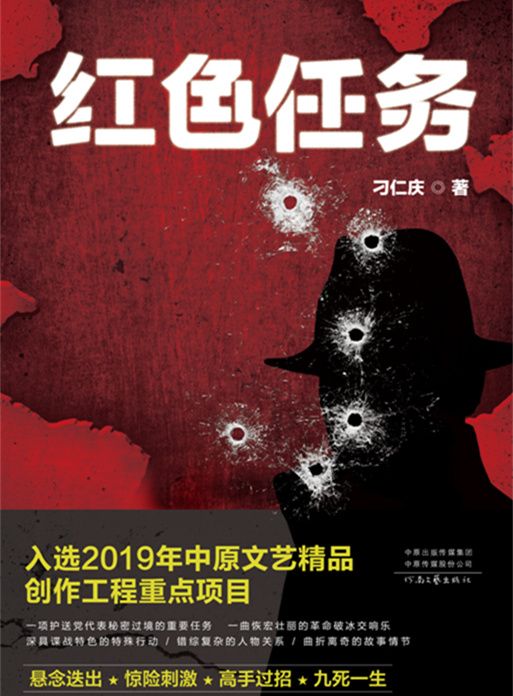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十一
1928年元旦過後,蔣介石複職了。元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致電在上海的蔣介石:“應即旋都複職,共竟革命全功。”元月4日下午,蔣介石乘火車由上海抵達南京。當晚,國民政府設宴歡迎蔣介石抵寧複職。蔣介石發表講話,希望大家精誠團結,完成北伐大業。同心協力,消滅異黨。元月7日,蔣介石通過媒體宣布正式複職,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
北京的張作霖聽說蔣介石回南京複職了,站在軍政府大門口的石級上,看著天上的太陽連打了五六個噴嚏說:“老蔣這個家夥回來肯定還要與我見高低的。來吧,我不怕!”
蔣介石複職後的心腹之患不是張作霖這個與他對抗的土皇帝,而是共產黨。消滅共產黨的各地組織機關是蔣介石的當務之急。從此,全國各地加緊了對共產黨的清剿。北京的軍政府事事與南京政府作對,但在剿共問題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小小的滿洲裏也不例外,到處都是剿共的聲音……
審訊室內,胡春江見到了被深魚出賣的共產黨人螞蚱——他已是個快死的人了。
胡春江被宣布任局座助理職務後,也沒什麼具體事兒,什麼案件也不讓他參與,什麼事兒也不讓他管,隻是讓他跟著局座羅高明應酬外邊的事兒。晚上沒事的時候,總務科長毛先征常常來到他宿舍嘮嗑,更多的時候是毛先征帶鮮羊肉來,用取暖的爐子燉,對飲解悶兒。
他的辦公室就在二樓東頭,隔牆就是他家持股的養馬場。白天沒事的時候,他隔窗看著養馬場發呆。他總有一種感覺,今後的工作會與這個養馬場有關。為啥有這種感覺,他自己也說不清。這些天,瞿華瑩老往他辦公室跑,他知道她來得多了不是什麼好事兒,他必須與她保持一定的距離。
今天中午,丁基元突然來他辦公室說:“走,到審訊室去,羅局座在等著你呢。”
當胡春江身著警服走進用地下室改造的審訊室時,他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鐵製十字架上,吊著一個雞骨支床的人,看樣子這個人已經不行了,渾身軟軟地掛在那裏,像風幹的大條牛肉。羅高明坐在一邊抽煙,胡春江進來時,羅高明看他一眼沒有說話。審訊室還有七八個人,都是丁基元的手下。十字架兩邊,站著兩個打手,一個人手裏拿一把長刀,一個人手裏拿一條皮鞭。十字架不遠處,有一盆炭火燒得正旺。炭火把一個人的臉烤得通紅,這個人就是副局座塗榮清。
胡春江走到羅高明麵前,問道:“局座,你找我?”
羅高明把頭抬起來,甩了甩煙屁股,說:“這個人隻承認自己是共黨,其他啥也不說,我們已經給他放出了話,隻要說出來一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就可以放他走,去英國、法國、日本等地都行,而且我們還為他保密。可是,他死活不說,每審訊一次,他都是大笑而結束。你是老刑警了,看看你有什麼辦法把他的嘴撬開。”
胡春江看了一下十字架上的人,形銷骨立,癡若木偶。他問:“他是誰?”
塗榮清說:“他就是深魚供出來的螞蚱。”
胡春江冷冷地笑了兩聲。這笑聲,讓塗榮清和丁基元他們背後涼涼的。通過他這陰冷的笑聲,他們感受到胡春江是有背景的人,水是很深的。
他說:“如果他真是共黨分子的話,這不足為奇。”說完,胡春江走到螞蚱麵前,隻見螞蚱鳩形鵠麵,無神而憔悴。他的右邊耳朵已經被割了去,黑紫色的大血塊如耳套一樣硬硬地貼在腦袋的右邊。鼻子尖也被割掉一塊,鼻梁腫得如胡蘿卜一樣。十個指頭的指甲早已被拔掉,兩隻手腫得如熊掌一樣,又黑又大。一條腿明顯是骨折了,無力垂下來。他穿一件灰土色的單衣服,用鐵鏈吊起的胳膊,也是腫得如小腿肚一樣。他的頭向前耷拉著,如一隻特大的茄子。他是昏迷了,還是死了,胡春江看不出來。看到這一切,他的心如刺進去一把鋼刀,疼痛得無法形容。此人受刑到如此地步,還能堅持,這種精誠貫日的精神和視死如歸的意誌,隻有在共產黨員身上才能體現出來。他想,眼前的情景,他可能也要麵對,求死容易,受刑難忍。他知道,他身邊的同誌,不少都受過大刑,但都挺了過來。比如金牙大媽,滿口好看的細牙,被敵人打掉的打掉,拔掉的拔掉。她的革命意誌使她挺了過來。過去,他很佩服金牙大媽,金牙大媽用大無畏的氣概征服了他。而此時,他更佩服眼前這位戰友,被敵人折磨成這樣,還是守口如瓶,視死如歸。他的心在流血……他心裏說,這位戰友,你是誰我不知道,但你為了誰,為了啥,我都知道。你受這麼大的苦,我卻不能把你從苦難中解救出來,心裏真是難受。想到這兒,胡春江突然意識到,這是羅高明在用審訊的辦法考驗他,那就是看他是否同情共黨,如果看出來他同情這個被審訊的螞蚱,那麼他們就會懷疑他是共黨的人。想到這兒,他走向前,用手輕輕地扇扇螞蚱那滿是幹血的臉,咬著牙說:“醒醒。”
那人真的有動靜了,睜開了他那細細的眼,向胡春江呈現出疾首蹙額的表情。一會兒,笑了,露出了黑紅的牙,這黑紅的東西,是血液。他的眼睛雖然很細,但從瞳孔裏射出來的凶光,直穿胡春江的心靈,並且在他的心靈中交換力量。螞蚱突然唱起來,唱的啥,嗚嗚啦啦聽不出來,肯定是振奮人心的歌曲。他滿嘴的血液噴了很遠。
胡春江等他唱完,問:“你想要什麼結果?”
那人用力地說:“死,有本事把我弄死。”
胡春江說:“那我不讓你死呢?”
那人說:“那不算本事。”
胡春江問:“難道,難道你為了你的什麼共產主義,真的什麼也不要了嗎?父母、妻子和孩子,都不要了?”
那人說:“讓我死吧,一群狗熊懂什麼?”
胡春江說:“我們這兒是天高皇帝遠的邊境線,用什麼刑隻有你知道,別人是不會知道的。再往下走,你不一定扛得住。到扛不住再說,不如現在招了。”
螞蚱說:“試試吧,對你們的種種酷刑,我都感興趣!”
這時羅高明向丁基元使了個眼色,丁基元會意。他轉過身,大聲地吼道:“他是疲馬不畏鞭,別讓他囉唆,剁他倆指頭!”
丁基元話音剛落,手拿大刀的大漢吼叫一聲,舉刀軋著螞蚱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兩個指頭被壓到十字架的鐵柱子上,劊子手猛地一用力,螞蚱的兩根指頭輕鬆地離開了手掌,叭叭兩聲,落在腳下的地麵上。鮮血如泉水一樣,噴了出來。螞蚱如木頭人一樣,無言語、無表情地懸在那裏在擺動。這時羅高明站起來說:“收了吧,把醫生叫來,包紮一下。”然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螞蚱的一聲吼叫,驚得羅高明一群人都停了一下,扭頭看著螞蚱,眼睛裏都充滿了難以言表的目光。然後他們個個無力地爬著樓梯走了。
螞蚱是這樣吼叫的,他大聲地說:“國民黨、北洋軍政府,最終沒有好下場!”
塗榮清用鐵鉗鉤了鉤爐火,也起身走了。丁基元帶著他的人也走了。
胡春江輕輕對螞蚱笑了笑,說:“我看還是招了吧。”螞蚱突然又大吼一聲:“狗!”說完,頭又耷拉了下來。留下的兩名年輕警察把他解下來,他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看守人員與醫生一起給螞蚱包紮。
胡春江表現得十分平靜,他知道,此時,有很多眼睛在盯著他,他必須得通過今天的考試。但是,他心裏怎能平靜呢?
胡春江雖然表現得很霸氣地走了,但他心裏還是亂亂的。
他回到宿舍,用被子蒙著頭,哭了。
他是來滿洲裏建特別交通站的,沒想到特別交通站沒有建起來,反而還要遭到這樣的心靈磨難。交通站怎麼建不知道,來什麼人不知道,但為了隱身,為了安全,必須得與魔鬼打交道,必須經受著各種折磨!他的心碎得如一塊巨石被炸開一樣。當年在武漢,生活那麼艱難,任務那麼艱巨,環境那麼凶險,他沒有感到為難和艱辛,反而鬥誌越來越旺盛。蔣介石和汪精衛叛變革命後,在那樣的白色恐怖中,有多少共產黨員因革命形勢低落而脫黨,甚至叛變和投敵,然而,他的信念和信仰一點也沒有動搖,反而義無反顧地參加了“紅隊”。在老南的領導下,在金牙大媽的帶領下,他和戰友們一起戰鬥,保衛黨中央的安全。那時他生活在黃浦江的船上,如蛟龍得水一樣,奔走在租界;如鳥兒投林一樣,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他們來無蹤、去無影的戰鬥狀態,讓國民黨、外國巡捕聞風喪膽。在上海工作和戰鬥期間,他們膽大心細而充滿激情。然而,到滿洲裏這些天來,他除有無助感外,心裏還充滿了焦慮和不安。他不適應這種鉤心鬥角的群體,他還不知道將來特別交通站在建站中會遇到何種困難,護送黨代表出境還會遇到何等的問題。母親不讓他主動聯係任何人,可是他的接頭人員為何還不出現,是誰,怎樣出現,他心裏沒有數。母親隻告訴了他接頭暗號,而且還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說,這個暗號隻能第一次接頭時用,過後作廢。
中午他沒有到食堂吃飯,而是喝點開水準備睡一會兒。他剛躺下,有人敲門,一聽是瞿華瑩的聲音。他真不想起床,但對這個女人又不能怠慢,隻好起來把門打開。
白皚皚的雪把他的眼睛照得難以睜開。隻見瞿華瑩雙手捧著一個保溫飯煲走了進來,她大聲地說:“中午為何不去吃飯,天這麼冷,不吃飯怎麼行呢?你又不是神仙!”
他接過飯煲,很自然地問:“是什麼?”她說:“是米飯,菜是蘿卜羊肉粉條。”他笑了,說:“原來今天中午是這麼好的飯呀,早知道是我最愛吃的飯,我不躲在宿舍吃烤地瓜了。”瞿華瑩把兩眼睜得大大地說:“咱局夥上能有這麼好的飯?這是我今天中午精心給你做的好不好!”胡春江一聽忙驚慌地說:“哎呀,是你特意給我做的?謝謝,謝謝了!”這時她看見他的烤爐上,還放了兩個剩餘的地瓜,這是昨天晚上他吃剩下的。今天中午他什麼也沒有吃,隻喝了兩杯開水。
瞿華瑩說:“吃飯吧,熱著呢。”
胡春江說:“其實我吃飽了,不想吃了。”
“胡說,你根本就沒吃!”她大聲地說。
他心裏一驚,看著她那紅紅的臉蛋問:“你憑啥說我沒吃?”
她詭異地一笑說:“你還是搞刑事偵查專業的呢,這點小伎倆能騙了我?進這屋一聞味道,就知道你吃沒吃。如果你吃了白薯,這室內的白薯味兒三個小時是不會散去的。你自己聞聞,現在還有味沒有?昨晚吃的白薯,現在還會有味?臭襪子味吧!”
胡春江被她這麼一說,沒話了。他不得不承認瞿華瑩的厲害,這種聞味法,的確是刑事偵查學的一種技法,沒想到她能用到生活的細節中。他笑了一下說:“我中午胃寒,不想吃飯,想休息休息。”她說:“吃了吧,我今天中午給你做的米飯很香,羊肉也很鮮嫩,粉條是地瓜粉,很筋道,吃了正好可以暖胃。”
沒有辦法,胡春江隻好吃了。
瞿華瑩坐在爐子邊,把雙手伸向爐子上方,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全警察局有女警十幾名,其他都是一般警察,分散在機關各個部門工作,隻有她一個人在中層當頭頭兒。她的背景很明確,就是汪主席的線人,主要是暗暗監督要害部門的履職情況。背地裏很多人都稱她是女特務。明裏她是項世成的副科長,但實際她根本沒有把項世成放在眼裏。人人都怕項世成那獵鷹一樣的眼神,但她不怕。她的姿色打動了項世成,項世成想把她攬入懷抱,然而,瞿華瑩不是一般的女人,她不去討好項世成,反而時時處處把項世成弄得很尷尬。瞿華瑩與羅高明關係似乎不一般,明裏看沒有什麼,但暗地裏一定是很密切的。憑胡春江的敏感性,斷定他們的密切關係絕對不是純私人感情,而是私情攪著公事兒,並且相互利用。他報到的第一天,就見瞿華瑩與羅高明在辦公室單獨說事兒。還有那天上午,瞿華瑩在他宿舍說了句“從今以後,局座會步步離不開你的”。後來他隨羅高明去古爾多那兒吃火鍋,在車上,羅高明就對他講,決定讓他當局座助理。這些事羅高明可能提前與瞿華瑩溝通過。
瞿華瑩突然把話題一轉問:“你妻子為何不來這兒和你一起生活呢?”
胡春江說:“哈爾濱是大城市,她不想來這兒的邊防小鎮。再說了,我嶽父家有事業需要她去做。”
她問:“聽說你嶽父家產業不小啊!”
他說:“不大,做些商業生意而已。”
她問:“你妻子叫什麼名字?”
他笑道:“怎麼,是查戶口呢,還是審查我呢?”
她也笑道:“嘮嗑嘛,隨便問問,你何必那麼敏感呢?”
他說:“她叫井黎黎,有機會她會來的。”
她說:“好,歡迎她來,我在這兒沒個伴兒,她一旦來了也有個說話的人。”
他哈哈一笑說:“你不是說羅局座老婆很寂寞嗎?你不與她接觸?”
她身子往前傾一下,晃晃脖子說:“看見那個娘兒們,身子起雞皮疙瘩。”
胡春江突然問:“深魚被擊斃案偵破了嗎?”
她說:“你是局座助理,你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呢?”
他搖搖頭說:“我這個助理你還不知道?我到目前還不被別人信任,案件更不會讓我知道了。”
她問:“不信任你還讓你去審問共黨分子?”
他說:“那隻是讓我熟悉業務而已。”停了一下他又說:“我隻是問問深魚被殺的案件進度,你不便說也就算了。”
瞿華瑩沉思一會兒說:“不是他們不想讓你知道案件進度,也不是我不便說,是他們不敢對你說。”
他知道了,他們目前真的把他當成為日本做事的人了。他暗暗地高興起來,隻有他們把他當成日本人的內線、特工、臥底,他才安全,才能順利地建立特別交通站。
瞿華瑩說:“我才不管你是什麼人,我該說的還是要說。深魚的死,肯定是共產黨派人幹的,凶手他們永遠是抓不到的。”
胡春江問:“為啥?”
她說:“那些人都藏在蘇聯,有任務了他們潛伏回來;沒有任務了,他們又蟄伏回蘇聯去,你往哪兒抓他們去?”
一會兒,她站起來,伸了一下懶腰,打了個哈欠,說:“我也困了,回去休息一下,你也午休吧。”說完,她頭也不回地拉開門走了。
下午胡春江剛到辦公室,傳達室老趙就把幾份報紙送過來了。他一張一張地仔細看。現在,胡春江已經養成了習慣,隻要來報紙,不管是什麼報紙,他都要從頭到最後看完,一個字也不落下。特別是廣告,他都一個一個地看完,母親沒有給他說接頭的辦法,但他猜想,通知他接頭的唯一辦法可能就是報紙上的廣告。
突然,胡春江的心大跳起來,他在一張《鬆花江晨報》的第四版最下邊,看到了一份尋人啟事。這時,他想到了在哈爾濱家裏,那個報童給他送的就是《鬆花江晨報》。他忙把門反鎖好,認真看了看,是寫給他的暗語,意思是讓他從今天起關注蘇聯海關門前廣場上的尋人啟事。他懸著的一顆心終於落地了,他深深知道,接頭人馬上就要來了。
吃完晚飯,胡春江換上便裝,把手槍掛在腰間,戴上厚厚的棉帽,穿上黑色的皮衣,衣冠楚楚地下樓向大門口走去。本來,他想明天上街去看尋人啟事,但現在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想去蘇聯海關廣場轉一轉。這時,有十幾名特別行動隊的便衣匆匆忙忙地從他身邊走過,他們向他打了個招呼,快速地走了。他問一個便衣:“晚上還有行動?”這個便衣是個年輕人,忙說:“有新的跟蹤任務,我們得上崗去。”胡春江說:“天這麼冷,你們辛苦了。”
胡春江慢悠悠地向前走著,當他快走到大門口時,他的身後突然有人喊道:“胡局助,等等我!”他一聽,知道是瞿華瑩。他馬上收住腳步,轉過身,隻見瞿華瑩穿得厚厚的站在了他的身後。
“晚上你一個人出去幹啥?”她問他。
他說:“寂寞,沒事幹,想出去轉悠轉悠。”
瞿華瑩笑道:“我也寂寞,我也沒事幹,我也想出去轉悠轉悠。”
胡春江哈哈一笑,說:“那一塊走走吧,男女搭配,走路不累!”
她說:“走,看看咱滿洲裏的雪夜。”他倆一起向大門外走去。
這時胡春江判斷,他一來到這裏就受到這個女人的關愛絕對不是她有愛心,而是她受人指使在跟蹤他,控製他,監視他。受誰指使,當然是羅高明。
瞿華瑩他倆並肩走著。她給他介紹著馬路兩側的建築和機關。不知不覺,他倆來到了蘇聯海關小小的廣場上。
廣場上冷冷清清,鋪滿了臟臟的積雪。廣場四周有幾個路燈,路燈杆上,貼滿了廣告。胡春江隻能用餘光看那些廣告,他不敢直麵去瞧,他知道,自己如果有一個小小的失誤,就會給他帶來諸多的不安全因素,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事小,黨的利益事大。他漫無邊際地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慢悠悠地走著。
前邊有個廁所。胡春江靈機一動,他說:“我去一下廁所。”
瞿華瑩聳了聳肩,說:“去吧!”廣場在黑暗中,像睡著了一樣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