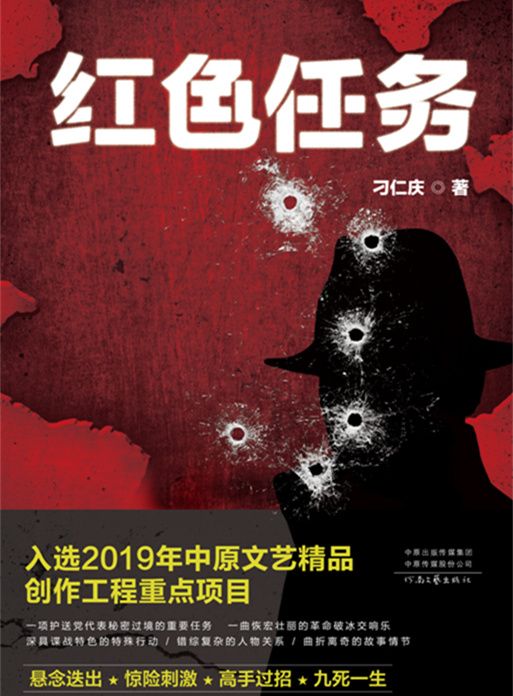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九
第三天,天陰沉沉的,從北方吹過來的冷風,含著西伯利亞泥土的獨特味道,瘋狂地掃過滿洲裏的大地,向南奔去。天大亮的時候,綠豆大小的雪粒從天上蹦了下來,落在了大街上、房屋上和廣闊的原野上。這些雪粒打在人們的臉上,疼疼的。
羅高明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俄國製造的小吉普。這種汽車的特點是底盤高,馬力大,四輪驅動,在雪地上跑很穩重。弱點是不保溫,坐在車內與坐在車外一樣冷。上午十點多,羅高明從他那深綠色的吉普上下來時,雪粒裏邊已經開始夾雜有雪花。一列火車拉著貨物從西北方的黑雲中衝出來,吼吐白煙,向這兒駛來。
羅高明在外邊辦事回來,剛到辦公室,有人敲門。進來的是總務科長毛先征。他進來後,找到羅高明辦公桌上的保溫杯子,給他倒了一杯開水。辦公室早已是爐旺室暖,舒適而溫馨。羅高明把黑色的皮大衣脫下,用雙手抱住保溫杯,輕輕地喝了兩口,然後抬眼看一下毛先征,問:“你看給新來的胡安排個啥職位?”毛先征在給一盆君子蘭澆水,聽局座這麼問,他放下水壺,想了想說:“這個胡是北京市警察廳派下來的,我們應該重視。他又是你的日本朋友推薦來的,還在日本上過警官學校,在關內又任過職,我們更得用心對待。我們這個地方,大家都想離開,到大城市去,到關內去,而他卻來這兒效力,僅憑這一點,他的職務不能太低。”
羅高明說:“他來我們這兒,肯定是有目的。他來幹什麼呢?”
毛先征說:“他打的是日本牌,你說他會幹什麼呢?日本人現在在打咱東北的主意,將來有可能打咱整個中國的主意,他們不從基層著手,能從哪兒著手呢?”
羅高明想了想說:“他打日本牌並不可怕,我怕他打日本牌幹其他事兒!”
毛先征愣了一下,問:“你怕他姓共?”
羅高明歎道:“是啊,我不怕他姓日、姓蔣、姓汪、姓張,我就怕他姓共。”
毛先征嚴肅地問:“他如果真姓共怎麼辦?”
羅高明沉思了半天,又喝了兩口白開水,站起來走了幾步,說:“深魚死了,深魚供出來的這個螞蚱已經承認自己是共黨分子了,但除此之外,什麼也不說。幾種大刑都用了,還是不說。共黨都是能吃刑罰的,但我沒有見過這麼能吃刑罰的。”
毛先征想想說:“如果你對胡不放心,隨後你可安排讓胡去看守所會會這個螞蚱,看他是什麼反應。”
羅高明點了點頭,說:“隨後吧,現在先把他的職務安排了再說,你說,給他安排什麼職務呢?”
毛先征想了想說:“職務安排小了不服眾,安排高了眾不服。他是二級警司,得找個適當的活兒給他。我感到姓胡的有內涵,不一般,可以考慮給他個局座助理職務。”
羅高明點了點頭說:“那就給他個局座助理吧,什麼事都可管,什麼事都不可管。名次排在兩名副局座之後,眾科長之前。”
毛先征笑了笑說:“我看合適。”
羅高明在辦公室轉了幾圈,回到辦公桌前坐下說:“你別看我們這個地方的潭小,但是所臥的龍一個比一個大呀。我現在是刀尖上跳舞,火爐子上睡覺,難受呀。要不是我身後背靠張大帥,也不知道會是一個什麼下場呢。”
毛先征把身下的椅子往前移了移,低聲說:“我有些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羅高明把手揮一下說:“你跟我還說這些話?講!”
毛先征喝口水潤潤嗓子說:“局座,你要先看形勢走向,其次是要權衡利弊,最後才是盡職盡責呀。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羅高明問:“什麼目的?”毛先征把聲音壓低說:“保身!孫大總統去世後,北洋政府三天兩變,蔣司令移官換羽,前景還不明朗。汪主席今興明滅,似乎還沒有掌握著大局的主動權。張大帥靠實力穩坐北京城,但南方各路軍閥均不服氣,跟隨蔣介石討伐張大帥。今後誰勝誰負、誰死誰生,還說不準。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唯有保身是上策。”
羅高明閉了閉眼睛,點了點頭。
毛先征接著解釋說:“目前我們國家亂成這個樣子,如果自己不保護自己,那一切都無從談起。一是先看形勢。現在是什麼形勢?現在是國家權力割據,南京、北京爭相稱霸,戰火不斷。我個人認為,將來國家大約有六個走向,哪家勝出,都是未知數。”羅高明忙問:“哪六種走向?”毛先征停頓了一下,說:“一、蔣總司令看似政由己出,革故鼎新,以武統國,掌握全局,其實不然。各地軍閥植黨營私,各自為政,暗流湧動,各行其是。明著擁蔣,暗地裏倒蔣,如咱北京的張大帥,蔣就沒辦法,蔣拉他,拉不動;蔣打他,他不怕。他不但不聽蔣的,而且要把蔣拉下馬,永世不得翻身。國內好多地方事務,也都不聽蔣的。二、汪主席與蔣介石各不相謀,除了他反共誌向與蔣總司令是一致的外,其他事都與蔣反其道而行之,這不,現在汪主席不是撂挑子跑到法國躲清閑去了嗎?我看他將來一定會靠外來勢力與蔣作對,從而吃掉蔣。三、北京的軍政府號稱是合法政府,但就看目前情況,北京對抗不了南京,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央軍比張大帥領導的安國軍強大,安國軍早晚要歸順老蔣的中央軍。現在上層是一蛇兩首,誰主沉浮還不一定。四、日本已經不甘心在小島上生存,他們早已把目光盯住中國,他們目前不是已經開始登陸山東和東北的沿海城市了嗎?將來能不能蛇吞象還說不定。目前東北全境危在旦夕,我估計用不了多久,東北就會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東北歸日,我們這個小小警察局能不聽日本人的?五、各地軍閥還在爭權,北伐已進入尾聲,且無後勁,名曰禁暴誅亂,實則走走過場。六、共產黨是明敗暗強……”
聽到這兒,羅高明把頭抬起來,雙眼迷茫了一下,問:“明敗暗強?怎麼講?”
毛先征把身子往前伸了伸,說:“雖然蔣、汪、張三人都開了殺戒,共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失,但是,蔣、汪、張三人反水以前,共產黨手裏是沒有軍隊的,現在蔣、汪、張一變臉,把共產黨驚醒了,共產黨開始反思,總結教訓,於是有了南昌兵變,有了廣州造反。我認為,現在是共產黨明裏失敗了,但暗地裏骨頭更硬了。因此中國的六大走向,誰勝誰負,難料。不管哪方勝出,我們都得跟人家走,所以我們做啥事都要留下後路。否則,河決魚爛,我們就是那魚。大水過後,河還是河,而魚呢?易學上講,想把腳下前進的道路留寬,必須把身後的道路留足。留後路,是現在精英們的最佳選擇。”
羅高明用異樣的目光看著毛先征,說:“你分析得很對,不管誰得天下,我們隻是一條狗而已。”
毛先征繼續說:“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既要悟透生活,又要生活糊塗。俗話說,清水不養魚,難得糊塗好。你說得對,我們隻是條狗而已,但是,我們不能真當狗,因為狗除盲目地忠於主子外,沒有思想和智慧。我們要裝狗,忠誠有度,守護有方,決不盲目。要想留後路,就得裝糊塗。裝糊塗的核心就是悟透不說透,真明白,假糊塗。現在在我們這個小鎮,各路勢力角逐,明爭暗鬥,你死我活。有些事情,堅決不能太認真。黨國是虛的,咱一家老小的性命才是實的。馬上要春節了,有些事情該鬆的要鬆一鬆,不管是哪路神仙,都讓他們好好過過年,歡樂一下,喜慶喜慶。現在的事情,你不管他,就沒有事兒。你管得太緊,事就來了。物極必反,這是真理。”
羅高明喝了一口水,眉毛擰成了一個疙瘩。他沉默地坐在辦公桌前一動不動。
毛先征說:“我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要權衡利弊。現在這個社會,皆為利來,皆為利往,沒利的事情人們是堅決不能做。萬事皆規律,社會如此,我們這警察局是個小社會,也是如此。利益有兩種,一是我們個人自己的利益,二是某個集團上下大夥兒的利益。其他都是假的,虛的。蔣司令、汪主席和張大帥都想囊括四海、包舉宇內讓我們戡亂,但戡亂弊太大,利太小,我們要謹慎。”
羅高明歎了一口氣,說:“老弟你說得對啊,我手下這些精英,各有背景,各有其主。剛來這個胡,絕對不是善茬兒。”
毛先征繼續往下說道:“我說的第三件事是盡職盡責。我看我們的人都很盡職,不管是刑事偵查、治安管理,還是情報獲取等,做得都很好。我們滿洲裏,北靠蘇聯,各色人員出出進進,都從我們這兒過,你不盡職不行,但做得太死也不行。河裏的水不管怎麼小,你不讓流是不可能的。我們在盡職時隻要睜眼合眼相兼就行。我們看不見的東西堅決不要搶著去看,看得見的,要摸透根源,權衡利弊,再做決斷。”
羅高明想了想說:“當下,我們的工作怎樣開展?深魚曾經給我們提供一個情報,說共黨過完年可能有大批人員從我們這兒過境到蘇聯開會,雖然他這個情報不能全信,但我想不可不信。”
毛先征問:“深魚提供得詳細嗎?”
羅高明搖搖頭說:“不詳細,他也是知道個大概。”
毛先征說:“我認為,你知道就行了,裝在心裏。這件事,我們堅決不能擅自行動,要等上峰指示。沒有上峰發話,我們自己做主,師出無名不說,主要還是自找麻煩。共黨隻要不在咱們轄區殺人放火,他們出境,那是東北軍的事兒。他們出多少人進多少人,那隻是過境,與我們無關。”
羅高明笑了笑說:“是啊,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層呢?”毛先征說:“如果上邊不發話來,深魚也已經死了,他提供的信息也無從查起,從此不再提這事兒。”
羅高明說:“這個螞蚱已承認自己是共黨分子,但他拒絕交代一切,怎麼辦?”
毛先征說:“我看先放一放,過完年再說,如果他真的是共黨的重要分子,哈爾濱方麵的人會感興趣的,他們有辦法。如果是一般共黨分子,先關起來,以後再說。”
羅高明深吸一口氣,濃濃的眉毛一展說:“你看問題高瞻遠矚,分析問題鞭辟入裏。你不但是我的好助手,更是我的好朋友啊。”毛先征高興地說:“局座您過獎了,我這都是皮相之見,是說一些感受而已。”
這時,外邊有人敲門。進來的是特務行動隊長葉自文和特情科長項世成。毛先征見他倆進來,忙起身對羅高明說:“今冬的冬裝庫存不夠,你還得向上峰打報告要錢,不少弟兄的大衣舊得不能再穿了,再穿有損我們警察局的形象。另外,幾個士紳捐的錢還沒有到位,你還得出麵催催。”羅高明說:“今天一上班我就坐車去了商會,會長說年底了銀行盤賬,盤完賬馬上把錢打過來。”毛先征停了一會兒說:“如果不行了得給他們點壓力,現在的有錢人,你給他笑臉不行,給笑臉了他認為你是在求他們。你得給他們壓力,一旦你給壓力了,他們就會認為他欠你的。”羅高明點了一支煙,深深地吸上一口,用力把煙霧從鼻孔裏逼出來,藍藍的煙霧嫋嫋升起,在他麵前形成一個霧簾。他似乎在想什麼重要的事情,心不在焉地說:“過完春節再說吧,年內堅持一下。過完春節不行了找個典型辦他們的案!現在的人啊,都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毛先征微微笑了一下,轉身走了。
葉自文和項世成站在羅高明的辦公桌前,羅高明又吸了一口煙,問:“跟蹤得怎麼樣了?”
葉自文說:“昨天晚上被跟蹤的人去日本領事館了,到現在還沒有出來。”
羅高明一驚,問:“是日本人?”
項世成說:“不像,但出進日本領事館很自如。”
羅高明把煙屁股一甩,說:“那算了,我們不問日本人的事兒。不是我怕他們,是我煩他們!”
“這……”葉自文似乎有些不忍。
羅高明馬上提高聲音說:“咱張大帥還懼讓日本人三分呢,蔣介石不也看著日本人的臉辦事兒?他這次下野不是哪兒也沒有去,唯獨到日本求和去了嗎?汪主席見日本人像親人一樣,不是天天喊中日友善嗎?我們一個小小警察局,搭理人家日本人幹啥?把人撤了吧。”
“是!”倆人同時回答。
項世成笑了笑,試探著問:“深魚被殺一案,進展如何?”
羅高明邊整理桌上的文件邊說:“已經交給丁基元他們破去了,還沒什麼進展。”
葉自文說:“這還用說,肯定是共產黨派人殺的。”
羅高明沒有理會葉自文,而是看著項世成的雙眼問:“今天上午下雪了,是不是很冷啊!”
葉自文和項世成兩個人都知道局座的意思了,忙說:“那我們走了。”
當他倆走到門口時,羅高明突然對他們說:“那啥——”他倆一聽忙轉過身來看著羅高明。羅高明說:“螞蚱不是已經承認自己是共黨分子了嗎?既然承認了就告一段落了,不要再審了。等我向上峰彙報後再說,先關押著吧。”
他倆又是同時說:“是!”
室外的雪越下越大,中午時分,風停了,雪沒有停。胡春江的宿舍是兩間房子,在警察局後院東南角的二樓上,門朝西。站在他的後窗戶前,正好能看見有他家持股的養馬場。這個“北國草原之夏養馬場”,現在是誰在管理經營,他不知道,也不能擅自去打聽,這是紀律。他隱約地感到,將來他組建的特別交通站與這個養馬場有關。他站在窗口往院牆外望去,大雪籠罩下的養馬場靜悄悄的。養馬場的房頂上,一排煙囪在吐著青煙。院落裏白雪皚皚。他心裏有些急了,他想讓交通站的其他人早點見麵,早點建站,早點完成任務。
胡春江回想昨天晚上喝酒時每個人的表現,心裏沉沉的。這幫人,從麵上看似乎是團結一致,一團和氣,其實是各懷鬼胎,各想其事。他們都是各路諸侯派來的小鬼,是一幫不太好纏的妖人。他很佩服局座羅高明,在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警察局能坐穩位置,是件不簡單的事兒。胡春江深知,他昨天一來到這裏,他們就把他當成了日本係的人,很可能把他看成了日本的情報人員,不然昨晚上項世成也不會莫名其妙地大談什麼情報工作。他們這些人上上下下都不會小看他,而且還很尊敬他,懼怕他。然而,這幫人對他還是存有戒心的,特別是羅高明,昨天晚上當他手下談到案件時,他趕忙把話題岔開,就是怕他知道什麼。當什麼深魚被擊斃時,羅高明也是欲言又止。這說明,他們對他不放心。原因隻有一條,他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子。但他反過來一想,他剛剛來到這裏,對他不放心,也是很正常的。
不管這些人心裏怎麼各懷其誌,但有一條是共同的,就是在打擊共產黨方麵,他們是一致的,也是賣力的。他看得出來,特別是項世成、葉自文,還有那個妖女瞿華瑩,他們在這裏就是專門對付共產黨的。
胡春江想,不管他們怎樣陰險狡詐,惡意對付,他的特別交通站是一定要建的,全國各地的黨代表還是要從這裏出境的。
他這兩間臥室,昨天已由兩名年輕的警員打掃得幹幹淨淨,爐子也生得很旺。上午,胡春江坐在火爐邊,回憶往事兒。
咚咚咚,有人敲門。他打開門一看,是瞿華瑩。隻見她穿一身便裝,圍巾把頭包得很嚴實。上穿一件粉紅色的厚棉衣,下穿一件德國青棉褲,大頭皮靴上沾了不少汙雪。她走進室內,抬頭眯眼看了房子一圈兒,坐在胡春江的對麵,把細白的雙手伸出來放在火爐上取暖。胡春江給她倒了一杯熱開水,遞給她。她喝口開水,問:“昨晚沒喝多吧?”
他說:“沒有。”
她說:“好酒量。”
他說:“沒酒量,但不喝不行。”
她的眼睛突然放了亮光,問:“你夫人在日本?”
他正準備回答,這時,又有人敲門。他歉意地點了一下頭,開門去了。
打開門時,他看見了大雪還在飛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