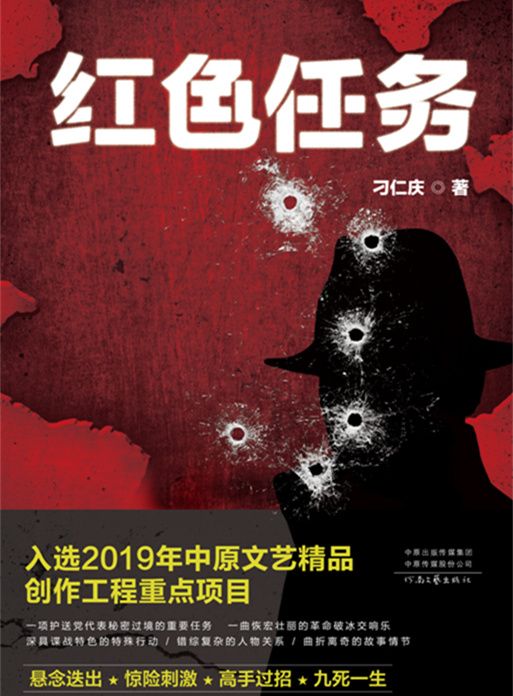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七
滿洲裏不是一座高城深池的都市,而是四周與草原相連接的邊防小鎮。
滿洲裏有兩個警察局,一個是中東鐵路警察局,一個是地方警察局。因為滿洲裏長期受俄國和日本的影響,公安局不叫公安局,叫警察局。鐵路警察局隻管鐵路上的事情,其他案件一概不管。
滿洲裏有一個軍事單位,叫哈滿司令部,是師級的建製,屬東北軍管轄。其實駐兵不到一個團,主要職責是守衛邊防。滿洲裏警察局離哈滿司令部不遠,哈滿司令部的兵營在郊區,而警察局在市區邊沿。胡春江是早上坐火車到滿洲裏的,他一下火車,看見車站大雪彌漫,十步開外什麼也看不見。他沒有馬上到警察局去報到,而是先選擇了一個小旅館住下。他要先觀察滿洲裏的地形,要了解一些情況,然後才能報到。
他觀察了一天的地形,並把重要地點繪到紙上。胡春江很關注日本的駐滿機關,這裏不但有日本領事館,還有個“日本軍事委員會”,在一個中學的東邊。他也關注蘇聯駐滿機關,他小時候的“俄國遠東代表處”現在改成了蘇聯駐滿領事館。來滿洲裏前,母親給他提供了不少滿洲裏的資料。有資料表明,1924年5月,中蘇正式建交,滿洲裏作為進出口貿易的口岸,鐵路客貨運輸達到高峰,工商業發展迅速。目前,蘇聯人在滿達到一千餘戶,五千餘人。從人數上講,日本與蘇聯相比較,蘇聯人多,日本人少。可以這樣說,現在的滿洲裏是蘇聯和日本明爭暗鬥的地方。蘇聯人爭的可能是貿易的主動權,日本人爭的可能是地盤。
1924年春,中國北洋政府改組滿洲裏的公共事務會,設自治會,把自治會作為市政的執行機關。3月,滿洲裏又改為市,設立了市政公所,也就是市政府,對滿洲裏實行市政管理。其實,北京軍政府真正管理是靠警察機製。於是,滿洲裏設地方警察局和中東鐵路警察局,地方警察局下邊設有派出所。中東鐵路警察局沒有設派出所。
張作霖在他的管轄區不設黨務機關,各地的一切權力歸政府。滿洲裏的權力歸市政府,這裏特務組織也設在市政府。目前在這兒誰也不知道誰是幹啥的,誰也不知道誰是啥身份,誰也不跟誰說真話。可以這樣說,這兒是群魔亂舞,各類特務猖狂活躍,陷阱遍地,你防我備。搞不好一個眼神,一句閑話,你可能就會被逮捕,也可能會失去生命。胡春江到滿洲裏的第一天,火車站就發生了一起冷槍案,有一個人在售票窗口買火車票時,被不知從哪兒飛來的冷槍子彈打中頭部,當場死亡。後來聽說是東北軍的特務打的冷槍,被打死的是個日本探子。
這樣一個複雜的小城市,胡春江將在這兒執行中央特別任務,可想難度有多大,風險有多高。眼前的道路,曲折迷離。
胡春江現在關心的不是誰來配合他組建這個特別交通站,而是關注整個城市的地形地貌,這對他很重要。胡春江發現,滿洲裏警察局的後邊,也就是南邊,一牆之隔就是他們家持股的養馬場,養馬場占地約五十畝,膘肥體壯的純種德國馬養了一院子。當然,養得最多的還是當地的蒙古馬。養馬場的名字叫“北國草原之夏養馬場”。胡春江不知道誰在這兒負責養馬,但他知道,這兒每年養馬的收入有他們家一份兒。而他們家的收入,母親全部用在了黨組織的活動上。
胡春江詳細地對日本領事館和日本軍事委員會兩個機關進行外圍觀察。這兩個機關的大門口,都有日本士兵站崗。外圍是中國警察站崗。這兩個地方,他以後可能要經常來往,因為,組織讓他當中國警察,還得充當親日派,他能不到這些地方來嗎?目的隻有一個,就是掩護他把特別交通站建好,把黨代表安全送出國境。
他在外圍觀察了三天。第四天上午,他準備到滿洲裏警察局報到,正式加入滿洲裏警察序列。他離開哈爾濱前,母親對他說:“到警察局以後,剛開始要隨大流,不要讓敵人感覺到你有什麼特別,一切小心從事,不做格外的事兒。”母親還交給他一份滿洲裏警察局中層以上警官名單和警察局基本情況。
中層以上人員名單如下:
局座:羅高明,四十歲,哈爾濱人。三級警督。
抓刑事副局座:塗榮清,四十歲,長春人。一級警司。
抓治安副局座:龔培潮,四十一歲,奉天人。一級警司。
特務行動隊長:葉自文,三十五歲,滿洲裏人。二級警司。
刑警隊長:丁基元,三十五歲,滿洲裏人。二級警司。
治安科長:何之幹,三十歲,滿洲裏人。二級警司。
特情科長:項世成,三十三歲,大連人。二級警司。
總務科長:毛先征,三十八歲,長春人。一級警司。
各科副科長若幹人。
胡春江已經把每個人的情況牢牢記住。
警察局基本情況如下:
全局共有警員三百人左右。其中中層以上人員三十一人,一線警員二百餘人,技術人員二十人,情報人員四十人,其餘為勤雜人員。
局座叫羅高明。他在哈爾濱大直街長大,這個在龍脊龍背上長大的孩子,從小就有當兵或當警察的願望,他父親先是北洋水師的一個管帶,張作霖成氣候以後,他緊跟張作霖闖天下,現在是東北軍一個師某團參謀長。羅高明十九歲從東北講武堂畢業,在哈爾濱當了一名警察。由於他有東北軍的背景,用十幾年的工夫,就當上了滿洲裏的警察局座。可以這樣說,他是東北軍的骨幹嫡係,東北軍是他的靠山。
抓刑事工作的副局座叫塗榮清。他生在長春,父親曾是國民黨秘密情報人員,他本人則宣稱是張作霖的人。
抓治安工作的副局座叫龔培潮。龔培潮在北京上完蘇聯人辦的警察培訓班後,當上了警察。由於他們家的蘇聯背景,讓他到這個特殊的小鎮抓治安,看來上峰是有用意的。
胡春江從這三個正副局座的背景看,母親把他打造成日本背景是對的。局座羅高明的背景是張作霖的東北軍,張作霖現在是北京軍政府陸海軍的大元帥,是安國軍的總司令,其實也就是大總統。羅高明靠這樣的大樹,可謂是樹大根深。塗榮清的背景是蔣介石,而龔培潮的背景是蘇聯。提起蘇聯,蔣介石和張作霖都是又愛又恨。愛的是他們很多地方離不開蘇聯的支持,恨的是蘇聯人又暗地裏支持中共發展。不把他胡春江打造成日本背景的人,他真的不好在這兒站住腳。
中層骨幹背景也是很複雜的:
特務行動隊長葉自文是本地人。他緊跟國家形勢,瘋狂地對革命黨、共產黨人進行逮捕和殺戮。
刑警隊長丁基元,本地人。丁基元在哈爾濱學過刑事偵查學,他的師傅是一位英國的刑事學家。他現在在這兒工作起來很吃力,也很苦惱。今年發生三起凶殺案,他一起也沒有破獲。去年他花錢買了兩個窮人頂替了凶手。頂替的當天,他就把他們以越獄為由給槍決了。
治安科長何之幹,也是本地人。二十歲時,他已是滿洲裏鐵路線上的小老大。當年的警察局座和他父親是朋友,並且有經濟來往,於是就讓何之幹當了個小警察。幾年下來,他就當上了治安科的科長。
特情科長項世成是個倜儻不羈之人。他出生在大連,前年,在父親和嶽父的運作下,項世成到滿洲裏警察局擔任特情科長。項世成傲慢固執,剛愎自用,聽不進去他人半句進言。他為人刁鑽古怪,不與人交心,與同事也是素不相能,是警察局人脈關係較差的人。項世成還長有一雙如獵鷹一樣的眼睛,看人直剜心底。就是他這雙特殊的眼睛,看一眼仇水蓮,就把仇水蓮弄到了手。
然而,他這雙獵眼也有失靈的時候。在他的特情科,有個副科長叫瞿華瑩,二十五歲,南京人,二級警員。自從瞿華瑩空降到滿洲裏警察局以後,項世成一心想把瞿華瑩弄到自己的懷抱,多次死皮賴臉地向瞿華瑩表示愛意,但瞿華瑩就是不買他的賬。她在他麵前隻說工作,不說其他事兒。但是,瞿華瑩是個才貌雙全的女人,她像磁石一樣,把項世成的心緊緊地吸著。在他的眼裏,妻子仇水蓮就像枯草,而瞿華瑩如清晨開放的玫瑰花,不但鮮豔美麗,而且香氣襲人。
總務科長毛先征,長春人,是位三十八歲的老警察。總務科就是後勤科,大到槍支彈藥的管理,警餉發放,小到全局的吃喝拉撒睡,都屬於他管。胡春江的母親重點介紹了毛先征,說他是個沒有私心雜念的人,他大膽而又謹慎,羅高明對他很是信任。毛先征在警察局是個實權派人物,但他為人低調,從不張揚,謙虛謹慎,有文化內涵。平時他很少穿警服,出門基本是便裝。他和其他幾位科長不一樣,其他幾位科長都與局座羅高明明裏是一團火,暗裏是一把刀,鉤心鬥角,暗度陳倉,因為他們各自都有家庭背景和社會基礎,所以誰也不聽誰的,誰也不服誰。而毛先征憨態可掬,透明無邪,他和局座羅高明關係搞得相當好。羅高明一個眼神,一個動作,毛先征就知道是讓幹啥的。
關於特情科副科長瞿華瑩,她的材料中有一張她穿警服的照片,大眼睛,高鼻梁,微笑著把細細的牙齒露了出來。母親和田家彬兩人都有交代,說對這個女人,不能遠,也不能太近。遠了,她會排斥你,打擊你。近了她會研究你,琢磨你。她應該是國民黨另一條線上的情報人員,也可能是汪精衛線上的人。她明裏是警察,實際是在這兒臥底。至於是誰把她空降到這兒來,恐怕羅高明也不知道,隻有哈爾濱警察廳的極少數人知道。不管是誰讓她來的,如果沒有北京方麵的同意,她是飛不來的。
這個警察局內部情況複雜,各種關係盤根錯節,給胡春江增加了不少難題。
黨組織也給胡春江編製了一份檔案:
胡春江,男,哈爾濱人,1920年日本東京警察學校畢業。直隸省警察廳刑事偵查處科員,後調入天津市警察廳。二級警司。
父親胡大山,前清吏部四品官員。民國後隱退於青山綠水之中。
母親烏蘭圖雅,蒙古族,北京蒙古買辦主的女兒。現與丈夫胡大山隱居於長白山深處一別墅山莊裏。
新婚妻子,井黎黎,哈爾濱人,日本留學生。
當胡春江看完這份假檔案後,笑了。母親問他:“你笑啥?”他說:“還給我編造個媳婦,在哪兒?”母親說:“在日本。”他說:“好,安全!既有媳婦,又不讓在國內,省得過假夫妻日子提心吊膽。”母親說:“不,你到那裏後,井黎黎會馬上去和你過日子的。”他一聽不笑了,說:“媽,我一個人習慣了,突然與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一起過日子,多別扭啊!”母親嚴肅地說:“這是組織的決定,你必須服從。”他無言了。他知道,這次的任務重大,來不得半點馬虎,方方麵麵必須想得周到細致。田家彬又給他弄了不少關於日本的資料,讓他熟讀詳記。母親說:“記好了有用。”胡春江知道,在這裏,人們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和地位。
這三天,他除到處看地形外,就是在旅館裏看警察局這些材料。他把拿到手的材料先是讀,後是背誦,這裏每個人的情況他都要熟悉掌握。
第四天早上,天晴了。太陽照在雪地上,陽光一點威力也沒有,冰雪還是那樣的硬,那樣的冷。
從今天以後,胡春江就要在這深淵薄冰的滿洲裏警察局與魔鬼們打交道了。
在他去報到的路上,路過日本領事館,他往大門口看了一下,似乎有一雙眼睛在窺視他,這雙眼睛不是別人,而是他的大哥胡春海。他又認真地看一下日本領事館院內,一個人也沒有。門口站的一個日本士兵和一個警察,像凍僵了一樣站在那裏。
在上海,他跟著冬渡學過幾年日語,檔案把他編成是日本東京警察學校畢業,他不會幾句日語還真不行。
滿洲裏警察局大門口上方,飄揚著五色國旗,而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胡春江走到大門口,被站崗的年輕警察攔住了,他說明來意後,又拿出北京警察廳的介紹信讓站崗的警察看。站崗的警察看後,趕忙敬了個禮,放行了。
來到警察局院內,他問了三個人,才找到局座辦公室。局座辦公室在二樓中間,沒有掛牌,也沒寫字,黑色木門擦得很淨。他泰然自若地敲開門時,看見局座羅高明身著便裝正和一個搽脂抹粉的女人說話。胡春江一眼認出這女人正是瞿華瑩,因為她本人和照片基本一樣。她也是穿著便裝,打眼一看,像個女大學生。此人風姿綽約、靈氣十足,屬於男人看見就很舒心的那種女人。她趴在羅局座辦公桌對麵,頭伸得很長,圓圓的臀部翹得很高,正對著門口。她聽見有敲門的聲音,扭頭看見胡春江進來,並沒感到意外,隻是輕描淡寫地看了一下。盡管是輕描淡寫地扭頭看他一下,但她的目光很有攻擊力,這樣的目光,像黑夜的閃電,直擊胡春江的心底。其實,瞿華瑩看似表麵平靜,實則內心頓起波瀾,因為她看見胡春江氣度不凡地站在那裏,她塵封已久的心,自然地顫抖了一下。羅高明坐在辦公桌前,用傲慢的眼神審視一下站在門口的胡春江,問:“你是……?”
胡春江馬上立正敬了個禮,抬頭挺胸地說:“報告局座,我是前來報到的胡春江。”
羅高明一聽,馬上站起來,笑著繞過辦公桌,把手伸出來,說:“前幾天我的老朋友下野忠來電話就說你要來,怎麼今天才到?”
胡春江忙握著羅高明的手解釋說:“因為在哈爾濱有些事耽誤了幾天,又到深山裏去看望一下父母,隨後又下了大雪,所以來晚了。”他說著拿出北京市警察廳的介紹信和下野忠的推薦信,然後雙手遞給羅高明。羅高明簡單地看一下,放到辦公桌上。羅高明說:“歡迎來到我們這個偏遠小鎮共事!你來得正好,我這兒正缺乏像你這樣專業的人才,真是缺啥人才來啥人啊,下野忠先生推薦你來是給我雪中送炭啊!”羅高明一邊接過被封得嚴嚴實實的檔案,一邊用目光瞄一下他麵前的女人,說:“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瞿華瑩,特情科副科長。”自從胡春江進來後,瞿華瑩一直用獨特的眼神看著他。這會兒聽羅高明介紹,她忙伸出她那細白的手與胡春江握手。她說:“歡迎您!”她身上有一股清香,口中飄出的氣息也有一些清甜。胡春江忙笑著說:“我叫胡春江,以後您得多多關照。”
羅高明讓胡春江坐下,胡春江坐在火爐邊,與瞿華瑩對麵而坐。羅高明也坐下,說:“房子已給你安排好了,生活用品也都齊了。晚上我為你設接風宴。”
胡春江忙站起來說:“不敢不敢。”
羅高明笑笑說:“你不用客氣,這是咱警察局的規矩。來報到的新同誌,警司以上的人員都要設宴歡迎。你的警銜是?”胡春江忙說:“報告羅局座,我的警銜是二級警司!”羅高明說:“就是嘛,你來了,哪有不歡迎之理!”
下午,羅高明召開中層以上會議歡迎胡春江,羅高明把胡春江介紹給大家。
胡春江從大家的目光裏沒感覺到敵意。看來,母親把他包裝成有日本背景的人是有道理的。現在在整個東北,人們一提起日本人,都是恨中有怕,怕中有恨。他麵前這幫人,都是這背景,那背景,一看他是日本背景,都不說什麼了。這幫人的骨子裏都是懼怕日本人的。讓這幫人掌管政權,中國怎麼會有希望?
胡春江上午報到完,年輕的警察領他來到宿舍。他的宿舍安排在院內東南角一棟三層樓的二樓,共兩間。一會兒,總務科長毛先征來到了他的宿舍,隨後又有一個年輕警察抱來一堆床上用品。毛先征對他說:“胡老弟,我叫毛先征,在咱局裏抓後勤,歡迎你來這兒工作,以後生活上、工作上有什麼需要的盡管跟我說,我盡量滿足你。”胡春江忙與他握了握手說:“我叫胡春江,初來乍到,請多多關照。”毛先征說:“我們這兒是邊防,條件差,不像內地的公安局生活條件好,有什麼不到之處請你多多包涵呀!”目前,南方蔣介石管轄的地方叫公安局,北方張作霖轄製的區域叫警察局。同是警序列,雙方兩種叫法。胡春江忙說:“很好,很好,我是來為國家效力的,再苦再累,不講條件的。”毛先征笑道:“我一看你就是一個正派人。”
開完見麵會,毛先征給他拿了冬季製服兩套,大衣兩件,一件是皮的,一件是棉的。另外,鞋帽、襪子及內衣、內褲若幹件。每件衣服都配一套二級警司的領章。
晚飯前,毛先征又領他到槍械庫裏看了看,胡春江一踏進這間警械庫,一下子驚呆了。他沒有想到警察局還有輕重機槍、山炮和高射機槍等武器,上海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應該也沒有這些裝備。真不愧是東北軍武裝起來的警察局呀。看來東北軍不光是讓警察局搞治安,關鍵時候還要能打仗呀!從這一點上講,張作霖是真正的戰略家。
毛先征說:“局座說了,給你配發一把日製十四式手槍。全局就兩把,一把借給日本領事館一個文官用了,這一把你用。”胡春江問:“有那麼多其他製式的手槍,為何給我配發日係手槍?”毛先征似乎很正經地搖搖頭說:“不太清楚,但局座交代了兩遍,讓你佩帶日製手槍。”胡春江想:難道這與他所謂的日本背景有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羅高明定是個有心人。
這時,有個小警察跑來報告說:“晚上羅局座設宴歡迎胡長官,你和幾位領導都參加。”
毛先征把日製十四式手槍及槍帶、槍套、彈夾和子彈都交給了胡春江。他笑著對毛先征說:“我想可能是我在日本留過學吧,不然局座為啥反複強調讓給我配日製手槍呢。”
毛先征拿出一張配發武器登記表,讓胡春江簽上了字。毛先征說:“你如果子彈用完了,隻管到這兒領取就是。”胡春江忙說:“好的,謝謝您!”
這把手槍槍體是白色的,看著很舒心。
太陽落山了,紅色的霞光把雪地染得血紅血紅的。
此時,胡春江小心謹慎,不多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