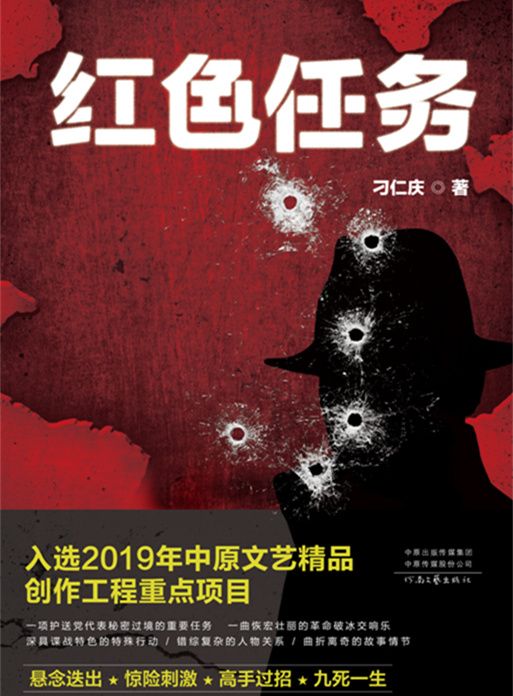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五
1927年深冬的哈爾濱,冰天雪地。整個鬆花江上下,愁雲慘淡。
胡春江是在一個深夜,乘火車悄悄地回到哈爾濱的。
哈爾濱,北方大都市,有三十餘個國家的十六萬僑民聚集在這裏。近二十個國家在這兒設有領事館。中國共產黨很早就在哈爾濱開展工作,這裏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較早,工人和學生運動比較活躍。這裏已成立了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目前,這裏屬北京張作霖的軍政府管轄,北京軍政府前身是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段祺瑞被張作霖趕下台後,張作霖成立了軍政府,組建了安國軍隊,自任陸海軍大元帥。黃河以北都是他的管轄區,並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對抗。南京國民政府目前在東北隻是暗中建立黨務,為將來推翻張作霖做準備。這裏懸掛的是紅、黃、藍、白、黑色橫條旗,而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
胡春江的家在王兆屯一帶,是祖上留下的老宅。他們家過去屬於中產階級,高祖父那輩人開的有商鋪,辦的有作坊。到曾祖父那輩人,兄弟多,時代亂,家道慢慢中落。到祖父那輩人,就成了貧苦人。父親這一輩人還算行,與滿洲裏的朋友合辦了一個養馬場,於是他們全家開始到大草原牧馬。胡春江小時候,對滿洲裏這個小城就很有感情。當然,大草原、呼倫湖是他印象最深的地方。
胡春江下了火車後,沒有馬上回家,而是在他家鄰近一個小旅館住下來。由於有重大任務在身,他不能見親戚,更不能找朋友。他隻能待在小旅館內,觀察他家四周的動靜。家裏隻有妹妹和母親,大哥和未見麵的大嫂都不在家住。如果母親和妹妹出入正常,說明這個家很正常,如果三天不見人出入,說明已經有危險了。他觀察了三天,妹妹胡秋實定點出去,定時回來,說明她在正常上班。母親有時白天出去,有時晚上出去,回來也很輕鬆。這也說明正常。他家是臨街的兩層歐式小樓,是爺爺蓋的。妹妹的臥室就在二樓,每次妹妹晚上回來後,她二樓的燈光就亮了,隨後傳出悠揚的琴聲。
第四天上午,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天空中零零星星地飄著雪花。上午九點鐘左右,母親走了出來,她穿著藍色的大衣,圍巾把嘴圍得嚴嚴實實的。胡春江走出小賓館,在前邊路口等著她,當母親走到他跟前時,他輕輕地叫了一聲:“杜媽媽!”母親警惕地一愣,認真地打量著麵前這個小夥子,當她看見麵前是自己兒子時,雙眼射出了驚喜的目光。她高興地說:“春江?是你小子,你啥時候回來了?”他沒有回答母親的話,反問:“這麼冷的天,你出去有事兒?”母親看了看天上的飛雪,感覺天空離這個城市很遙遠。母親平靜一下心境,說:“我出去辦件事。你先回家吧,你妹妹在家。”“好嘞!”他高興地說。
母親比起前些年,有些老了,明顯的變化是背有點駝了。他站在那裏,看著母親在白色的大街上前行,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胡春江回到家裏,妹妹吃了一驚,高興得尖叫起來:“二哥,你終於回來了,你沒有把媽媽和我給忘了?我想你在上海養馬,真的就不要這個家了?”
他笑道:“我誰也忘不了,特別忘不掉我的妹妹你。”
妹妹叫胡秋實,從小嬌生慣養,現在還有一點調皮。他們兄妹三個,大哥胡春海長相隨父親,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都像。胡春江和妹妹隨媽媽,穩重大氣,做事不急不躁。
胡秋實說她今天過周日,不去琴房上班。這麼多年來,胡春江已沒有了周末的概念了。這次回來,雖然任務在肩,重擔壓身,但沒有與哈爾濱的黨組織接上頭前,他就是個自由人。老南對他說:“回到家裏等消息,不要與當地任何黨組織發生任何聯係。你耐心地等待,會有人找你的。”金牙大媽說:“回到家裏隻說在上海養馬,別的什麼也不能說。”
妹妹問他:“二哥,你出去闖蕩這麼多年,就隻為養馬嗎?”他笑了笑說:“不是為養馬,而是為了生活。”
通往二樓樓梯口上方,懸掛著一具馬頭的標本。馬鬃是棗紅色的,馬的眼睛很有靈氣。這是當年父親親自掛上的。牧馬人對馬都有感情。受父親的影響,胡春江也很喜愛馬。於是,他在上海,就買了一具馬頭標本,掛在小船烏篷內的牆壁上,晚上寂寞的時候,看著那具馬頭標本就能睡著。
這時妹妹說:“二哥,你的臥室一直閑著,我馬上給你打掃一下啊!”她說著,把門打開,進去收拾去了。陽光從窗口照進來,明亮而清晰。胡春江突然感到,還是家裏好,溫馨,舒適,清靜,安寧。在上海這些年,他除住在船上外,還要東躲西藏,提心吊膽。船上夏天熱,冬天冷。吃飯也是東一頓,西一餐,冷熱不均,饑飽無常。每天當夜深人靜時,他都在想,為了追求真理,為了革命大業,為了解放勞苦大眾,再苦再累,都值得。帶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老狼曾經告訴他,我們一旦對著黨旗宣誓,就永遠不能後悔,永遠跟著黨走,要把生命交給黨。
他問:“大哥經常回來嗎?”妹妹平淡地說:“給日本人幹活,忙,回不來,一年也就是兩三次吧。”他又問:“有大嫂的照片嗎?我還沒見過呢。”妹妹說:“照片應該有,但咱家裏沒有。他們家裏應該有。”胡春江聽罷,點了點頭。一會兒,他又問:“大嫂一直在娘家住?”妹妹說:“是。人家有實業,有地位,嫂子在娘家忙大事哩。今年冬天,聽說去日本了,那裏也有他們的實業。我和嫂子很少來往,她家裏的事情媽知道得多一些。”
這時,母親回來了。她忙著下廚房給她這個多年未回來的兒子包水餃。秋實把一曲《鬆花江之夜》彈完後,也下樓幫助母親收拾餃子餡,餡是韭菜、大肉和蝦仁。一會兒,散發著清香的餃子餡盤好了,母親開始擀麵皮。
他想下手幫助母親包,被母親擋住了,她說:“你坐那兒說話吧,我和你妹子包。”
母親邊包水餃邊與兒子嘮嗑。
母親問他:“這些年隻在上海養馬嗎?”他回答說:“兒子沒本事,隻能給跑馬場養馬。”他尷尬地笑笑。母親問:“收入高嗎?”他回答道:“一般,每月吃吃喝喝落不下幾個錢。”自從他舉起右手宣誓以後,他是提著腦袋風裏來雨裏去,刀尖上跳舞,大浪中行船,槍林彈雨,沒有一點報酬。有時金牙大媽每月給他幾十塊錢,根本不夠吃飯。這些年,他在黃浦江上運貨,協助水警搞些治安,給修船廠老板冬渡跑腿,都是為了掙點小錢度日。他是幹著最大的事,掙著最小的錢啊!這時母親又問:“怎麼,出去闖蕩這麼多年沒存一分錢嗎?”胡春江笑笑說:“媽,外邊太難混,我沒攢著錢。”母親突然笑了,說:“兒子,隻要人安全就行,我要兒子,不要錢。”胡春江一聽,也釋然地笑了。
母親又問:“三十歲了吧?還是光棍?”
“是。”他回答。
胡秋實說:“媽,你這兩個兒子呀,都是不急著結婚。大哥三十多才結婚,現在大嫂還沒動靜,我看一年兩年也不一定能給你生孫子。這位二哥目前還按兵不動。二哥,我真不明白,你在等仙女嗎?”妹妹說完自己嘿嘿地笑了。
他對妹妹說:“大哥這時就不能再讓嫂子去日本了,她應該過來和媽生活在一起,一來她能照顧這個家,二來大哥也能常回來看看。”母親說:“你嫂子娘家在日本有工廠,她父母讓你嫂子管理廠子去了。”
母親邊包水餃邊說:“春江,你真的不小了,真該找媳婦了。如果遇著合適的,找一個吧。”
胡春江點了點頭,說:“好吧。”這時他突然又想起了小楓。嚴格講,小楓真的很喜歡他,如果他說馬上娶她,她會很樂意的。然而,小楓現在在哪兒?那天中午,陸師傅他倆喝酒時,陸師傅給他一個地址,現在看來,那個地址肯定是假的。因為已經證實,陸師傅是自己陣營的人,是我黨的地下工作者,是在冬渡身邊臥底的人。胡春江深知,我黨的地下工作者,不可能把自己老家的地址隨便送人的。
太陽升到了正南方向,陽光從天窗上方照射進來,正好照到胡春江的腳尖上。水餃快包完了。這時,有人敲門。妹妹去開門。
是大哥胡春海回來了。胡春江看見大哥,感覺他倆天懸地隔,不是一路人。因為,大哥是在為日本人做事兒,他心裏有陰影兒。
母親見大兒子回來了,用複雜的目光看著他。
胡春海進門看見弟弟在客廳裏坐著,眼睛一亮,笑著說:“我說我在火車上眼皮老是跳,原來是春江回來了,你沒把媽和我們忘了呀。”胡春江忙站起來,迎上去擁抱一下大哥。他聞到了大哥身上有一點微微的香水味。母親似乎是很理解大哥在這大冷天回哈爾濱,問道:“路上順利吧?”大哥把皮大衣脫下,把圍巾取下,說:“路上還行,很順利。嗨,還不是日本人事情多,讓我來哈爾濱領事館送一份材料。送完材料,我就急忙地趕回來看媽了。”母親若有所思地說:“日本人做事越來越不像話,現在咱東北人很不喜歡日本人,你給日本人做事,要低調,要小心,說話辦事別傷著咱中國人。”胡春海說:“媽,你這話已給我說過多次了,兒子也早已牢牢記在心裏。”母親說:“記住就好。”
胡春江抬眼看一下大哥,突然說:“我現在越來越理解當年韓國青年安重根,為啥跑到咱哈爾濱把日本老賊伊藤博文給擊斃了,就是因為日本人背盟棄約,是狼子野心,整天想著吃人。”
水餃下好了,妹妹把兩碗熱氣騰騰的餃子端了出來,兄弟倆每人一碗。胡春海趕忙把他那一碗放到母親麵前,說:“媽,你先吃。”母親把這碗水餃讓了回去,說:“你跑累了,你快點吃吧。”兄弟倆都沒有馬上吃,而是等著妹妹給母親端了一碗,他們才開始吃。
胡春江邊吃邊問大哥:“哥,我還沒有見過嫂子呢。聽妹妹說,你把嫂子弄日本工作去了?”
大哥明顯感到水餃太熱,吃到嘴裏燙得直往外吹氣。等他把這個熱水餃吃完,用右手拍了拍臉,把碗放下,笑笑說:“你嫂子的父親在日本辦有工廠,讓她去幫助他們打理一下企業。我也不想讓她去,可她自己想去,媽媽也支持她去。”他說完看了下母親。
胡春江似笑非笑地說:“我剛才說過,日本人都是狼,要吃人的。你給日本人工作,嫂子又去日本工作,我不知道你和嫂子是什麼樣的感受,但我感覺,人生活在狼群裏,肯定不舒服。”
吃完午飯,母親回到臥室休息了。妹妹上樓開始練琴,胡春海和胡春江倆人在客廳裏嘮嗑兒。
胡春江心裏惦記著滿洲裏,因為他要在那裏建特別交通站,怎樣建站,都有誰參加,他現在心裏還沒數。父親在那兒養馬時,他跟著父親去了很多地方,草原就不說了,父親放馬到呼倫湖,呼倫湖風大,有時候能把牧民的小羊刮到湖裏。那裏的牧馬人都用長長的繩子把小孩兒拴到馬背上,怕把小孩兒刮跑。記得父親帶他到呼倫湖時,也是用長繩把他拴到馬背上。當然也是防草原上神出鬼沒的惡狼。其實,胡春江很佩服狼。他認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團隊配合,群體奮鬥的意識。他現在還記得父親帶他到呼倫湖時,日出把湖水染得血一樣紅。神秘的烏蘭泡有很多鳥兒,很神奇。眾多的鳥兒都飛起來時,驚天動地,遮天蔽日,讓人熱血沸騰。那時,父親給他講了很多成吉思汗的故事,他至今還很崇拜成吉思汗。在上海,每當他端起長槍瞄準獵物時,他認為此時自己就是成吉思汗,甚至認為他有成吉思汗的血統。當時,在滿洲裏他最喜歡火車,每每長龍般的火車從遠方開來時,他隻要能看見,他都會一直把火車看到全部消失到天邊為止。火車向北的時候,父親告訴他那邊是俄國人居住的地方,現在叫蘇聯。那邊的人都是藍眼睛,大鼻子,薄嘴巴。他們需要中國煤炭和木材,火車是給他們送煤炭和木材去了。火車由北向滿洲裏開過來時,父親就給他講,我們中國需要鋼材,火車是給我們送鋼材來了。那時他的理想是想當一名火車司機,開著長長的火車,南來北去,多麼威風。
小的時候,滿洲裏就有日本人,但是俄國人更多。那個時候,俄國人在明麵上,日本人在暗地裏。因為日本人的心有一些陰。鬥智,俄國人鬥不過日本人;鬥勇,日本人鬥不過俄國人。論不怕死,還是日本人。1917年冬天,胡春江二十歲時,俄國人爆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慢慢地,馬列主義傳入中國,胡春江通過父親接受了新的思想,於是毅然決然地獨自出去闖江湖了。在老狼的引領下,他探淵索珠,開始為真理奮鬥。
父親不讓他和日本人說話,自己也遠遠地躲著日本人。父親說過,中國放日本人過來,將有神州陸沉之危。因為,日本人心比天高,野心勃勃。然而,他的大兒子現在不但給日本人辦事,還讓妻子到日本去工作。大哥去給日本人做事的時候,父親還健在,難道父親的觀點和思想變了?胡春江在武漢和上海時,基本不與日本人接觸。有時金牙大媽與日本人打得火熱,他就有些看不慣,但他隻能沉默,不能發聲。他知道金牙大媽與日本人打交道是假,掩護自己是真。他和冬渡這個日本商人接近,是工作的需要,是在黃浦江上生存的需要。
兄弟倆一陣沉默以後,胡春江冷冷地問:“大哥,不給日本人做事不行?”
胡春海一愣,苦惱地一笑說:“目前不行,以後可以不做!”
母親午休完了,她走進衛生間洗漱一下,喝了一杯清茶,說:“我有事得出去一下,你們嘮嗑吧。”胡春海忙站起來說:“我今晚得連夜坐車回滿洲裏,這會兒我得去火車站。媽,我陪你一起出去。”母親好像早有準備似的,說:“走吧,陪我一起走一段路。”
母親邊穿大衣邊對胡春江說:“兒子,你剛回來,對現在的哈爾濱不太熟悉,盡量別出門,在家待著好啦。”
胡春海穿上皮大衣,又把圍巾紮好,然後對弟弟說:“我有要事不能陪你了,今年過春節我也請假回來,咱們好好陪媽過個年。”大哥說完,同母親一起出門了。
大街上十分明亮,整個城市潔白無瑕。滿地的白雪反射著他們娘倆的眼睛,使他們有些不適。胡春海和母親肩並肩地走著。大街上冷冷清清,基本沒有行人。
這時胡春海小聲說:“今天送來的材料我看了,日本人計劃在東北建立政權,他們在設計建國框架方案。”
母親說:“這個情報很重要,我得馬上向上級彙報。以後,你不接到指令,不要冷不防地回哈爾濱,更不能隨便地回到家裏。”
胡春海說:“因為今天的情報太重要,我不得不冒險回來。”
母親說:“這個我知道。另外,給你媳婦寫信,要她有所準備,可能會讓她回國工作。”
胡春海說:“我馬上去辦。”說完,他警惕地環視了四周,沒有人。
冬日的哈爾濱下午很短,四點多鐘,天就快黑了。在一個十字路口,胡春海和母親分手了。母親去哪兒,他不知道。他將來的歸宿在哪兒,他似乎也不知道。
母親像風一樣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