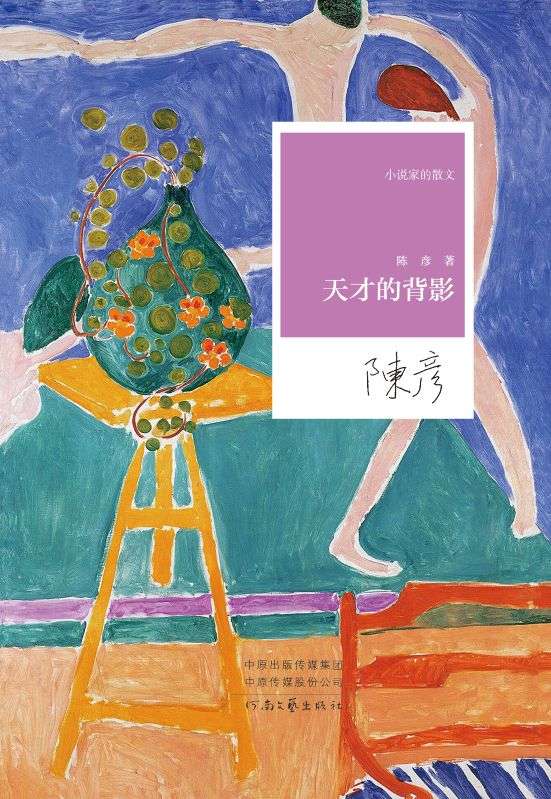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過柞水
因為家在秦嶺深處,因而一年總要路過幾次柞水。當走出漫天黃塵的關中大地,入終南山的灃峪口時,第一感覺便是空氣濕潤清新了。山綠,水綠,到這裏的人都想張開嘴多說幾句話。特別是炎炎夏日,當城裏的洋灰樓、洋灰板曬得腳沾不得、手摸不得、屁股挨不得的時候,再從城裏逃出來,一頭鑽進山裏,就像鐵匠把一塊燒得通紅的鐵板塞進水桶,隻“哧”一聲,溫度就降下來了。
柞水在秦嶺的那邊,如果是沒有到過長江的人,翻過秦嶺,隨便在哪條小溪裏掬一捧清泉咽下,就算是飲過長江水了,因為這泉,是長江的毛細血管。再往前穿行一段青的山、綠的水,就到了被譽為“西北第一奇洞”的柞水溶洞。已經十幾年了,這兒的紅男綠女,出洞入洞,逛得很是自在。我卻因小時候在山裏長大,見過許多山的大窟窿小眼睛,便對這一切沒有了興致。直到近幾年在城裏混飯吃,看多了假山、假泉和曆經人工裁剪的花草樹木,才突然又眷戀起了真真切切的自然山水。
在一個悶熱難耐的日子,我們一幫從山地突圍出來的文化閑人,又喊喊叫叫回去了。之所以要親近柞水,不僅因了這裏的人均森林蓄積量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素有天然森林公園之稱,更重要的是,這兒的山水幾乎涵蓋了山區所有奇異、俊秀、恣肆、詭譎的表征。
我們喝著啤酒,穿行在如此賞心悅目的森林王國中,有人就喊叫憋不住要“排泄”詩句了。結果,噴一些順口溜出來,終覺得是缺了概括自然的大器。不像當年遭流放的賈島,騎一頭瘦驢,走了三天兩後晌,弄得驢瘸人跛的,勉強爬上一座山梁,卻又見一堵奇峰迎麵撲來,才頹坐低吟:“一山未了一山迎,百裏都無半裏平。宜是老禪遙指處,隻堪圖畫不堪行。”想如今弟兄們都坐著一日千裏的現代化小轎車,僅憑窗戶裏觀得的一點淺紅嫩綠,就想吟誦出具有生命震顫感的絕唱,那又怎麼可能呢?
外麵下起了小雨,車窗玻璃逐漸模糊,隻有如潑的濃綠在滿世界浸淫。我們順著一條嘩嘩作響的小河,一直由北向南前行。當水聲由“嘩啦啦”變作“轟隆隆”時,我搖醒了身旁的沉睡者說:“都跌到甕裏了還睡。”他揉揉惺忪睡眼不知咋回事。我說這就是著名的風景勝地石甕子,一個隻需架兩挺機槍,就能要了甕中千千萬萬將士性命的“口袋陣”。他觀了觀朦朧山勢說:“這裏有佛在呢,佛法無邊,誰敢動刀槍?誰動誰就會耳聾眼瞎,瘸腳跛腿。”我問他此話怎講,言:“感覺。”
既然有佛,那就去拜佛爺洞。這是龐大的溶洞群中開發較早的一個。百十餘級台階隨公路“之”字形向上曲折,當眼前豁然出現一個崖石的半邊廳堂時,洞就張開了錦囊繡口。從口入,僅三兩步,就有一個能容上千人拜佛的大殿。據說,去年這裏還辦過舞會,終因麵對我佛,凡夫俗女有些畏首畏尾,而使紅塵未能在此長久滾滾。其實佛是姿態萬千的鐘乳。在洞中三層樓式的升騰結構中,幾乎無處不有佛在。大概是過於莊嚴肅穆的緣故,有人喊了聲那佛像一頭憨豬時,所有被佛法震懾得雙膝發軟、腿肚子轉筋的人,統統都放開了芒刺一樣的思維。很快,一切佛,便都幻化成了似像非像的鳥獸,連萬古凝結的“佛堂幔帳”,也成了“無戲幕不拉”的演藝場。三個“和尚”坐臥念經,更成了現代閑人眼中“三缺一”(麻將場)的寂寞等待。佛似乎並未立即讓這群桀驁不馴者口眼歪斜、手腳抽筋,反倒從凡胎無法洞見的地方送來了徐徐輕風。看來我佛也並非想象中的那樣見不得人說三道四。
從佛洞出來,入天洞、地洞、風洞,洞洞構造迥異,鐘乳儀態萬方:或玉宇瓊閣,細腰飛天;或陰曹地府,閻羅判官;或曲徑回廊,茅棚石庵;或花鳥蟲魚,塔筍柱簽。走在陰陽兩界,行在人妖之間,追溯著成百萬年的溶蝕、刻塑、沉積、澱結,遐想著大千世界的人、情、物、事,便突然覺得洞外關於住房、職稱、工資、級別、物價的煩惱,是何等微不足道。據導遊小姐講,石甕附近,群山皆空,期待開發的神奇洞穴尚有百餘。倘若他日有幸盡遊,不定真會墮入迷霧,唯願坐石化佛化仙,甚至化鬼化妖化豬,卻再懶得朝洞外走了呢。
出得洞來,細雨初霽。一甕的蒼翠,引來百鳥唱和聲聲。粼粼碧波,在甕底一溜白色鵝卵石上搖頭擺尾。大家心緒陡然疏朗遼闊,紛紛指點著甕中比比皆是的美妙處,天花亂墜地設想著給自己也弄一個“閑人齋”之類的書屋。有的人甚至奢望在百年之後,能將屍骨運來甕中,占去彈丸之角,好與佳山佳水同在。卻聽人說,甕中的每寸土地,都已千籌萬劃,度假村、避暑山莊即將拔地而起。到那時,魚貫入甕者,想必多是揮金如土之流。如我輩清貧之士恐怕隻能在這樣的大美境界中,嫉妒那逍遙在枝頭的鴉雀了。
旅遊部門聽說有文化人,便在洞前擺下案幾與文房四寶。果然有人握管揮就了上好的詩句,贏得觀者陣陣讚歎。當一位大作家寫下“今作陝南人,來世洞前柞”時,地方名士抱愧道:“隻有等千山煙囪如林,機聲隆隆,廠房座座,車水馬龍時,方不虧了你這棵‘洞前柞’。”我笑著說:“果真那樣,他可能就不來了。”卻是為何?我言:“那還是柞水嗎?”
1995年5月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