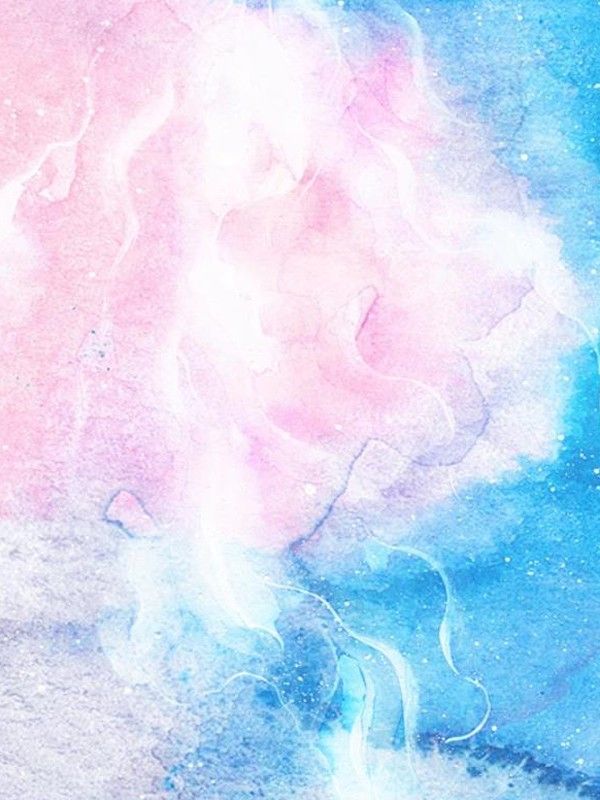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3
一段冗長的沉默後,欒城歎了口氣:
“你找人查我?”
他眸子深不見底,充斥著失望和無奈。
我從包裏掏出一張張照片、轉賬記錄、開放發票。
直到最後一張房產證複印件,男人抓起桌上的紙張往我臉上砸來。
他青筋暴起,聲音拔高:
“夠了!你知不知道這樣咄咄逼人的你有多可悲!怎麼,給我看這些,想要激起我的自責?痛苦?不堪?既然我選擇出軌,我就不害怕你知道。肖奈橙跟你不一樣,她獨立又自由,是著名的畫家,跟她戀愛是我最輕鬆最歡樂的時光。”
“你知道嗎?”欒城慢慢靠近,一把掀起我的衣服,“每次想跟你親密時,看見你的身體,還有這道可怖的疤,我瞬間沒了感覺。”
“繼續過日子可以,離婚更好,我都行。”
他聳聳肩,撞開我,徑直走了出去。
出門前,他給肖奈橙打去電話:
“親愛的,讓王姨做點我喜歡的飯菜。”
“對,穿上那套新給你買的小裙子,我馬上就來。”
玄關處,
欒城心揪做一團。
他頓了頓,回頭看了一眼我的背影:
“如果你求我——”
“嘭。”
臥室的門被砸上。
他心底的最後一絲不忍被砸散,再也沒有猶豫地轉身離去。
我靠在牆角,鮮血順著手腕滑落。
刺痛感喚醒了我的理智。
環顧四周,甜蜜擁吻的結婚照,榮譽拉滿的獎杯,還有......那一牆的往返機票。
四年前,我在國外留學後留校任教。
那段時間我和欒城大吵了一架。
我想回國重新找工作,他不希望我為了他放棄大好前程,我們在黑暗裏吵紅了臉,他滾燙的眼淚落到我手背:
“薑薑,我希望在愛情裏,你永遠都是自己。”
異國戀,幾千公裏。
他一周來回兩次,有時是匆匆為我做頓飯,有時隻能擠出十分鐘跟我緊緊相擁親吻。
那麼愛我的欒城,為什麼會出軌呢?
鮮血流了滿地。
電話響起,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接通。
“阿城,阿城,輕一點,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如果這段感情讓你掙紮又痛苦,我願意放手的阿城。”
男人悶哼,嘶啞又滿足地低笑:
“痛苦?這些年我沒日沒夜地賺錢,生意越做越大,就是為了能跟她般配,我有什麼好痛苦的?”
“出個軌,多愛個女人,又有什麼不對?”
不堪入耳的聲音一遍遍傳進耳朵。
血液浸透一地,
微弱的聲音在耳蝸裏放大百倍。
那些我引以為傲的知識在大腦中變成空白,那些我百倍珍藏的阿城漸漸變得模糊。
鼻腔裏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我艱難地睜開眼睛,嘴角揚起一抹苦笑。
這都沒死。
病房門被適時推開,熟悉的聲音傳來:
“薑姐,你終於醒了。”
“你昏迷的這幾天欒城每天都心神不寧吃不下飯,我代替他來探望你。”
“大好的年華,怎麼就想不開自殺呢?”
肖奈橙把一捧玫瑰花放到我床邊,誠懇又遺憾。
如果沒有看見她眼裏的那一抹得意,我或許真的以為她是個與眾不同的女人。
她笑了笑,露出紫紅色的脖頸:
“你都知道了?”
見我不搭理她,女人喃喃自語:
“最開始我根本看不上他,一個有家庭的男人,有什麼值得喜歡的?”
“可他追著我不放,說自己的妻子身材走樣,說自己的內心寂寞需要我來填補,還說,你長得很像你年輕的模樣。”
她的話像一根長滿鏽的鐵釘,狠狠紮進我的心裏。
一陣惡心襲來,我猛地爬起來嘔了出來。
肖奈橙卻依舊不依不饒,她把上千張親密照放到我眼前:
“看見沒,趴在地上的狗,你最愛的狗兒子吧。”
我再也控製不住情緒,猛地抓起她手腕,近乎聲嘶力竭:
“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你是小三,是情人,是見不得光的!”
胸腔的苦悶爆發,病房門被推開。
欒城三兩步走來,把肖奈橙護在身後。
他深吸一口氣,眼神複雜:
“薑薑,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
男人聲音顫抖又失望:“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肖奈橙更不應該背負你口中的這些肮臟的詞,女人何苦為難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