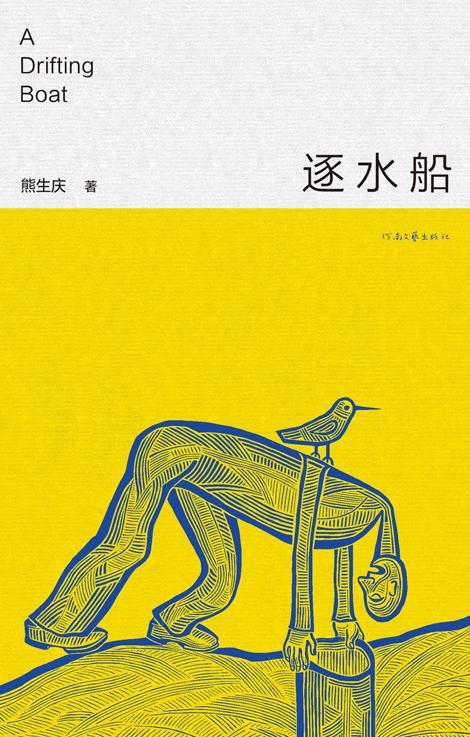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最後一刀
一
七月的一個傍晚,楊柳街突然鬧起來。人們都說,十九回來了,帶著一個苗族女人。女人身著盛裝,滿身銀飾叮當作響,像是剛從電視機裏走出來。
十九是我三叔,小時背乘法口訣總記成三六十九,得了這綽號。我飛快往家跑,打算告訴我爸。以往這時候,我爸通常在睡覺。他上晚班,晚八點到轉天八點,下班去公園下棋,中午回家。
院子裏擠滿了人,氣洶洶把我爸往院角逼。我媽一把將我攬入懷裏,推進奶奶生前住的小屋,嘭一聲關上門。奶奶過世還不滿年,屋子裏殘留著中藥味。我眼睛泛酸,有點想哭。院子裏吵得很凶,我趴在窗台上往外看,認出了葉小歡的爸爸葉屠夫。他光著膀子,衝我爸說,熊秉明,趕緊交人。李洋洋的爸爸李大耳抓住我爸衣領,咆哮道,要麼交人,要麼還錢,你選。
我爸被逼到牆角,慌亂中,他抽出藏在衣服裏的菜刀,指著人群:誰看見了,誰看見的?李大耳說,就是看見了。人們紛紛附和:肯定被你藏起來了。我爸將菜刀橫在胸前,怒道,誰過來我劈誰,看誰敢。葉屠夫冷冷哼一聲,搶近前,左拳虛晃,在我爸揮刀的瞬間右閃撤步,順勢勾住我爸脖子,把他摔倒在地,奪走了菜刀。
人群終於散去,我爸怒罵,貨,有種回來別躲著。我拿出鉛筆和作業本,趴在書桌上假裝寫作業。我爸把我拎起來,提著往外走,我媽跟在後頭。到街口李叔家羊肉粉店,我爸喊,老李,大碗兩個,小碗一個。我小聲說,媽,我也想要大碗。我媽說,兒子,你快些長大吧。
十九失蹤三年了。此前,他是廠裏的過磅員。雖是臨時工,但提到他,廠子裏沒人不知道。這主要歸功於兩樣事。
先說頭一樣。那幾年廠子裏流行估重賭彩頭,兩夥人湊在一起,找個估重對象,說定要押的東西,一瓶酒、兩包煙、幾個罐頭之類,雙方各估個數,然後過秤,誰估的數最接近實際重量誰贏,反之則輸。玩這個,地上跑的、天上飛的、水裏遊的,三叔隻消瞅一瞅,報個數,跑不了。石頭、磚塊這類笨家夥,三叔搭手一掂,八九不離十。廠子裏剛傳出三叔名頭時,有人不服氣,專門在下班路上守他,跟他試手。結果可想而知。後來,人們再玩這把戲,誰也不讓他參加了。
另一樣是搖骰子。楊柳街人都說,我爸和三叔哥兒倆都癡,一個癡棋,一個癡骰子。我爸下棋有輸有贏,賭注小,當個愛好消磨時間。三叔不一樣,他搖骰子十有九輸,那幫喜歡搖骰子的主,他輸了個遍,人人跟前都欠的有錢。說來也是稀奇,三叔手準,按說搖骰子也該經常贏才對,可他在骰子上不僅嘗不到甜頭,還吃盡了苦頭。賭注越下越大,三叔輸了個底兒掉。我爸說,屢戰屢敗,有意思嗎?三叔說,這叫屢敗屢戰。後來大概為躲債,他悄悄離開楊柳街,從此音訊全無。那時奶奶還在,她是個老中醫,街麵上做的有人情,人們不像現在這麼猖狂,敢堵我家的門。
三叔到底欠下多少錢,這始終是個謎,恐怕連他自己也沒算清楚。奶奶和我爸幫他還過些,見他越陷越深,便斷了經濟往來。三叔失蹤,債主們咬牙切齒,揚言要活剮了他。現在,他竟然回來了。我媽說,肯定是有人故意使壞。我爸說,無風不起浪,既然有人看見,可能真回來了。
吃過早飯,葉小歡和李洋洋來找我,約我去滾鐵環。路上,李洋洋指著一號冷卻塔大聲說,快看,有人。我們朝李洋洋指的方向看去,冷卻塔不再冒煙,高高的塔身上吊著兩個人,像兩隻灰色蜘蛛,緩慢向下移動。他們想偷塔,李洋洋說。李洋洋的話把我們逗笑了。葉小歡說,他們在檢修高塔,有什麼好看的。我趁機說,還不如去看你爸賣肉。
楊柳街十八家肉鋪,每家都燃的有一爐煤火,燒豬皮用的。肉沒賣完,爐火不會滅。閑時,葉小歡的爸爸會用竹簽穿上精肉,撒點鹽,架在火上烤。隻消幾分鐘,精肉嗞嗞冒油,香氣四溢。葉屠夫烤的肉好吃極了,可惜我和李洋洋每次隻能吃到一兩塊,不像葉小歡,可以隨便吃,把肚皮撐得滾圓。
葉屠夫忙著和人討價還價,切肉過秤,收錢找零,我們像三隻饞嘴的狗子,齊刷刷站在肉鋪後頭,盯著葉屠夫看。我突然想起來,昨晚是葉屠夫把我爸逼到院角,奪走他的菜刀。雖然烤肉好吃,但我絕不能接受敵人的施舍,我準備回家。這時,街麵上人頭攢動,接著傳來清脆的當啷聲,那聲音由遠及近,十分悅耳。正想看個究竟,葉屠夫一聲斷喝:站住!他操起案板上的砍刀,往街上一躍,橫刀立馬,截住來人。
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三叔。
他真的回來了,帶著個滿身銀飾的女人。
街麵上很快圍得水泄不通,葉屠夫滿臉漲紅:你還敢回來。三叔順手捉來張條凳,搭在街邊,手一伸,伴隨著清脆的當啷聲,女人穩穩坐到條凳上。她不說話,淺淺笑著。三叔身形一轉,閃到葉屠夫跟前。他穿著白襯衣,袖子高高挽起,衣角紮在西褲裏,腳上的皮鞋鋥光黑亮。幾年不見,沒想到三叔變化這麼大,如果不是有人叫他,如果不是他下巴上那顆肉痣,我已認不出他。
三叔兩手一拱,朗聲道,各位叔伯兄弟,之前是我的不是,這次回來,一定解決。他對著人群轉一圈,接著說,大家高抬貴手,欠下的錢,我盡快還清。人群一陣躁動。葉屠夫把砍刀一橫:不還錢,休想往前半步。三叔走到女人跟前,丁零,他扶起女人,一步步朝前走去。站住,葉屠夫又叫了一聲。李大耳貼到葉屠夫身邊,手裏握著把油亮的尖刀。三叔攤手,女人會意,閃到一邊。他往前遞兩步,拱手問,葉大哥,欠你多少?葉屠夫冷哼一聲,看來需要我幫你回憶回憶。李大耳說,十九,我那錢……三叔對著葉屠夫豎起五個指頭,轉向李大耳,折起三根手指,是這個數吧?葉屠夫和李大耳同時點頭。半年,三叔說,給我半年。李大耳盯葉屠夫一眼,玩我們呢,他吼。李大耳右手一抖,刀背橫搭在屈起的左臂上,刀口正對天空,刀尖指向三叔,葉屠夫也拉開架勢,兩人撲向三叔。
一聲驚叫,人們還沒反應過來,三叔已躥到兩人身後,手上多了兩把月牙短刀。李大耳摸摸腦袋,涼颼颼的,當啷,尖刀掉落在地,人跟著軟下去。人群裏一陣驚歎。三叔冷冷地說,能剃你們頭發,就能摘你們腦袋。這時人們才看清,葉屠夫和李大耳同時被剃掉了撮頭發。三叔是從兩人中間躥過去的,身形極快,出刀奇準,仿如閃電。
我媽來到我身後,一把將我逮出人群,磕磕巴巴說,快,去叫你爸。我朝公園飛奔而去。我爸和我回來時,葉屠夫還一動不動站在街上,像尊泥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