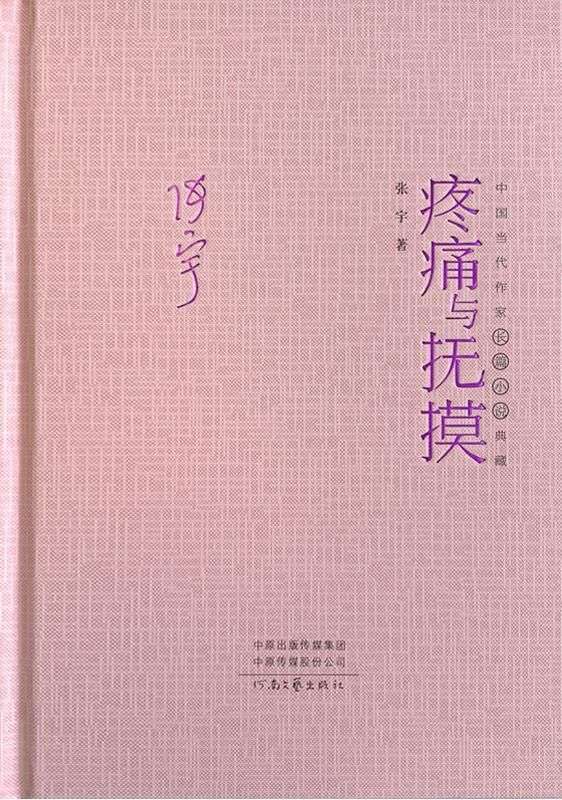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二
水草離家出走那天,空中有風卷著雪花。她什麼也沒有想,就一頭紮進這風雪裏。她最大的心願就是離開這個家,永遠不再回來。當她走出村子來到野地裏,才想起來不知道往哪裏去。她站在雪地裏,風鑽進衣縫蛇一樣在她身上遊走,冷得她發抖。她站住腳開始思考到哪兒去安身。她站住腳開始思考這一時刻,使她擁有了選擇。
我們都從這條路上走過。當母親把我們生下來,那隻是誕生了我們的肉體,接著我們又掉進父母意識的子宮裏。他們包辦我們的選擇和思考,強迫我們要這樣不要那樣,侵占殖民地一樣占有著我們的心靈,我們久久在父母意識的牢房裏服役。父母永遠希望兒女們做他們的替身,他們做兒女們的法則。兒女們就像他們手裏玩的木偶。當有一天我們以各種方式終於遠離父母,獨立麵對生存,開始思考那一刻間,我們才真正從父母那裏分離出來誕生了,從肉體到精神成了獨立的人。就像水草如今呆呆站在風雪裏,麵對整個世界進行選擇。
由於寒冷,她站著站著就蹲下來,把自己團結住。雪花飛來逐漸把她掩蓋,遠遠看去就像一堆雪。地上這麼多路,她不明白走哪一條。走哪一條路,往日是用眼看,現在要想,要把這條路想出來。
她在想路的時候看著這漫天飛雪,覺得她和這雪花一樣,沒有家,沒地方去。風把雪花卷到哪裏就在哪裏落下。無論如何她要先找個地方,那地方沒有風雪,有水喝有飯吃。我們發現,生存開始影響並決定著她的選擇。
我們常說人生處處是選擇,人的一生就是選擇的一生。其實沒有那麼多選擇,說白了人生基本上隻有兩種選擇,我一直把它叫作吃不飽選擇和吃得飽選擇。吃不飽選擇通常指向物質,吃得飽選擇才能指向精神。像水草蹲在雪地裏的這種選擇,當然屬於吃不飽選擇。
有趣的是,水草剛從家裏逃出來。那家裏有吃有喝,她卻忍受不了家裏熬煎,忍受不了那恥辱的圍困。為了逃出精神痛苦的困境,她選擇了背叛。沒想到剛逃出精神困境就掉進生存困境。這就使她從家裏逃出來,隻是從一個困境轉移到另一個困境裏。就像她背叛的那一切趕來追殺她,使她又陷入了自己的背叛裏。
這種人生現象向我們揭示,人生其實就是從一個困境到另一個困境的不斷跳躍和轉移。就像我們小時候玩跳格子遊戲那樣,隻能從一個格子跳進另一個格子,不能跳在格子外邊,格子外邊是死亡。並不是重複,意義和價值就在我們不斷掙脫困境時的體驗和感受裏,是這些體驗和感受放射著人生的光芒。
水草蹲在風雪裏,怎麼也想不到可去之處。姥姥和姥爺死得早,姨和舅她也沒有,沒有親戚可以去投靠。她又沒上過學,也沒有老師和同學可以幫她。但她拿定主意不去討飯,她不能從一種恥辱轉移到另一種恥辱。就覺得天下這麼多路,沒處放下她的雙腳。
她如果實在無路可走,當然還可以再拐回去,媽媽正在家焦急地等待她。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曆,逃出來後沒有辦法就再拐回去,走回頭路。不過這拐回去很容易挫傷銳氣,也許會斷了脊骨那樣軟了骨頭,再也走不出這種軟弱,再也撐不起精神的風帆。水草沒有這樣想,她決心就是死在外邊,也不再回頭。這一筆描繪出她性格的格調。她已經十六歲,開始萌芽人生態度,敢叛家出逃,說明她開始超越物質局限追求精神。追求精神,水草在這風雪之中吹響了她人生的號角。
馬蹄聲是從身後遠處傳來的,把水草驚動。水草站起身,像豎起一堆雪。接著就有人騎馬來到她麵前,那騎馬人跳下馬背時,她看見他身上還挎著手槍。那時候水草想不到怕,就沒有去想這人是刀客還是土匪。隻忽然覺得這個人能把她帶走,她盼望他把她帶走,趕快離開這風雪地。她不關心到哪裏去,她本來就無處可去。她隻要離開這風雪,好像離開這裏就有了希望。
騎馬人一直在看她的模樣,她不明白她漂亮得讓人吃驚。他問她叫什麼家住哪裏,她老實說她家住黃村名叫水草,並連忙說她沒有家了,她已經從家裏跑出來永遠不再回去。他對她叫水草也表示吃驚,並說果然是水家姑娘。看樣子他知道她們水家。接著他又問她多大了。她說十六歲。他對她十六歲表示滿意,笑著說十六歲就長成一盤菜了。她不理解什麼叫一盤菜,為什麼她長成了一盤菜。最後他才說把她帶走,那裏有好吃有好穿有炭火烤,問她去不去。她連忙點頭說我去我去。
那塊黑布條是從他懷裏掏出來的。他要用這塊黑布條蒙上她的眼睛,哄著她說看騎馬頭暈。她沒有反抗,她才不反抗哩,反而覺得有趣。他把她抱上馬,他騎在馬上時一隻手摟著她,怕她往馬下掉。他一吆喝,馬就在雪地上奔跑起來,隻把馬蹄聲灑在風雪裏。
由於眼睛蒙著黑布,又蒙了兩層,她騎在馬上什麼也看不到,就像跑進了黑夜裏。她從來沒騎過馬,她覺得騎在馬上很得意。開始她覺得是往前跑,後來就覺得拐彎,又是拐彎,就這麼三拐兩拐把她拐迷了方向,再也不知道往哪兒跑了。但她覺得路程很遠,跑了好久好久才進了村子。村子裏有風箱聲和牛叫聲,雖然她蒙著眼,她也感受到了村子裏的氣息。走進院子以後,她才被抱下來。又牽著她的手往院子裏邊進,好長的院子,過了三個門檻,才站住了腳。解開她眼上蒙的黑布時,她才發現天已經黑下來。趁著雪亮,她看瓦房很高,就明白這是有錢人家。她不認識這村子更不認識這院子,隻覺得陌生,想起她們家黃村,就覺得很遙遠。
挎槍的男人把她交給一位婦人,他對那婦人說他要去給先生回話,讓婦人把她拾掇拾掇去見太太。她覺得自己像一件東西被轉來轉去。她看出這婦人是家裏的下人,這挎槍人也是下人,主人是先生和太太,一下就覺得先生和太太很神秘。
婦人先掃她身上的雪,一邊掃雪一邊笑著誇她長得好看,就像牆上的年畫。接著端熱水讓她洗臉洗腳,洗得她熱乎乎地舒服。這才牽著她的手去見太太,就像牽著一隻羊那樣。走進太太住的裏屋,屋裏有炭火正旺著,太太站在燈邊,穿著綠緞子棉襖,看去和媽媽年紀差不多。她使喚婦人去給弄飯,走過來就拉住水草的手,往火邊拉。人和氣可親,看見水草就誇她好看如一朵花。由於伸手拉她時摸著了她的濕襖袖子,連忙說:“哎呀,看把你凍成啥了,快換衣裳。”
“不用,太太。”
“濕透了,還不用?”
她那麼親切,水草就脫衣裳。她站著脫,她又把她拉過來,讓她坐床邊上。又去關上裏屋門扇,這才拐回來先扒下她的濕棉褲,又扒下來她的濕棉襖。她把水草的濕衣裳往牆角一扔,像扔垃圾一樣。太太讓她上床,水草臉熱著難為情,她就揭起被子把她按在了被窩裏。太太揭箱子取衣裳,一件一件扔在床上,扔衣裳那副樣子和媽媽一模一樣。太太讓她脫光,從內衣開始換,一件一件全穿成了新衣裳。她最喜歡紅緞子棉襖,穿上又輕又軟和。太太把她脫下的內衣也扔過去,在牆角扔成了一堆,吆喝一聲,那婦人進來,笑著把水草的臟衣裳全抱出去了。
飯是在屋裏吃的。坐在炭火邊喝著熱辣辣香噴噴的麵條湯,吃著暄騰騰的豆餡白饃,吃了個飽。那婦人進來收拾碗筷時還遞給她一塊熱手巾,讓她擦手和擦嘴,一下子把她敬成了小姐一個。她不明白這家人為啥待她這麼親。
“丁三回來說了,你是黃村的?”
“嗯,黃村的。”
這時候她才知道那騎馬挎槍的人叫丁三。
“丁三說你叫水草?”
她點點頭。
“你是水秀家閨女吧?你媽可是遠近聞名的大美人。”
她誤會了。她覺得太太在說她媽不正經,就聽著這話覺得刺耳和別扭。她認真地說:“太太,我沒有媽了。”
“別說憨話,你這大雪天跑出來,還不知把你媽急成啥樣兒了。過一會兒我讓丁三去給你媽說一聲,別讓她惦著。”
“太太,別別,我再也不回去了。”
“坐下坐下,沒有人趕你走,我隻是怕你媽著急。”
“我不管她。我沒有媽了。我是水草。”
“憨閨女,別說氣話。你還不知道這是哪兒吧?”
“不知道。”
“我給你說這是曲陽,離你家黃村才五裏遠,抬腳就到。”
水草不相信,她搖搖頭。曲陽村她去過,沒有這麼遠的路。她騎馬跑到天黑,怎麼會是曲陽呢?
“丁三給你耍哩,騎馬在雪地裏轉圈兒。我可不敢哄你,我們曲家不興哄人說假話。你來到曲書仙曲先生家了,這話你信了吧?”
水草這才明白她跑進了曲先生家。帶她回來的丁三是曲先生的護兵,這太太是曲先生的媳婦。她常聽人說起曲先生,有錢有學問,連各處土匪刀客都敬他。他又肯行善,人家都叫他曲善人。怪不得這家人待她這麼親,她跑進了好人家。就覺得慶幸,沒有白跑。又覺得有福,老天爺有眼,讓她一跑就跑進了善人家。馬上就想到,我以後也給曲家幹活兒當下人,出力掙吃飯錢,做一個正經女人。
她當然不會知道,丁三半路看見她漂亮才撿回來,是準備讓她給曲先生當房生孩子哩。她就這麼一跑,跑進了她未來的婚姻裏。
這純是偶然。她正好那天跑出家門困在雪地裏沒處去,丁三正好那天出外辦事回來碰見她。她又偏偏生得漂亮,讓丁三看驚了眼,一問又是水家姑娘。丁三想帶她,她盼著丁三帶她走。丁三就把她撿回來。一切全是偶然,水草就這麼走進自己命運的偶然裏。
偶然經常是擺渡命運的帆船。
後來每每回憶起來,水草總覺得那是一個夢。那天的風雪永遠在她的記憶裏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