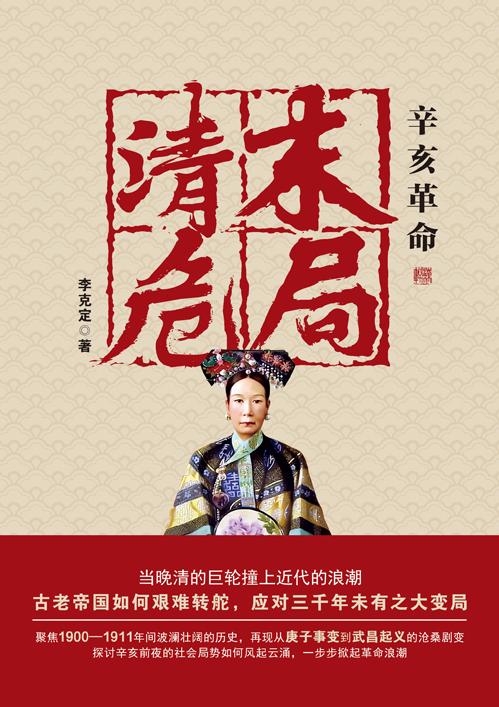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漢口起義
一、救國難上海開國會
“中國議會”在上海召開的前夕,唐才常奔忙了一個通宵。
這次會議籌備了兩三個月,預約參加者一百二十餘人,截至這天傍晚,確定到會的有六十七人。為了省一點租費,唐才常趕到愚園跟管事人懇商,將會址由北大廳移至南新廳。當即指揮人員,重新布置,一小時後方才鋪排就緒。唐才常退至門口打量,滿意地舒了一口氣,肚子不爭氣地咕嚕起來。忽然想起一件要事,他伸手去腰間掏摸,觸到了折疊著的兩張紙。這是反複修改的議會大綱。他打算回到亞東時報報社住處,進餐後再做一次修改。
唐才常走出愚園大門,已是亮燈時分。聽見有人招呼,扭頭看見葉瀚的笑臉。葉瀚帶著歉意說:“明知唐兄日理萬機,還是請去見一下穰卿,他臨時有事相商。”穰卿是汪康年的字,汪康年與唐才常最早提議,籌辦議會商討國是。汪康年是進士出身,曾與梁啟超共創《時務報》,後因康、梁搶奪報務,大起紛爭,唐才常要想周旋其間,不能不壓抑門戶之見。他苦笑著回答葉瀚的揶揄:“我剛搬走幾張桌椅,老兄就吹捧我日理萬機了。”
三人在汪家會麵,汪康年報出七八個人名,稱這些人各有理由,無法參會。另有三位增補人士,準定於明日趕赴會場。汪康年無愧於江浙派首領之稱,大多數與會者都是他邀約來的。唐才常既要借用他的人脈,又要提防他的掣肘。果然,說罷人事變動,汪康年轉換話題,詢問會章定稿情況。唐才常默默取出大綱,雙手奉上。汪康年知道他用謙恭掩飾不滿,卻不理會,一本正經地捧稿閱讀。讀完將稿遞給葉瀚,等對方讀完,他輕聲問:“你看如何?”
葉瀚笑笑,隻把稿子還回來。大綱隻有八條,加上條例簡略內容,總共三百來字,汪、唐反複斟酌,可謂爛熟於心,怎麼還要反芻?唐才常心頭躥火。汪康年瞅他一眼,喚著他的字道:“佛塵兄,你別焦躁。章程是議會之綱,半字不可含糊。葉浩吾被推為會議主席,他要開口念的,不定準怎麼行?”
唐才常麵色如常:“穰卿兄看這樣,還要如何改?”
汪康年正視著唐才常,似要答應,卻又低頭瞧著那稿,輕聲誦讀:“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八國來侵,社稷之憂。而廷無賢臣,軍無良將,朝廷誤信端王、剛毅之言,竟欲以拳匪禦外侮,無異於抱薪救野火。今津沽已失,強敵壓境,京畿震動,危在旦夕。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凡在華域,義無坐視。是以開議會於滬濱,會合海內仁人誌士,共講忠君救國之實。保全東南半壁,以為自立之基;廓清北方大局,得收勤王之效。君憲民權,相輔相成,宗旨歸於變法改製,更新國是。使人人開其獨立自由之心性,上切不共戴天之仇,下啟何以為家之思,而後可以自立於二十世紀世界中。”
這是吸納各方意見,由唐才常一字一字磋磨而成,此時聽來仍如春霖灌頂,令人心開。但他明白,汪康年這位謀篇老手,鋪墊之後才見真章。唐才常接著問:“有什麼不妥嗎?”
汪康年改用明快的語氣講話:“這段前言意思周全,下麵綱目尚需推敲,瞧這第一條,‘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開口便是當頭棒喝,豈不叫人退避三舍?”唐才常分辯說:“有一派人堅持此議,議會議會,列出來就是讓大家議論。比如貴同鄉章太炎,他還要拒絕滿洲人入會呢。若不容人暢所欲言,這會恐怕開不起來。”汪康年笑言:“那個書呆子,他的話能當真?無論如何,舉大事不同於寫文章,鋒芒畢露授人以柄,不是伸長脖子讓人砍嗎?”
唐才常並不跟他拗,答應把那一條拿下來。到開會時有得吵呢,議論紛紜,莫衷一是,這不是國人通病嗎?辭行出門,正想雇車,一輛馬車由東街駛來,畢永年坐在車上喚他。唐才常上車坐下,把剛才的情形告訴這位同鄉。畢永年鄙夷道:“那人膽小如鼠,你為何跟他共事?”唐才常回稱:“汪兄並不怯懦,再說他是上海坐地虎,要辦事你能繞開他?”畢永年將眼一橫道:“汪康年的口舌幫,康有為的保皇派,都把你架在火上烤!佛塵你聽我說,康、梁在戊戌年害人不淺,你不要成為第二個譚嗣同!”
唐才常聞言一驚。畢永年伸手拍拍他:“咱們去見你弟弟,催他把票證趕快印出,廣為散發,助你成軍。”
這是庚子年,1900年。北方的義和團運動鬧得正凶,八國聯軍乘勢入侵,攻陷天津,挺進北京。慈禧在發動戊戌政變後,遲遲得不到列強的承認。對於義和團打出的扶清滅洋旗號,她像在洪流沉浮中抓到一塊漂木,咬牙決定用拳滅洋。在這場亂局中,劉坤一、張之洞等南方督撫,與英、法、美等強國達成諒解,發起東南互保,謀劃局部和平。處於朝廷和江南大吏夾縫中的,是唐才常鼓動的第三方勢力。他們由三方人馬會合而成,一是唐才常、沈藎為首的康、梁係;二是汪康年、葉瀚為首的江浙派;三是畢永年、林圭為首的興中會,這是孫中山的革命黨。唐才常跟三方都搭得上關係,可也遭受各方撕扯,難以擺平。幸運的是,有兩位頭麵人物堪作緩衝,一為容閎,一為嚴複。前者曾任中國駐美公使;後者翻譯西方名著《天演論》,堪稱推介西學第一人。
來到虹口新馬路梅福裏,二人下車,拐入東麵一條小巷。這裏有一間低矮的房屋,側邊附有半間耳房,可供造炊。唐才常立在門口輕輕一咳,“吱呀”一聲屋門打開,他的三弟唐才質,站在裏邊衝著他笑。唐才常跨進屋,回頭招呼畢永年,卻見畢永年瞄向耳房。怎麼了?唐才常還沒問出,畢永年先問唐才質:“誰在那裏?”唐才質一時愣住,想了想才醒悟,他稱讚畢永年:“你有千裏眼順風耳?是有一個陌生人,來呀,過來見過兩位貴人。”
耳房中走出一個年輕人,有點茫然地望著這邊。唐才質吩咐這人:“來見見你大表哥。”年輕人膽怯地囁嚅著,趨前兩步又後退一步。唐才常責怪地叫一聲“三弟”,唐才質這才告訴哥哥:“這是楊姑父的小兒子。”楊姑父家迭遭變故,又遇天災,無法糊口,隻好打發表弟前來投奔。唐才常接過弟弟遞來的信,看到姑父在紙上的傾訴,心中似有什麼東西梗著,一時想不清楚,抬頭便見畢永年狐疑地瞅著他:“姓楊的姑父?我沒有聽你說起。”
唐才常向他解釋:“一位堂姑,住在瀏陽鄉間,平時來往較稀。”
畢永年不依不饒:“這表弟你沒見過?”
唐才常答道:“是,堂姑家孩子多。”
“他怎麼找到這裏來了?”這句問話無人回答,畢永年徑自追問年輕人,“誰引你來這裏的?”
年輕人唧唧噥噥地,總算說清了,是村鄰帶他到上海,找到村鄰在洋行做事的叔叔。那叔叔送小表弟到亞東時報館,等不到大表哥。叔叔從報社那裏打聽到這個地方,指引他找到三表哥。爹媽叫他來投親,不隻求一口飯吃,還叫他幫表哥幹活。聽出這話有央告的意味,唐才常連忙收起信紙,笑著呼喚表弟,叫他進屋來說話。畢永年跨前一步,堵住門問:“你會幹什麼活?”年輕人低聲答:“我不怕吃苦,下力的活都能幹。”
這位畢兄疑心重,曾經誤會過不少人。唐才質生怕得罪了親戚,跨出門將他擠開一些:“表弟來得巧,我正缺人手呢。我還沒告訴大哥,幫工日前回鄉奔喪,把印刷事務撂下了。我剛要跟表弟搭幫幹活,二位兄長就來查工。”
他伸手要拉表弟進屋。畢永年橫他一眼,麵向年輕人:“這裏沒地方住,你還回報社吧。”這可有點過分了。唐才常開了口:“鬆琥兄,讓表弟進來,俺弟兄說說話。”畢永年沒有回頭:“有話到報社說。我不是硬充惡人——”
對麵一聲嘶吼,聲音卻又噎住,年輕人麵色紫漲,噙著淚嚷:“我不要你們施舍!好,好,我走。”說著扭頭疾走,唐才質追了上去,唐才常也趕出來。畢永年有意延緩他們的腳步,拉拉扯扯間,已經看得見路口。畢永年東張西望,喚來一個人力車夫,打發他把年輕人送往亞東時報館。
唐氏兄弟滿腹怨氣,罵他心狠手辣。畢永年一臉正經:“閑話少說,我要取走票證,兩萬張。”
唐才質打了個愣:“兩萬?哪有啊,你來看。”
三人相跟著回屋。屋裏陳設簡單,東西牆角各有一張木床,正中靠裏的那個物件卻甚顯眼,那是一架英製石印機。中國古時依靠雕版印刷,先要一刀一刀在木版上刻字。歐洲人發明石印,機器核心部件是一塊光滑的青石板,印刷流程甚為簡便:先用一種特殊藥液在紙上寫字,半幹時將紙附貼在石板上,用清水刷過,便製成字版。然後用白紙刷墨印製,既快捷又清晰。此法由法國教會於光緒二年傳入上海,現已流行於沿海各商埠。
此時機器上空空如也。畢永年繞開它,打開東床腳頭的一隻木箱。他搬出一遝紙,放在床頭上,張開右手拇指和中指,量一下它的厚度,不相信地問:“就這些?還有嗎?”
唐才質道:“五千,多一張也沒有。”
畢永年大為生氣:“你怎麼磨洋工!上回一萬三千,半月工夫發散精光。漢口催得十萬火急,安徽、湖南也在討要,你耽誤咱招兵買馬。”
“我不是沒幫工嘛,剛才你就趕走一個。”
畢永年不再吱聲,尋到印墨、紙張,拉著唐才質開印。兩人配合默契,印品一張張成形,亮眼地擺放在唐才常麵前。唐才常拿起一張端詳,很熟悉的字眼,仍使他產生新奇的感覺。這是西洋造的上等白紙,幅麵有書頁一半大小,票麵仿照市上流通的錢票樣式,上方橫書“富有”二字,像是錢莊的字號。正文豎寫“憑票發典錢壹仟文”,左邊年、月、日,下方留有蓋印的空白處。背麵右邊印“某年某月某人來”,這是拉人入會的記號。唐才常抬眼打量二人操作,看著票證越印越多,仿佛看到新兵入伍,不禁感慨地長籲一聲。
唐才常想起戊戌年夏秋之交,他應譚嗣同之召匆忙赴京,參與變法。行至武昌得到噩耗,太後一黨推翻光緒,譚嗣同等六君子,喪命北京菜市口。唐才常懷恨挾仇,東渡日本,加入了康有為的保皇會。畢永年對康、梁嗤之以鼻,拉他接近孫中山。徜徉於康、孫之間,唐才常對兩派並無成見,認為革命、保皇各有道理。光緒帝主持變法,對譚嗣同有知遇之恩,如能複辟帝位,唐才常樂見其成。孫中山要革慈禧之命,進而推翻異族統治,也應祝禱成功。不過比較而言,康有為坐而論道,擺出老氣橫秋的帝師架子,令人心生厭煩。孫中山勢單力薄,卻敢於發動廣州起義,雖然遭遇失敗,但仍在策劃再起。保皇會號召勤王,勤王就要起兵。梁啟超推動康有為同意,由唐才常率領林圭、秦力山等,一同回國舉事。行前聚會於東京紅葉館,梁啟超特邀孫中山出席,以示兩派精誠合作。慷慨悲歌之際,唐才常即席賦詩:
燕市譚君死,湖湘弟子殘。
椎心酬故劍,泣血吐新丹。
顧盼煙雲亂,喑嗚甲杖寒。
楚旌北指日,掃穴問田單。
他沉浸在往事中,忽然聽見畢永年的聲音,似從遠方傳來:“佛塵你睡著了?快回報館休息吧,我得熬夜印票。”稍停他又改口:“不要回去了,章太炎正在找你,叫他纏住,休想擺脫。”
唐才常振作一下精神:“他要跟我辯論。我若不跟他說清,明日別想開會。”
唐才常便往外走。卻見畢永年趕上來,往他懷裏塞了一個物件,感覺硬邦邦的,是不是一個饅頭?唐才常顧不上享用,趕到馬路上,準備賃車乘坐。此時夜色已深,街無行人,連一輛黃包車也尋不到。這裏是英租界西南區,不遠處就是美租界,治安比華界好得多。唐才常加快腳步,到了一個小十字路口,拐入左邊一條巷子。今天是六月三十,無有月光,兩旁房屋緊夾著狹窄的道路,顯得越發黑暗。聽見自己腳下的摩擦聲,他突然心頭一悸,直想回頭重走大街。
你竟然疑神疑鬼!唐才常嘲罵著自己,腳步卻停住了,他望見前麵出現幾個人影,很快便逼近了。“逼”是他的感覺,可是千真萬確,他依稀認出一個人,那是他剛剛見過的。唐才常掃一眼四周,鎮靜地發問:“小表弟,你怎麼在這裏?”
小表弟沒有回話。同來者也都沉默。他們一共五人,除了當頭的那個,都比唐才常低矮,他應不畏懼與之交手。為首那人,仿佛見過,對了,是他!唐才常出國前回鄉探親,路過長沙南門外時,被一夥人截住去路。他們七嘴八舌,罵唐、譚夥同謀反,譚嗣同已經伏誅,該殺唐才常了!爭鬧衝突之中,有一人手持鐵尺,擊傷了唐才常的額頭。脫險之後得知,那是鄒姓武秀才,是維新派的死對頭。這叫善者不來。唐才常抱拳招呼:“這位是鄒老兄吧?”
鄒秀才咧開嘴笑:“看來你還認得我。”
“長沙鄉親,不敢不認。請問此來有何貴幹?”
“你該問我有何公幹,我想為公家幹一件正事。你去日本乞討一遭,回來仍跟倭人勾結,真叫記吃不記打。”
“我還記著你那一打。道不同不相為謀,你習武的不同於我作文的,咱們各行各路吧。”
“你想跑路?可以,隻要給我留下字據:自知有罪,痛改前非,將以斬殺倭寇自贖。”
隨著鄒秀才的手勢,幾個人趨上前來,做出讓他寫字的架勢。唐才常閃身退避,目光緊盯這幾人,卻給鄒秀才一個空子。他搶步上前將手一探,同時大喝一聲:“上海道台下令捉拿反賊!”一個碩大的布袋淩空落下,把唐才常兜頭罩住。唐才常奮力踢打,被那袋子通身包裹,正是動彈不得。綁架者還要用繩捆紮,唐才常拚命掙踹中,手肘觸到一個硬硬的東西,忽覺靈光一閃,手槍,天哪手槍!他盡力探手入懷,抓住那把槍,向外開槍射擊。槍聲穿破夜空,打出一片驚呼。那些人拋下獵物,便要四散奔逃。鄒秀才大聲喝阻,那些人聽令回頭,要把這事幹完。
馬路口響起警哨聲,接著馬蹄嘚嘚,奔過來兩匹快馬。在一片慌亂中,租界巡捕趕到事發現場。這是兩個印度人,替英國主子幹活,他們用鷹眼藐視這夥“清國奴”。印度人聽不懂漢話,把雙方押回巡捕房審訊。唐才常向華人巡捕陳述:這是一夥長沙暴徒,模仿北方的義和團,遵奉頑固派的意旨,加害維新人士。鄒秀才哪肯屈服,自稱執行上海道台的命令,前來捉拿謀反之人。巡捕要他拿出指令,鄒秀才拿不出,當即受到訓斥:“即使你有指令,在租界也沒有執法權力。當街綁架乃是重罪,應予收押,等待審判!”
唐才常被釋放出來,昏昏沉沉地回到報館,感覺耗竭了心力。從側門進了院子,摸著黑往前走,距離住室不遠時,發現一間屋子亮著燈光。他站住想了一下,才明白怎麼回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這個書呆子,天快亮了還在等我!唐才常大步走進那片亮光:“好哇,先生終於等到我了。請問章太炎,再問章炳麟,你要跟我論辯,還是跟我辯論?”
太炎是這人的字,本名叫章炳麟。在人世交往中,字比本名叫得響的,有個說法叫“以字行”。隻有大名人才能以字行。章太炎是經學名家,卻非食古不化,曾任《時務報》主筆,又赴日本遊學,跟各色各樣的新派人物交往。從發呆到發憤,他每行一步都比別人更激進。比如這一回,他力主拒絕滿人入國會,甚至提出要殺金梁。金梁何許人也?他乃滿洲瓜爾佳氏,世代駐防杭州。北京發生政變,金梁公開祭奠殉難六君子,上書請殺奸臣榮祿,被時人稱為“滿洲聖人”。章太炎殺金的理由是:“我願滿洲皆惡人,無聖人。若有聖人,我華夏光複漢業尚有何望!”
章太炎從書桌旁起立,覷著唐才常的臉:“你回來這麼晚,是否突然生變?”
這呆子猜到他出事了?唐才常對著他點頭。
章太炎急忙問:“什麼事,明日會議不開了?”唐才常說請放心,按時開。章太炎說聲那好,舉起一份文稿,湊近桌上的煤油燈:“我寫了一份《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念給你聽。章炳麟白,為請嚴拒滿蒙人入會事:竊以東胡賤種,狼子野心。今之滿洲,明時號野人女真,淫暴殘殺,是其天性。自多爾袞入關以後,盜我疆土,戕我人民,揚州之屠、江陰之屠、嘉定之屠、金華之屠、廣州之屠,流血沒脛,積骸成阜,枕戈之恥,銜骨之痛,可遽忘乎?……”
這篇檄文洋洋灑灑,鞭撻滿洲,章太炎念得音調鏗鏘,口沫橫飛。唐才常口中讚賞,心中膩歪,連聲告饒道:“好了我的先生,在下是不可雕的朽木。明日到會者皆為名士,先生與之切磋,那才撓住了癢處。”
“我在說痛處,你來扯癢處!”章太炎將稿一擲,憤然轉身,不料出了一個小意外。那把座椅早已破舊,章太炎的辮梢,被一處榫眼卡住了。唐才常走上前去,幫助章太炎脫了困。這條辮子引發了他的感慨:“太炎兄啊,不管有多痛,滿人和漢人,都有一條相同的辮子。”
章太炎猛然回頭,托著辮子瞪著,仿佛麵對仇敵:“我們國會,就要對付這條辮子!”
庚子年七月初一上午九時,上海愚園南新廳,一共聚集六十三人。從容閎、嚴複往下數,鄭觀應、文廷式、張元濟、陳三立、汪康年、唐才常、夏曾佑、宋伯魯等,皆為知名人士。籍貫涵蓋廣東、浙江、江蘇、湖南、安徽、江西、福建、廣西、四川、陝西、直隸,可謂群賢畢至。這些人聲氣相求,身份殊異。例如,陳三立、丁惠康、吳保初,出身貴介,與譚嗣同合稱“四大公子”,對於嗣同之死,同懷切膚之痛。又如,文廷式是帝師翁同龢的弟子,官至禮部侍郎,深得光緒信任。甲午戰爭前夕,因諫阻擴修頤和園,觸怒慈禧而遭罷斥。他由亡命日本,到潛回上海,一個人的曲折經曆,描畫出這群人的會聚過程。
章太炎不關心這些。到場以後東張西望,沒有發現不想見的麵孔,他才舒一口氣。會場坐北朝南,擺放著連排桌椅,已經坐滿了人。麵對一座方形講台,唐才常、汪康年、葉瀚三人,在一張長桌旁商量事情。章太炎疑心頓起,沿著中間過道往前走,一個人的脊背擋了路。章太炎說聲“借光”,那人回過頭來,他看到了孫寶瑄的笑臉。孫寶瑄字仲璵,是李鴻章之兄李瀚章的女婿,出入權貴之門,卻為新派人物。二人是浙江同鄉,章太炎跟他不講客氣:“我堅拒滿人入會,仲璵兄以為如何?”
孫寶瑄要逗逗他:“排除滿人,合乎大義。為何?因為本會為拯救中國,不為振起東胡。為保全人民,不為保全異種。是故聯合誌士,隻取漢人諸賢可備顧問,若滿人則必不令其闌入也。”
這幾句話十分入耳,章太炎正要誇讚,忽想起這是《請拒滿蒙人入會狀》中的詞句,他皺起眉頭:“我這文章脫稿不久,你從何處得知?”
“先生上月賜寄信函,向在下傳授高見。下麵應當講這番道理了:或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雖在滿洲,豈無才智過人如壽富、金梁者?”
章太炎氣惱地搶過話頭:“豈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愈材則忌漢之心愈深,愈智則製漢之術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陽稱平權,而陰求專製。今所拒絕,正在此輩。”他把嚴厲的口氣放緩些:“好在今日未見此輩。”
孫寶瑄笑嘻嘻地說:“目中無,冊上有。”
“冊上?”章太炎打個激靈,向台上望去,看那樣子要開會了。他擠開孫寶瑄急步上前,到了桌前,從葉瀚麵前抓起一本花名冊。一行一行往下看,果然看到壽富、金梁。他氣呼呼地用手指點:“壽富,出身宗室;金梁,世代駐防!”
葉瀚像要故意氣他:“那宗室讚助變法,這駐防反對政變,他在祭孔時祭奠六君子,膽量非常人可及。再說,他不是你的朋友嗎?”
見章太炎梗起脖子,唐才常拉起他往台下走,示意地向汪康年瞟了一眼。汪康年麵向大眾作揖:“容純甫博士,嚴又陵總辦,各位同誌各位同胞:今日在此開會,公推葉浩吾做主席,以下便請浩吾主持。”
葉瀚鞠躬就位,宣布三項議程:一是選舉會長、副會長;二是擇任議會職員;三是議定議會章程。就此征求意見,大家一齊鼓掌,這便一齊通過。
葉瀚笑容可掬:“多謝諸君抬舉。現在進行第一項,選舉正、副會長。當選人須具備以下資格:處世公正,精通西學,明曉大勢,察悉外情,不偏不倚,和衷包容。選舉仿照日本辦法,也是西方通例,采用無記名投票方式。”
汪康年、唐才常等滿場走動,分發筆墨和紙張。葉瀚宣講的選人標準,畫下一個明顯的框框,況且大家早有默契,所以選得很順利。經過唱票和監票,主席葉瀚鄭重宣布:容閎得四十二票,當選正會長。嚴複得十五票,當選副會長。大眾鼓掌,歡迎正、副會長就位於主席台。七十三歲的容閎容光煥發,發表了簡短的即席演說:“各位同誌,容閎年輕時求學於美國耶魯大學,是中國第一個西方博士。可我沒有榮光,隻感痛心。因為我畢業四十年來,中國的罪業一步一步加深,直到今天,我求學的美國與七國一起,其兵鋒已經抵近北京!國亡在即,我們若不奮起自救,隻有忍受屠戮與奴役。中國議會即為救亡而開,議出方法,會合英才,方有化弱為強之一天。容閎與諸君共勉之!”
眾聲應和之中,會長和副會長協商推薦,眾人表決同意,以葉瀚等三人為書記,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為幹事,唐才常兼任會計。中國議會至此正式成立,按照議程,開始討論章程綱要。先由葉瀚宣讀草擬的提綱:一、保全中國疆土與自主之權;二、力圖改革,日新文明;三、聯絡外交,保持和平之局……
葉瀚念罷第一條,下麵已響起議論聲。沒等念出第四條,後排站起一個清瘦的身影:“請問主席,頭一條應該是: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
此人是林圭。葉瀚沉得住氣:“大家對這一條有疑慮,可以先把它拿下來。”
“什麼大家?我和沈藎、狄葆賢等十五人,共同提出此議,這叫不叫大家?隻有除掉偽政府,才能保全國家自主。刨去這一條,你那第一條便無以立足。”
笑意僵在葉瀚的臉上。新當選的幹事汪立元站起身,替同鄉主席解圍:“林老弟有十五人同意,卻不知有更多人有意見。他們並非擁戴慈禧太後,而是擔心未樹旗,先樹敵,招來四麵八方的攻擊。說到立足,請問腳下的地盤是誰的?是劉、張兩位大帥的。咱這裏明言不認政府,在本地就過不了關,你還如何起事?”
林圭要反駁,卻被沈藎搶了先:“汪兄言之成理。要想過關,先得打通關節,最好拜在大帥門下,當一個幕賓或者清客,仰人鼻息,討人歡心。”
汪康年早年曾入張之洞幕府,對這種尖刻的諷刺,並未放在心上。這激起了朋友們的義憤。便有人說:“沈君不要一棒子打翻一片人!在場者大多出自督撫門下,就說容、嚴二位會長,當年便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僚屬。督撫乃是鎮疆之城、守土之山,我等開會於此,豈能繞開城隍老爺?議會與督撫不應對立,而應配合,以我之議,定他之計,才算腳踏實地做事,否則與清議何異?”
林圭越聽越不耐煩:“你這一條盤算,真把議會鼓搗成張之洞的幕府了。”
汪立元笑著回答:“如能踐行議會的主張,張之洞就是幕府的夥計了。不瞞老弟,他們的確打算照計行事,起兵勤王,迎光緒皇帝南下。”
“勤王勤王,自取滅亡!”
這一句很是突兀,眾人愕然回顧,見是章太炎從外麵走進來,兩手捧著一個盆子。他剛才出了大廳,沒有趕上這場爭論。他邊往前走邊問話:“迎光緒南下幹什麼?”
汪立元道:“脫離太後虎口,請皇帝陛下複位。”
“複什麼位?太後是虎口,皇帝是虎尾,苛政猛於虎的虎!”
章太炎登上台去,將盆子朝桌上一蹾。葉瀚探頭看看盆中,不由吃驚地咂舌。容閎和嚴複也瞧見了,皺起眉審視章太炎。章太炎似要釋疑,從盆中抓起一把短刀,向台下晃了晃。然後放下,麵對質疑,放言高論:“自從清軍鐵騎入關,我炎黃子孫淪為奴隸,經曆九代皇帝加一太後,苦難如山,萬劫不複。此前曾有太平天國起義,幾乎顛覆清朝統治。可惜曾、左、李甘做漢奸,掐滅我漢人振起生機。現今清室惡貫滿盈,漢人唯有祝其早亡,豈能叫它借屍還魂!”
對於章太炎的文人狂傲,人們原是喜歡的,有時還故意逗他發作,今日此言卻甚逆耳。汪康年轉對唐才常笑:“這是你亞東時報的主筆,題旨需要佛塵兄拆解。”
“他這小主筆,遇上你這時務報大主筆,那叫小巫見大巫。”唐才常隨和地笑笑,麵向章太炎,“當前勤王是大題目,因為覆巢之下,不能淪為沒王的蜂。光緒皇帝因變法而失位,你也承認皇上賢明。今天能使賢明複位——”
“從今天起,我不尊稱光緒,隻稱他為愛新覺羅第十一。不管賢不賢,他是第十一個僭我皇權的滿洲人。我們開議會講民權,難道還需要皇帝嗎?西方民主國家,皆以總統為元首,分析字義,就是歸總、統管之義。總統是民眾的大管家,哪像皇帝握有生殺予奪之權,充當天下萬物之主宰。”
章太炎講得口沫飛濺,孫寶瑄安撫這位書生:“不要皇帝也好,若能救出光緒,可以請他當總統。”
章太炎當即駁回:“救出讓他當平民!”
將“平民”加於光緒之身,這話令人心中一震。議會中人無論何種身份,都是同情光緒的。把翻倒的龍椅扶正過來,等於還世間一個公道,是人們願意看到的。不過,光緒如今連平民都不如;而且,如果真讓皇帝做總統,看上去是不是有些滑稽?章太炎攪起更多爭議,會場一時眾聲如潮。經過反複抗辯,容閎歸納出第四條綱要:平息內亂,使人民進步。林圭所堅持的“不認偽政府”,不明確列為第一條,可以作為實行要點:一、尊光緒帝;二、不認端王、剛毅等死硬頑物;三、隻要力行新政,並不排除滿人。
容閎請大家舉手表決。樹林般舉起的手臂,像在對章太炎打臉。章太炎茫然望去,突發狂笑:“嗚呼哀哉,噫嘻甚矣!中國士人來開議會,賢者則以保皇為念,不肖者則以保爵位為念,莫不遵奉滿洲,漠然世仇。如此而談民主,緣木而求蠹魚。我依《請嚴拒滿蒙人入會狀》,請與諸君歃血為盟。盟誓之後,如有引滿蒙人入會者,同會共擊之!”
章太炎從盆中抓起刀,豎起左手中指,請大家觀看。刀光閃處,鮮血滴入盆中。多人驚訝出聲,也有人憤然作色,斥責章太炎胡鬧。章太炎觀察台上三人的臉色,然後移目往下看,沒有發現甘願追隨者。章太炎將目光瞄準唐才常:“佛塵,你肯出血嗎?”
唐才常坦然道:“我願傾盡熱血,區區一滴兩滴,不值得耗費心思。”
“說得好,我願還你一個幹得好。”章太炎轉向大眾,“一麵排滿,一麵勤王,諸君自相矛盾,炳麟去意已決。”
章太炎伸出左手,從腦後攫住辮子,舉刀去割發辮。這激起一片驚呼,台上人要去阻攔,但對那刀有所忌憚。反手難以著力,辮子不易割斷,章太炎焦躁起來。卻有一人從後排站起,疾步登台,這是畢永年。他對章太炎點點頭,接過刀子,用力一揮,割斷了那根長長的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