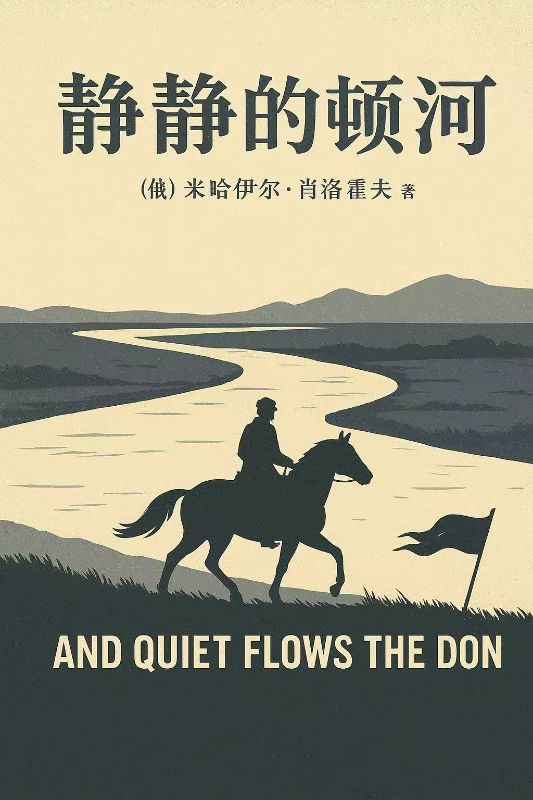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卷 二
第 一 章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莫霍夫的家世,有很悠久的曆史。
在彼得一世統治的時期,有一次,一艘官船滿載著幹糧和火藥, 沿著頓河向亞速海駛去。頓河上遊,離霍皮奧爾河口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叫奇戈納克的“強盜”市鎮,這個小鎮的哥薩克在夜裏偷襲了這隻船,殺死了正在酣睡的守衛,把幹糧和火藥搶劫一空,把船也鑿沉了。
按照沙皇的命令,從沃羅涅什①派來了軍隊,把那個強盜市鎮 奇戈納克燒光了,在戰鬥中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參加過搶船的哥薩克 全都擊潰,把俘虜的亞基爾卡大尉和另外四十名哥薩克在水上絞刑 架上絞死;為了恫嚇下遊騷動的村鎮,把絞刑架順流放到頓河下遊 去。
十多年後,在奇戈納克的舊址上,重又炊煙繚繞,許多新移來的 和那些劫後幸存的哥薩克又在那裏定居下來。市鎮重又發展起來, 並修築了一道環鎮圍牆。從那時候起,從沃羅涅什派來一名皇家坐 探和眼線——農民莫霍夫·尼基什卡。他販賣各種哥薩克日常生活 中必需的雜貨:刀柄,煙草,火石等等;他也買賣贓物,而且每年要到 沃羅涅什去兩次,表麵上是去辦貨,實際上是去報告,說鎮上目前還 算安靜,哥薩克也沒有策劃什麼新的叛亂。
這個莫霍夫·尼基什卡後來繁衍成了商人莫霍夫家族。他們在 哥薩克的土地上牢牢地紮下了根。在鎮上撒下了種籽,而且繁衍起 來,就像野草一樣拔也拔不淨;他們神聖地保存著沃羅涅什督軍派遣 他們的祖先到這個叛亂集鎮時頒發的、已經破爛不堪的證書。如果 不是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的祖父還在世時的一場大火,把藏在神龕
———————————
① 沃羅涅什是南俄的重鎮,位於頓河支流,沃羅涅什河邊。
裏裝著證書的錦匣燒掉的話,也許會一直保存到今天呢。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的祖父因為喜歡賭博,弄得傾家蕩產;他原要重振家業, 可是大火又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燒光了,所以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就不得不又重新創業。他埋葬了癱瘓的父親以後,拿一個已經磨損得盡是麻坑的盧布做本錢,幹起事業來了。起初他走村串巷,收購豬鬃和鵝毛。過了五年的窮日子,一戈比一戈比地欺騙和榨取附近各村的哥薩克,可是後來他不知怎麼地,搖身一變,收破爛的謝廖什卡① 就成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了,在鎮上開了一個小雜貨鋪,和半瘋半傻的神甫女兒結了婚,拿到了一筆相當可觀的陪嫁錢②,又開了個布店。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的布店開的正是時候。依照軍區政府的命令,開始把頓河左岸各鄉鎮轄區內的哥薩克整村整莊地遷移到右岸來,因為左岸的土地貧瘠,都是像石頭一樣硬的黃沙地。一個新的克拉斯諾庫特斯克鎮發展起來;新建房舍天天在增加。在與原屬地主土地交界的地方,在奇爾河、黑河和弗羅洛夫卡河的兩岸,在草原上的山穀和窪地裏,一直到烏克蘭小村莊一帶的廣闊區域內,出現了許多新的村莊。過去買東西,常要跑到五十多俄裏以外去,可是, 現在這裏開了一家新鋪子,一色的新鬆木貨架,架子上擺滿了誘人的布匹綢緞。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的事業就像一隻拉滿了的三排鍵的手風琴一樣,全麵地發展起來;除了布匹綢緞以外,凡是鄉民的樸素生活必需的一切東西他都販賣:皮革製品、鹽、煤油和服飾用品,一應俱全。近來連農業機器都賣了。從阿克薩伊斯克的工廠裏運來的收割機、播種機、犁、風車和選種機都整整齊齊地排列在臨時搭起、漆成綠色的、涼爽的夏季店麵前。當然別人口袋裏的錢是很難計算的, 但是看得出,機靈的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的生意賺了很多錢。三年後,他開了一個糧店,又過一年,在第一個妻子去世以後,又在著手修建一座機器磨坊了。
他把韃靼村和附近的村莊都牢牢地掌握在他那黝黑的、生著一
———————————
① 謝爾蓋的愛稱。
② 俄國舊俗:嫁女兒要陪送嫁妝,身份高,有錢的人,除一般的嫁妝外,還須陪送大量的財物,女兒有缺陷,則陪送的要更多,才有人肯娶。
層稀疏的亮晶晶的黑絨毛的小拳頭裏。沒有一家不欠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的債:一張張印著橙黃邊的綠色借據——有的是買收割機欠的,有的是為了女兒置辦嫁妝欠的(因為嫁姑娘的時候到了,而帕拉莫諾夫糧店又把小麥價格壓得很低,所以都到這裏來求他:“賒給我們一點吧,普拉托諾維奇!”),要賒欠的東西還多著呢……磨坊裏有九個工人,鋪子裏七個夥計,家裏有四個傭人——他們這二十張嘴都是靠買賣人的恩典吃飯的。第一個妻子給他留下了兩個孩子:一個是姑娘麗莎①,一個是比她小兩歲的、瘦弱多病、萎靡不振的男孩弗拉基米爾。第二個妻子是個骨瘦如柴、窄鼻梁的女人,叫安娜·伊萬諾夫娜,她沒有生過孩子。她把那晚來的、從未顯示過的母愛,以及長期鬱積在心裏的苦惱(她已經三十四歲了才嫁給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全都傾注到前妻留下來的孩子身上了。後母神經質的性格, 對於子女的教養沒有產生好影響,至於父親對他們的關心,也並不比對馬夫尼基塔或者廚娘的關心更多一點。做買賣、跑生意占去了他的全部時間:一會兒去莫斯科,一會兒去下諾夫戈羅德,一會兒去烏留平斯克,一會兒又去各鄉鎮的市集。孩子在沒有人照顧的情況下成長起來。並不敏感的安娜·伊萬諾夫娜根本不想深入了解孩子心靈上的秘密——繁多的家務使她顧不到這些——因此姐弟倆在成長過程中,互不理解,非常陌生,性格各異,根本不像親生姐弟。弗拉基米爾成了一個性格孤僻、精神萎靡的人,總是愁眉苦臉,流露出一種不是兒童應有的嚴肅神色。而麗莎卻是混在女仆和廚娘中間,在放蕩、見過世麵的娘兒們群中長大,她很早就看到了生活的醜惡麵。婦人使她產生了一種不健康的好奇心,當她還是一個幼稚、羞澀的少女時,就像荒林中的毒莓一樣,自生自長起來。
歲月悠悠逝去。
老年人照例是更老了;而年輕人卻像一片茂盛的叢林長起來了。 有一次喝晚茶的時候,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瞥了女兒一眼,不
禁大吃一驚(伊麗莎白這時候已經中學畢業,出落成一個引人注目的美貌的少女);他看了一眼,手裏盛著琥珀色茶水的茶碟顫抖了起來;
———————————
① 麗莎是伊麗莎白的愛稱。
“真像去世的母親。我的上帝,簡直太像啦!”他叫了一聲:“麗茲卡①,把臉轉過來!”竟沒有注意到,女兒從小就酷似母親。
……弗拉基米爾·莫霍夫是個瘦弱的、臉色焦黃的小夥子,中學五年級的學生,他常到磨坊的院子裏去玩。不久前,他和姐姐一同回來過暑假,弗拉基米爾和往常一樣,回來以後總要到磨坊裏去看看, 在渾身是麵粉的人群中亂闖,聽聽那有節奏的磨粉機和齒輪的轟隆聲,滑動的皮帶的沙沙聲。他喜歡聽來磨麵粉的哥薩克們小聲的恭維:
“少東家……”
弗拉基米爾小心地繞過滿院子的牛糞堆和車輛,走到木柵門口, 忽然想起來還沒有到機器間去過,他就又回來了。
磨粉工人季莫費和綽號叫做“鉤兒”②的磅秤工人,以及磨粉工 的助手、一口白牙的小夥子達維德卡,都把褲腿卷到膝蓋上麵,正在 機器間入口處、紅色儲油罐旁邊和著一大堆粘土。
“啊啊,東家!……”“鉤兒”露出嘲笑的神情向他問候道。 “你們好呀。”
“你好,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 “你們這是幹什麼?……”
“我們在和泥哪,”達維德卡艱難地從散發著牲口糞臭味兒的粘 泥裏往外拔著腿,惡意地微笑說。“你爸爸舍不得花一個盧布去雇女工,就逼著我們來幹這種活兒。你爸爸真是個守財奴!”他咕唧咕唧地挪動著兩條腿,又補充說。
弗拉基米爾的臉立刻漲紅了。他對這個總是麵帶微笑的達維德 卡,對他這種輕慢的腔調,甚至對他的雪白牙齒,產生了一種無法壓 製的敵意。
“怎麼是守財奴呢?”
“就是。他吝嗇得要命。連自己拉的屎都要再吃下去,”達維德卡簡單地解釋說,還微微一笑。
———————————
① 也是伊麗莎白的愛稱。
② 原文的意思是撲克牌中的“ J”,意即這個工人的身形像“鉤子”。
“鉤兒”和季莫費都讚賞地笑了起來。弗拉基米爾覺得受到了刺 心的侮辱。他冷冷地打量了一下達維德卡。
“那麼說……你是很不滿意啦。”
“你過來,和一下泥試試看,你就明白啦。什麼樣的傻瓜會滿意呢?應該把你爸爸弄到這兒來,叫他的大肚子晃蕩晃蕩才好呢!”
達維德卡搖晃著身子,艱難地在粘泥裏走著圈子,把腳抬得很 高,現在他已經是在毫無惡意地、愉快地笑了。弗拉基米爾感到一絲 的快意,他搜盡枯腸,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回答。
“好,”他一字一板地說道,“我去告訴爸爸,就說你不滿意這裏的工作。”
他斜睨了一下達維德卡的臉,這句話所產生的效果使他吃了一 驚:達維德卡的嘴唇既可憐,又勉強地笑著,另外兩個人也皺起了眉 頭。三個人都一聲不響地在稀溜溜的粘泥裏和了一會兒。最後達維 德卡把眼睛從臟腳上移開,恨恨地、結結巴巴地說道:
“我是說著玩哪,沃洛佳①……喂,我是說著玩哪……” “我要把你說的話全都告訴爸爸。”
弗拉基米爾為父親和自己受到的侮辱,為達維德卡可憐的笑容 感到難過的眼淚正奪眶而出,便繞過油罐走去。
“沃洛佳!……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達維德卡驚 呼道,跳出爛泥堆,把褲腿從濺滿汙泥的膝蓋上擼下來。
弗拉基米爾停了下來。達維德卡跑到他的麵前,上氣不接下氣 地央告說:
“不要告訴你爸爸啦。我是逗你玩才說的……請原諒我這個傻 瓜……真的,我沒有惡意!……是為逗你玩才說的……”
“好吧。我不告訴啦!……”弗拉基米爾皺著眉頭喊道,然後向 板柵門走去。
可憐達維德卡的心情占了上風。他懷著輕鬆的心情,順著板柵 走去。從磨坊院子角落裏的鐵匠作坊那裏傳來雜亂的打鐵聲:先在 鐵上敲一下——聲音喑啞、柔和,再在錚錚響的鐵砧子上打兩下——
———————————
① 弗拉基米爾的愛稱。
發出叮當的響聲。
“你惹他幹什麼?”“鉤兒”壓抑的低音傳到正走開去的弗拉基米爾的耳朵裏。“不碰他,就不會散發出臭味來啦。”
“瞧這混蛋,”弗拉基米爾恨恨地想,“罵得多難聽……告不告訴父親呢?”
他回頭看了看,又看到了達維德卡往常那種露出白牙齒的笑容, 於是下了決心:“要告訴父親!”
商店前的廣場上,停著一輛套好的大車,馬拴在拴馬樁上。一群 孩子正在從消防棚子的頂上轟一群灰色的、唧唧喳喳叫的麻雀。從 陽台上傳來大學生博亞雷什金的洪亮的男中音和另一個人沙啞的顫 音。
弗拉基米爾走上台階,爬滿台階和陽台的野葡萄的葉子在他頭
頂上飄動,它們從藍色飛簷的雕花上垂下來,像一頂頂鼓脹起來的綠 帽子。
博亞雷什金搖著剃得光光的紫紅色腦袋,對坐在他旁邊的、年輕 但是卻留著大胡子的教師巴蘭達說道:
“雖然我是一個哥薩克農民的兒子,對一切特權階級懷有一種非 常自然的仇恨,可是您簡直想不到——讀他的作品,我竟非常可憐起 這個垂死的階級來了。我自己幾乎要變成貴族和地主了,狂熱地研 究起他們理想中的婦女,為他們的利益擔心,——總而言之,鬼知道 是怎麼一回事!親愛的,您看,天才有多麼巨大的威力!它可以改變 你的信仰。”
巴蘭達玩弄著絲帶的穗子,譏諷地笑著,仔細打量著襯衫前襟上 絨線編的紅花。麗莎懶洋洋地坐在沙發椅裏。顯然,她對客人的談 話毫無興趣。她那總像是丟失了什麼東西和在尋找什麼東西的目光 在無聊地看著博亞雷什金傷痕斑斑的紫色腦袋。
弗拉基米爾行了個禮,走了過去,敲了敲父親書房的門。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正坐在皮涼椅上,翻閱六月份的《俄羅斯財富》①。
———————————
① 《俄羅斯財富》是在彼得堡出版的月刊。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成為民粹派的機關刊物。
地板上放著一把骨柄已經發黃的裁紙刀。“你有什麼事?”
弗拉基米爾把腦袋往肩膀裏縮了縮,神經質地理了理身上穿的 襯衣。
“我剛從磨坊裏回來……”他遲疑地開口說,但是他看著父親裹 在絲綢背心裏的圓滾滾的肚子,想起了達維德卡的刺眼的笑容,就堅決地說了下去:“……聽見達維德卡說……”
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仔細地聽完他說的話,然後說道: “咱們叫他滾蛋。你去吧。”他哼哼著彎下腰去拾裁紙刀。
晚上,村裏的知識分子都來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家裏聚會:博 亞雷什金——莫斯科技術學校的學生;幹瘦、自命不凡、患肺病的教 師巴蘭達;他的姘頭,女教師瑪爾法·格拉西莫芙娜——一個圓滾滾 的、總也不見老的大姑娘,她的襯裙總是很不雅觀地露在外麵;郵政 局長是一個古裏古怪、身上又臟又臭、總是散發著火漆和便宜香水氣 味的光棍漢。年輕的騎兵中尉葉甫蓋尼·利斯特尼茨基也偶爾從自 己的莊園上到這裏來,他正在父親——貴族地主——處小住。他們 坐在陽台上喝茶,扯些毫無意義的話,等到無精打采的談話中斷的時 候,客人中的一位就會去把主人那鑲著寶石的貴重留聲機開開。
有時候,在重大的節日,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很歡喜顯顯闊氣:
大宴賓客,請他們喝貴重的酒,吃特地從巴塔伊斯克定來的新鮮鱘魚子和上等的菜肴。平常日子,他過得很儉省。隻有一件事情是例外: 他從不吝嗇買書的錢。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很喜歡看書,對什麼都要用自己像菟絲似的頑強的頭腦去研究一番。
他的合夥股東葉梅利揚·康斯坦丁諾維奇·阿捷平是個淺黃頭發、蓄著尖尖的小羊角胡子和眼睛深藏在細眼縫裏的人,他很少到這裏來。他跟梅德維季河口修道院的一個還俗的尼姑結了婚,同她過了十五年夫妻生活,共生了八個孩子,他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家裏。 葉梅利揚·康斯坦丁諾維奇是從當團隊文書發跡的,他把軍隊裏那種拍馬和奉承的腐敗習氣也帶回家裏來了。孩子們在他麵前都要踮著腳尖走路,小聲說話。每天早晨,孩子們盥洗完畢,就在餐廳裏掛的像口黑棺材似的大鐘下排成一隊,母親站在隊後,一聽到父親的幹咳
聲從臥室裏傳來,立即開始用各種聲調,裝腔作勢地依次朗誦禱詞:
《主啊!救救你的子民吧》和《我們的父》。
葉梅利揚·康斯坦丁諾維奇正好在他們禱告完了,也就穿好衣 服,走出臥室,來到餐廳,眯縫著白菜葉色的小綠眼睛,像大主教似的 伸出一隻肥胖的光手。孩子們依次走過去親吻。葉梅利揚·康斯坦丁諾維奇吻過妻子的臉頰,就開口了,“奇”音總是發得模糊不清,成了“茨”音:
“波莉茨(奇)珈,擦(茶)泡上了嗎?” “泡上啦,葉梅利揚·康斯坦丁諾維奇。” “倒一杯濃一點的。”
他管理商店的會計事務。在每頁的“借方”和“貸方”的粗體字欄下,都寫滿了文書們慣用的、花哨字體的數字。他每天讀《市場報》, 毫無必要地在疙疙瘩瘩的鼻子上帶上金框夾鼻眼鏡。對待店員們卻很客氣。
“伊萬·彼得羅維茨(奇)!請您給這位鄉親量幾尺道利花布。”他的妻子稱呼他葉梅利揚·康斯坦丁諾維奇,孩子們都叫他金
(親)愛的爸爸,店夥都叫他“擦擦兒”。
兩個神甫——威薩裏昂神甫和監督司祭潘克拉季——都和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沒有什麼交往,因為他們跟他有宿怨。兩個神甫彼此也不很和睦。剛愎自用、喜歡挑撥是非的潘克拉季最善於在鄰裏之間製造不和;而威薩裏昂是個單身漢,跟烏克蘭女管家姘居在一起,因為生梅毒所以說話甕聲甕氣,他生性隨和,所以很少與這位監督司祭來往,而且不太喜歡司祭那種自高自大和愛撥弄是非的性格。
除了教師巴蘭達以外,其餘的人在村子裏都有了自己的私宅。莫霍夫那油漆成藍色的、薄鐵頂的宅子坐落在廣場上。商店就在家對麵——聳立在廣場正中央,裝著玻璃門,掛著一塊褪了色的招牌:
謝·普·莫霍夫與葉·康·阿捷平合營商店
和商店毗連著的是一長排有地窖的低矮板棚,離這裏約二十沙 繩,是教堂的圓形磚圍牆和圓頂的教堂,這圓頂很像是熟透了的綠洋 蔥頭。教堂對麵,是一帶粉刷得莊嚴、肅穆的學校圍牆和兩座漂亮房
子:一座是淺藍色的,花園的木柵欄也漆成同樣的顏色,那是潘克拉季司祭的;一座是褐色的(避免兩座房子一樣)、有雕飾的圍牆和寬大的陽台,那是威薩裏昂神甫的。然後從這個街角直拐到另一個街角, 是阿捷平的怪模怪樣、狹長的二層小樓;再過去,就是郵局、哥薩克的草頂或鐵皮頂的家舍,屋頂傾斜,上麵裝著一隻生鏽的鐵公雞的磨坊。
村子裏的人關上裏裏外外的百葉窗,過著與世隔離的幽靜生活, 如果不去作客,天一黑就都把門閂上,放開鐵鏈鎖著的狗,寂靜的村子裏就隻聽到更夫的梆子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