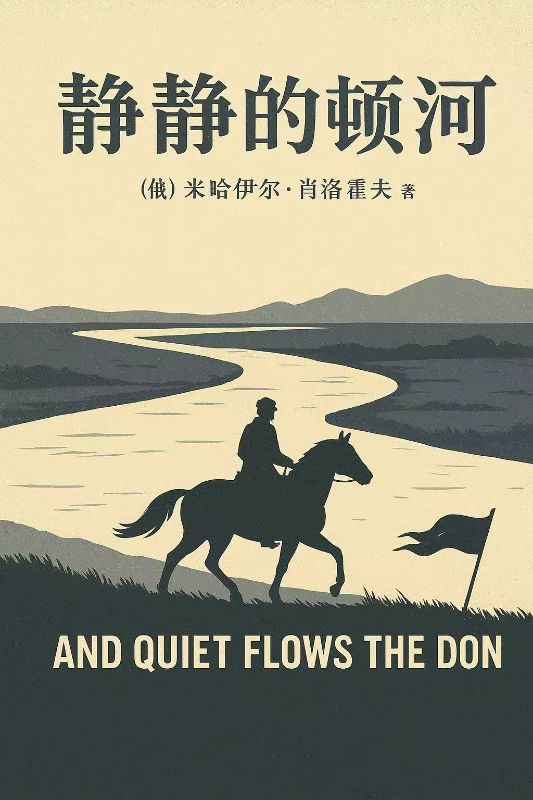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 二 章
第 二 章
灰色黎明的天空上閃爍著稀疏的晨星。風從黑雲片下吹來。頓 河上,霧氣奔騰,在白堊山峰的斜坡上盤旋,像條沒有腦袋的灰色巨 蛇,爬進了峽穀。左岸的河汊、沙灘、湖沼、葦塘和披著露水的樹 林——都籠罩在一片涼爽迷人的朝霞裏。太陽還在地平線後麵懶洋
———————————
① 杜妮亞什卡是葉芙多基亞的小名。
洋地不肯升上來。
麥列霍夫一家人,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第一個醒來。他一麵 走著,一麵扣著繡有小十字架的襯衫領子,來到台階上。長滿了青草 的院子到處閃著銀色的朝露。他把牲口放到街上去。達麗亞隻穿著 一件襯衣跑去擠牛奶。她的兩條白皙的光腿上濺滿了像新鮮乳汁似 的露水珠,院子裏的草地上留下了一串煙色的腳印。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朝著那被達麗亞踩倒、又慢慢挺直起來 的小草看了看,便走進內室去了。
開著窗戶的窗台上落滿了小花園裏已經開敗了的、毫無生氣的 粉紅色櫻桃花瓣。葛利高裏一隻手伸出床外,在趴著睡覺。
“葛利什卡①,你去釣魚嗎?”
“你說什麼?”葛利高裏小聲問道,把兩條腿從床上耷拉下來。 “咱們釣魚去,可以釣到太陽出來。”
葛利高裏哼哧著,從掛衣鉤上扯下一條便服褲子穿上,把褲腿塞 進白色的毛襪筒裏,扳正歪斜的鞋後跟,半天才穿上了皮靴子。
“媽媽做好魚食了嗎?”跟著父親朝門洞裏走的時候,他嘶啞地問 道。
“做好啦。你先到船上去吧,我立刻就來。”
老頭子把冒著熱氣的、噴香的黑麥裝進壇子,仔細地把落到外麵 的麥粒撿到手巴掌裏,然後跛著左腳,一瘸一拐地向坡下走去。葛利 高裏無精打采地坐在船裏。
“往哪兒劃?”
“到黑石崖去。到前兩天咱們在上麵坐過的那棵倒在水裏的樹 旁試試看。”
小船的船尾滑下土岸,漂進水中,離開了河岸。激流卷起小船, 搖晃著,極力要把它橫過來。葛利高裏並不劃船,隻用船槳撥正方向。
“你劃呀。”
“等漂到河中流再劃。”
———————————
① 葛利高裏的愛稱。
小船橫過中流,向左岸漂去。從村子裏傳來公雞的叫聲,在河 上,這啼聲變得低沉多了。船舷擦著陡立在水中的黑黢黢的石礫斷 崖,停在崖下的河灣裏。離河岸五沙繩遠的地方,可以看見那棵沉到 水底去的榆樹伸出的樹枝。漩渦在榆樹四周追逐著褐色的泡沫。
“捯開釣線,我來下食,”父親悄悄對葛利高裏說,一隻手塞進了冒著熱氣的壇子口裏。
黑麥粒聲音清晰地濺落到水中,發出一陣噝的響聲,就像有人發 出的低沉的噓聲。葛利高裏把幾粒鼓脹的黑麥安到鉤子上,露出了 笑容。
“吃呀,吃,大魚小魚都來吃。”
抖成圈子落到水裏去的釣魚線像弦一樣拉直了,然後又彎下去, 差不多沉到水底去了。葛利高裏用腳踩著釣竿的手柄,竭力不使身子搖動,爬過去拿煙荷包。
“爸爸,今天運氣好不了……月亮還不圓呢。” “你帶著火柴嗎?”
“帶著哪。” “給我點個火。”
老頭子抽著煙,瞅了瞅浸在水中的大樹那麵遲遲沒有升起的太
陽。
“鯉魚不一定什麼時候出來。有時候月亮不圓也出來咬食。” “你聽,好像小魚在咬食,”葛利高裏鬆了口氣說。
小船附近的水撲哧響了一聲,泛起了波紋,一條有兩俄尺長的、
好像紅銅鑄的鯉魚,彎起寬大的尾巴,在水麵上拍了兩下,叫著向空 躍起。珍珠般的水花濺了一船。
“現在你等著瞧吧,”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用袖子擦了擦濕漉 漉的大胡子。
浸在水裏的榆樹周圍,在那些有胳膊粗的禿樹枝中間,同時跳出 兩條鯉魚;第三條小一些,在空中打著旋兒,一次又一次地、頑強地往 崖石上撞。
葛利高裏在焦急地嚼著濕透了的煙頭。不很耀眼的太陽已經升
到半棵橡樹高了。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撒完了所有的魚食,喪氣 地噘起嘴,呆呆地望著那一動不動的釣竿頭。
葛利高裏啐出煙頭,恨恨地望著它迅速地飛去。他心裏在咒罵父親,老早就把他叫醒,不讓他睡夠。因為空肚子抽煙,嘴裏有一股燒焦頭發的惡臭。他正要彎下身子,用手去捧口水喝,——這時候, 離水麵有半俄尺①的釣竿頭輕輕地抖了一下,慢慢向下彎去。
“咬鉤啦!”老頭子舒了口氣說。
葛利高裏抖擻精神,拉了一下釣竿,但是竿梢立即彎進水去,釣 竿從手攥著的地方彎成了弓形。一股巨大的力量,像絞車似的把繃 得緊緊的紅柳木釣竿向下拉去。
“攥住!”老頭子哼哼著,把船從岸邊撐開。
葛利高裏竭力想把釣竿舉起,但是辦不到。很粗的釣線哢的一 聲斷了。葛利高裏因為失去了平衡,身子搖晃了一下。
“簡直像條公牛!”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悄悄地說道,怎麼也不能把魚餌安到魚鉤上。
葛利高裏激動地笑著,拴上新釣線,又拋了出去。 釣線上的鉛錘剛沉到河底——竿梢就彎了下去。
“你看,這壞蛋!……”葛利高裏哼了一聲,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把 那條向激流衝闖的魚從水底拉出來。
釣線刺耳地響著,劃破水麵,沿著釣線,垂下一道淺綠色的水簾。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用短粗的手指頭在捯動著撈網的木柄。
“先在水裏把它蹓乏啦!頂住勁,不然釣線又要被它掙斷啦!” “放心吧!”
一條金紅色的大鯉魚浮到了水麵上來;攪起了一片白沫,它把扁 平的大腦袋往下一紮,又向深處遊去。
“好大的勁兒,手都麻啦……好啊,你等著瞧吧!” “頂住,葛利什卡!”
“頂著哪——啊——啊!” “當心,別讓它鑽到船底下去!……當心!”
———————————
① 一俄尺等於○.七一公尺。
葛利高裏喘著氣,把斜著身子的鯉魚拉到船邊來。老頭子拿著 撈網正要彎下身子去撈,但是鯉魚鼓起最後的勁兒,又紮進水底去 了。
“把它的腦袋提起來!叫它喝點風,就會老實點兒啦。”
葛利高裏拉起了鯉魚腦袋,又把這條折騰得疲憊不堪的鯉魚拖 到船邊來。鯉魚大張著嘴吸氣,鼻子頂到粗糙的船舷上,搧動著金光 閃閃的橙黃色的鰭,不動彈了。
“折騰夠啦!”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用撈網撈著魚,呷呷地說道。
他們又呆了半個鐘頭,釣鯉魚的戰鬥才結束了。
“收起釣線來吧,葛利什卡。大概咱們把最後一條都釣上來啦, 再不會有啦。”
他們收拾完了。葛利高裏把船從岸邊劃開。劃了有一半路程的 時候,葛利高裏看見父親臉上的表情好像是要說什麼,但是老頭子卻 隻在默默地眺望山腳下村子裏的宅院。
“你,葛利高裏,聽我說……”他一邊摸索著腳底下麻袋上的繩結,一邊遲遲疑疑地開口說道,“我看得出,你跟阿克西妮亞·阿司塔霍娃有點兒……”
葛利高裏的臉立刻漲得通紅,扭過頭去。襯衫領子勒進筋肉發 達、被太陽曬黑了的脖子,勒出了一道白印。
“你當心點兒,小夥子,”老頭子已經是凶狠地、氣衝衝地繼續說道,“我可不是跟你說著玩的。司捷潘是咱們的鄰居,我不準你調戲他的老婆。這會造孽的,我預先警告你:要是叫我察覺了——我要用鞭子抽你!”
潘苔萊·普羅珂菲耶維奇把手指頭攥成疙疙瘩瘩的拳頭,眯縫著 鼓出的眼睛,看著兒子的臉變得煞白。
“都是謠言!”葛利高裏目不轉睛地直盯著父親發青的鼻梁,含糊 不清地嘟囔說,那聲音好像是從水裏冒出來的。
“你給我住嘴。”
“人們什麼話都編得出來……” “住嘴,狗崽子!”
葛利高裏彎身劃起槳來,小船一衝一衝地前進。水在船尾打著 旋兒,嘩嘩地響著。
一直到碼頭,兩個人都沒有再說話。船快要靠岸的時候,父親又 提醒說:
“留神,別忘了,要不——從今天起,就再別去遊戲場。一步也不許走出院子。就是這樣!”
葛利高裏沒有說話。他把小船靠了岸,問道: “把魚拿回家交給娘兒們嗎?”
“拿去賣給商人吧,”老頭子口氣溫和了一些,“錢留著你買煙抽吧。”
葛利高裏咬著嘴唇,走在父親後麵。“你算了吧,爸爸,就是你把 我的腳捆起來,今天我還是要上遊戲場去,”他一麵惡狠狠地盯著父 親扁平的後腦勺子,一麵心裏想。
葛利高裏在家裏仔細地把鯉魚鱗上的幹沙子洗淨,用柳條拴著 魚鰓。
他在大門口遇見了同年齡的好友米吉卡①·科爾舒諾夫。米吉 卡一麵走著,一麵玩弄著鑲著銀飾的皮帶頭,兩隻圓滾滾的、土黃色 的眼睛,在細窄的眼縫裏閃著黃澄澄的油亮的光澤。兩個瞳人像貓 眼似的朝上翻著,因此米吉卡的目光就顯得變幻莫測,難以捉摸。
“你拿著魚上哪兒去?”
“這是今天的戰利品。拿到買賣人那裏去。” “給莫霍夫家嗎?”
“是給他家。”
米吉卡用眼睛估量了一下鯉魚的重量。“有十五俄磅②吧?”
“還多半磅呢。我稱過啦。”
“帶我一塊兒去吧,我會幫你做買賣的。” “走吧。”
———————————
① 米吉卡是德米特裏的愛稱。
② 一俄磅等於四○九.五克。
“請客嗎?”
“那好說,別說廢話啦。”
做完禱告回來的人散滿了街道。
沙米利家的三弟兄也在路上並排走著。
大哥,獨臂的阿列克謝,走在中間。窄小的製服領子把他那筋肉 發達的脖頸勒得筆直,鬈曲、稀疏的小山羊胡子神氣活現地往一邊翹 著,左眼神經質地眨個不停。很久以前,在射擊場上,阿列克謝手裏 的步槍炸裂了,槍栓的碎塊打傷了他的腮幫子。從那時起,這隻眼睛 就有事沒事地眨個不停;淺藍色的傷痕橫過臉頰,一直伸到頭發裏 去。左手被從肘部炸去,但是阿列克謝卻能很巧妙、準確地用一隻手 卷煙:他把煙荷包夾在凸出的胸膛上,用牙咬下一塊夠用的紙片,把 紙片半卷起,倒進煙草,手指頭便巧妙地、簡直是難以察覺地卷了起 來。你還沒有看清是怎麼回事,阿列克謝已經眨著眼睛叼起卷好的 煙,在向人借火了。
他雖然僅有一隻胳膊,但卻是村子裏最好的拳擊家。他的拳頭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隻不過桃南瓜那樣大。可是有一次耕地的時候,他對公牛生起氣來,因為鞭子丟掉了,就用拳頭捶了公牛一下。 公牛倒在犁溝裏,從耳朵裏流出血來,好容易才把牛治好了。兩個兄弟,一個叫馬丁,一個叫普羅霍爾,都很像阿列克謝,就像一個模子倒出來的:也是那樣身材短粗,像棵橡樹,不同的是他們都有兩隻胳膊。
葛利高裏跟沙米利弟兄們打招呼,米吉卡卻把腦袋扭得咯吧咯 吧地響,走了過去。這是因為謝肉節時在拳鬥場上,阿廖什卡①·沙 米利毫不憐惜米吉卡的嬌嫩牙齒,照著臉上猛擊一拳,米吉卡就把兩 個槽牙吐在被皮靴上的鐵後跟踏碎的藍灰色冰塊上。
阿列克謝走到他們跟前,一連眨了五次眼睛。 “是賣劈柴棍子②嗎?”
“你買吧。” “要多少錢?”
———————————
① 阿廖什卡是阿列克謝的愛稱。
② 指魚。
“一對公牛,外加一個媳婦①。”
阿列克謝皺著眉,把那半截胳膊揮了一下。
“怪物,啊呀,怪物!……噢哈哈,外加一個媳婦……你還要牛犢 子嗎?”
“你自個留著傳種接代吧,不然的話,你們沙米利家就會絕種啦,”葛利高裏粗野地嘲笑說。
廣場上,教堂圍牆旁邊聚了一群人。教會長老正在人群裏把一隻鵝舉在頭頂上,喊叫道:“半個盧布,有人給過價錢啦。誰還肯多出?”
鵝扭動著長脖子,藐視地眯縫著碧玉般的眼睛。
旁邊的一個圈子裏,一位灰白頭發、胸前掛滿十字章和獎章的小 老頭正在揮舞胳膊。
“我家的格裏沙卡爺爺又在講土耳其戰爭的故事啦,”米吉卡向 那邊瞟了一眼。“咱們去聽聽嗎?”
“咱們聽故事的時候,鯉魚可就要臭啦,鼓脹起來。” “脹起來會加重分量,對咱們有利。”
在廣場上,消防棚子後麵,露出莫霍夫家的綠色房頂,消防棚裏 扔著幾輛斷了車杆的、水桶幹裂的消防車。走過消防棚的時候,葛利 高裏啐了一口唾沫,掩住鼻子。從破爛的消防車後麵走出一個老頭 子,他嘴裏叼著皮帶扣,一邊走,一邊扣著肥大的燈籠褲的扣子。
“憋不住啦?”米吉卡挖苦地問道。
老頭子扣上了最後一個扣子,從嘴裏拿出皮帶扣,問道: “跟你有什麼相幹?”
“應當把你的鼻子按進屎裏去!把大胡子,你的大胡子在裏麵蘸 蘸才好!叫你的老太婆洗一個星期也洗不幹淨。”
“我把你這個壞小子按進去!”老頭子發火了。
米吉卡停了下來,像怕陽光一樣眯縫起貓似的眼睛。
“瞧,你有多文明。你給我滾開,狗崽子!你在這裏糾纏什麼? 不然,我要拿皮帶抽你啦!”
———————————
① 指母牛。
葛利高裏跟米吉卡說笑著,走到莫霍夫家的台階下邊。欄杆上 密密麻麻地雕著一嘟嚕一嘟嚕的野葡萄。台階上灑滿斑斑點點的懶 洋洋的陰影。
“你瞧呀,米特裏①,人家過的什麼日子……” “門把手都是鍍金的。”米吉卡推開通到陽台的門,嘮叨說:“要把
剛才那位老大爺送到這裏就好了……” “誰呀?”陽台上有人問他們。
葛利高裏膽怯地頭一個走了進去。鯉魚的尾巴掃著油漆的地
板。
“您找誰?”
一個姑娘坐在藤搖椅上。她手裏端著一個裝著楊梅的碟子。葛 利高裏一聲不響地望著她那豐滿的、吃過楊梅的紅豔的心形嘴唇。 姑娘低下頭,打量著走進來的人。
米吉卡立即來幫葛利高裏說話。他先咳嗽了一聲。 “你們買魚嗎?”
“魚?我這就去說一聲。”
她搖了一下椅子,站起身來,兩隻光腳穿的繡花拖鞋,啪嗒啪嗒響了起來。陽光照透了她的潔白的衣裙,於是米吉卡看見了兩條胖腿的模糊輪廓和襯裙上擺動著的寬花邊。兩條光腿肚那種滑膩、白嫩樣子使他感到驚訝,隻有兩個圓圓的腳後跟上的皮膚略呈乳黃色。
米吉卡推了推葛利高裏。
“瞧,葛利什卡,你看這裙子……像玻璃一樣,什麼都看得一清二 楚。”
姑娘從過道的門裏走過來,輕輕地坐在圈椅裏。 “請到廚房裏去吧。”
葛利高裏踮著腳尖向屋子裏走去。米吉卡伸出一隻腳站在那 裏,眯縫著眼睛瞅著把姑娘的頭發分成了兩個金黃色半圓形的那道 白印。姑娘則用頑皮不安的眼睛打量著他。
“您是本地人嗎?”
———————————
① 米特裏是德米特裏的簡稱。
“是本地人。” “是誰家呢?” “科爾舒諾夫家。” “您叫什麼名字?” “米特裏。”
她仔細地看了看自己那粉紅色、晶瑩的腳趾甲,就趕緊把兩條腿 蜷起來。
“你們倆是誰釣的魚呀?” “葛利高裏,我的好朋友。” “您也釣魚嗎?”
“高興的時候我也釣。” “用釣竿嗎?”
“也用釣竿釣,照我們的說法,叫做用鉤竿釣。” “我也想去釣釣魚,”她沉默了一會兒說道。 “這好辦,要是你高興,咱們就去。”
“當真嗎?不開玩笑。我們怎麼來安排呀?” “要很早就起身。”
“我起得來,不過得有人叫醒我。” “叫醒你是可以的……但是你爸爸呢?” “爸爸怎麼的?”
米吉卡笑了。
“別把我當賊捉!……還會放狗咬。”
“您淨說胡話!我一個人睡在角上的屋子裏。就是這個窗戶。” 她用手指頭指了指。“您來了,敲敲我的窗戶,我就起來啦。”
廚房裏傳來斷斷續續的說話聲:猶豫忐忑的,是葛利高裏的聲 音;重濁、油滑的,是女廚子的聲音。
米吉卡玩弄著哥薩克皮帶上的發烏的銀片,默默不語。 “您結婚了嗎?”姑娘問道,露著隱約的笑容。 “你問這幹什麼?”
“沒有什麼,覺得有趣罷了。” “沒有,還是光棍兒。”
米吉卡的臉忽然漲紅了,可是她微微含笑,玩弄著垂在地板上的 溫室栽培的楊梅枝條,問道:
“怎麼樣,米佳①,姑娘們愛您嗎?” “有些愛我,也有些不愛。”
“請您說說……為什麼您的眼睛很像貓眼睛呢?” “像……貓眼睛?”米吉卡終於給弄得狼狽不堪了。 “一點不錯,完全像貓眼睛。”
“準是從娘胎裏帶來的,……我對此不負任何責任。” “米佳,為什麼還不給您娶親呢?”
米吉卡窘了一會兒,立刻就鎮定下來,覺得她的話裏有一種難以 覺察的諷刺意味,黃眼睛就閃爍起來。
“我的媳婦兒還沒有長大呢。”
她驚異地把眉毛向上一挑,臉漲得通紅,站了起來。 傳來一陣從街上走到台階上來的腳步聲。
她那摻雜著嘲弄的、一閃而過的微笑像蕁麻一樣刺疼了米吉卡。 主人,謝爾蓋·普拉托諾維奇·莫霍夫,輕輕地踏著肥大的軟羊皮靴子,威嚴地挺著肥胖的身軀,從站到一旁去的米吉卡麵前走過。
“是找我嗎?”他走過去的時候問道,連腦袋都沒有扭一扭。 “他們是送魚來的。爸爸。”
葛利高裏空著手走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