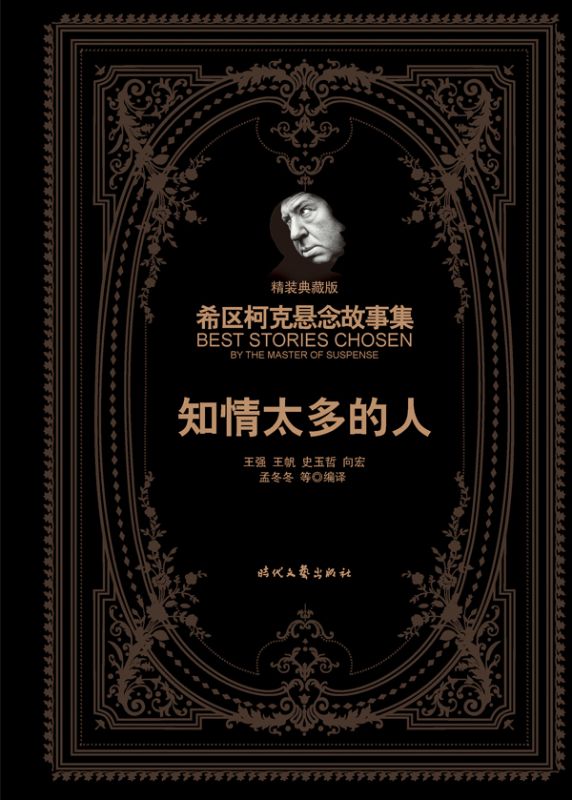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監獄黑幕
新監獄長勞森,星期一中午上任。那天,天空陰沉沉的,下著毛毛細雨。
上任後一個小時,他就舉行了一次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副監獄長、警衛隊長和三個有官銜的警衛。
“諸位,”他坐在辦公桌後麵說,那張辦公桌是前任監獄長上午才騰出來的,“你們知道我是誰,為什麼來這兒。我是州長指派來接替前任監獄長的,州長授權我處理本監獄的一切事務。”
勞森站起來,轉向椅子後麵的窗戶,看著外麵的大院,由於四十八小時前的一次暴亂,院子被燒得黑乎乎的。
“兩名囚犯死亡,”勞森冷靜地說,“十六人受傷,其中五名是警衛,還有,”他轉回頭,“損失了好幾萬元公款。”
他坐下來,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舊煙鬥,小心地從一隻皮袋裏拿出煙絲塞進煙鬥裏。裝好煙鬥後,他把煙鬥咬在嘴上,然後劃火柴點著,吸一口,吐出來,灰色的煙在屋裏慢慢散去。“州長向我提出了三項任務,”他說著,把火柴搖滅,扔進煙灰缸,“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須恢複監獄中的秩序;第二,我必須加強和維護內部的安全;第三,我要深入調查這次暴亂的原因,找出主謀。現在,”他往椅背上一靠,“我想聽聽大家對完成第一項任務的意見,也就是說,如何完全恢複監獄中的秩序。”
“我可以回答這一問題,”雷蒙回答道,他是警衛隊長,“實際上,我可以告訴你如何完成這三項任務。把弗蘭克關進洞裏,永遠不放出來。”
“弗蘭克?”勞森想了一下這個名字,手指在椅子的扶手上輕輕敲打著,“弗蘭克?是不是那個專門收購贓物的?他已經在這兒服刑十四五年了吧?”
“十六年,”雷蒙隊長說,“他被判了二十年,他會在這兒服刑到期滿的。三個月前,保釋委員會駁回他的申請,他們給他一個四年的期限,所以,他必須服刑滿二十年。”
“你的意思是說,弗蘭克是關鍵人物?監獄的暴亂就是他引起的?”
“是的,”雷蒙坦率地說,“正是如此。”
“嗯。”勞森說,吐了一口煙,緩緩地點點頭,“其他各位的意見呢?你們同意雷蒙隊長的說法嗎?”
房間裏沉默了一會兒。三位警衛互相看看,沒有說什麼。最後,年輕的副監獄長說話了,他叫吉爾德,他對勞森說:“監獄長,雖然我們很尊重雷蒙隊長的地位和經驗,但是,我很冒昧地說,我不讚成他的說法。我認為雷蒙隊長誇大了弗蘭克在囚犯中的重要性。我認為他的影響並不像雷蒙隊長說得那麼……”
“影響?”雷蒙隊長吼道,“整個監獄裏,每次鬧事,他都是幕後主使者,他控製了每一個有職位的囚犯。”
“不是這樣的,”吉爾德說,“他並沒有控製每一個輔導班的老師……”
“什麼老師!”雷蒙隊長不屑地說,“誰想控製他們?他們在那些囚犯的眼裏根本不算什麼!我說的是控製那些舉足輕重的人——那些在監獄教堂、餐廳、洗衣間有影響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想花點錢讓自己吃得好、過得好的人。”
“你在暗示說,那一切全是由弗蘭克控製的?”勞森問。
“是的,可能還不僅如此,”雷蒙隊長說,“我並不是在暗示,我是在陳述事實。”
“一種沒有事實根據的意見,不能稱之為事實。”副監獄長平靜地說。
“吉爾德說得有理。”新監獄長對雷蒙隊長說,“隊長,你有沒有什麼證據?有沒有什麼確切的指控?”
雷蒙隊長瞥了副監獄長一眼,慍怒地說:“沒有。”
“囚犯中有沒有願意和我們合作調查弗蘭克的人?”勞森問。
雷蒙搖搖頭。
“你們一定有一兩個告密者,”勞森說,“我從沒見過沒有告密者的監獄。”
“當然有,”雷蒙承認說,“我們是有內線,他們會把任何一名囚犯的事告訴我們……弗蘭克除外。”
“這麼說,我們對此無能為力了?”
“除非你接受我的意見,把他孤立起來,否則就沒有。”雷蒙的語氣有些僵硬地說。
勞森的手指又在桌麵上敲打起來,然後說:“這件事讓我考慮一下,我得熟悉這裏的事情,在我做出最後的決定時,我會和你們商量的。同時呢,我想我們最好快點動手,恢複整個監獄的秩序。目前情況怎麼樣?”
“安全上沒有什麼問題,”雷蒙回答說,“A、B兩棟都在我們的控製中,C棟的1號到5號牢房,也都在控製中。C棟的6號牢房,囚犯都被鎖在裏麵,他們在絕食,從上星期六早晨起就沒有進食。”
“你認為他們能熬多久?”
雷蒙摸摸下巴,沉思地說:“最多到星期二中午吧。”
“好,還有什麼別的事嗎?”
“暴亂分子中,有八人仍然占據著鞋廠,他們都沒有武裝……”他意味深長地看看副監獄長,“不過,我們接到指示,不要用武力逼他們出來。”
勞森轉向副監獄長,探詢地揚起眉毛。
“那個廠裏,有價值四千元以上的製鞋設備,”副監獄長解釋說,“如果我們用武力逼他們出來的話,他們就會毀壞那些設備。我已經派神父進去溝通,我想他們會自動出來的,”他掃了雷蒙一眼,“這樣就不必遭受損失了。”
“好,”勞森說,又轉向雷蒙,“還有什麼嗎?”
警衛隊長聳聳肩,“大致就是這樣。隔離囚房一半是滿的,醫務室也差不多滿了。三棟牢房都早早上鎖,暫停各種娛樂活動。”
“很好,”勞森說,“現在,我們這麼辦:繼續早早地鎖上牢門,但是恢複聽收音機和閱讀書籍,絕食的那個牢房除外。今天晚餐的時候,推兩輛有熱騰騰飯菜的餐車過去,給每個絕食者一盤吃的,不論是誰,先吃的人,就可以回到餐廳吃飯。至於在製鞋廠的那些人,讓神父去勸說。”說到這兒,他掃了雷蒙的三位部下一眼,“明天中午之前,我要每棟牢房的主管,寫一份對各牢房情況的報告,附上采取什麼步驟的簡單意見。關於弗蘭克的事,我們以後再研究。”他停了一下,“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問題了。”雷蒙回答說,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他的三位部下也跟著站起來,四個人一起走出去。
屋裏隻剩下勞森和吉爾德兩個人。年輕的副監獄長說:“對剛才的意見我很抱歉,我希望你的第一次會議順利一點。”
“別把這事放在心上。”勞森微笑著說,“說句實話,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也不指望事事順利。”他站起來,把煙鬥塞進嘴角,“我們到餐廳喝杯咖啡,聊一聊。”
囚犯的餐廳很寬敞,不過,現在除了工作人員外,沒有其他人。勞森和吉爾德取過金屬杯,自己動手倒了兩杯咖啡,然後走到附近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來。勞森默默地喝了一會兒咖啡,然後盯著年輕的副手。
“我們才認識,我真不願這麼快就找你來談話,”他坦率地說,“不過,你知道我也是沒有辦法,我想盡快了結此事。你對雷蒙這個人有什麼看法?”
吉爾德勉強一笑,“你倒是很直率。”
“我一般不這麼開門見山,不過,我現在沒有時間了。”
“好,”吉爾德喝了一口咖啡,“雷蒙隊長很能幹,他兩天就平息了監獄的暴亂,要是在別的地方,起碼要拖兩個星期以上。還有,他在這兒十六年,沒有一個越獄的。但是在囚犯教育、職業訓練和心理重建方麵,雷蒙隊長是個徹底的失敗者。他認為,監獄的功能就是懲罰犯人,我認為那是錯誤的。”
勞森抿了一下嘴。“你不喜歡雷蒙?”他脫口問道。
“不喜歡,”吉爾德說,“不過,也沒有什麼不喜歡的,我們隻是誌向不同,成不了朋友。”
“是的,”勞森點頭說,“我很感謝你的坦率。”他的手指又在桌麵上敲打起來,他似乎有敲打的習慣,“弗蘭克這個人怎麼樣?他是這兒的囚犯頭嗎?”
吉爾德聳聳肩,“雷蒙認為是,我並不這麼認為。”
“雷蒙不僅僅認為是,”勞森更正說,“他堅信他就是囚犯頭,為什麼?”
“我不知道,”年輕的副監獄長說,“我承認,弗蘭克可能參與過一兩次,他在這兒已經十來年了,為了使生活好過一點,任何老囚犯偶爾都會參與。不過,我根本不相信他控製著所有囚犯。”
“你認為,雷蒙是不是由於某些原因而和弗蘭克過不去?”
吉爾德摸摸下巴,“有可能,他們兩人在這兒都很長時間了,他們可能很久以前有過什麼過節。”
勞森想了一會兒,說:“以後再討論這個問題吧,明天我就找弗蘭克問話,問他有關改進監獄的看法。”
吉爾德皺起眉頭,“你要向弗蘭克征求改進監獄的意見?”
“對,向弗蘭克和每一個在這兒的老囚犯征求意見。我在別處當監獄長時,用過這個方法,他們會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批評意見。”
“我非常讚成,”吉爾德回答說,“這種做法很開明。”
“我希望會有些好結果。”勞森說,“這件事就由你來安排,明天上午9點開始,每一位囚犯十五分鐘左右,今晚6點之前,把他們每個人的資料放到我桌上,我晚上要先看看。”
“是,我會照辦的。”
“好極了,”勞森喝完咖啡,“我們回去吧。”
第二天上午9點,勞森監獄長開始和監獄中的老囚犯談話。他很專業地問問題,刺探那些人的心理和思想,那樣子,就像一位高明的外科醫生在病人的身上刺探腫瘤一樣。
勞森在和六位老囚犯談過話以後,才輪到老弗蘭克。
勞森看到弗蘭克時暗暗吃了一驚。這位曾經顯赫一時的收贓者,在坐了十多年牢後,外貌大變。他有點駝背,頭發全掉光了,眼睛水汪汪的,皮膚灰白,很不健康,根本不像一個能煽動囚犯暴動的人。
“弗蘭克,”勞森開口說,“我請獄中所有的老人來談話,是想征求一下意見,看看有什麼需要改進的。你有什麼建議嗎?”
弗蘭克坐在椅子邊,愁眉苦臉地抓著一頂便帽,聳聳肩,“我……我……關於監獄……我什麼都不知道。”
“弗蘭克,你不要害怕,”勞森說,“你說的話絕對沒有人知道,請你坦白地說,說出你的想法。”
他再次聳聳肩,“當然有,監獄長,我的意思是說,有很多方麵可以改善。食物方麵可以改善,星期天放的電影都太老了。”
“這都是一般的意見,”勞森對他說,“我要找的是比較特別的意見,尤其是會引起暴亂的問題。”他漫不經心地打開弗蘭克的資料,“比如說,警衛對某些囚犯好,對某些囚犯不好,你說這種情況會不會有?”
弗蘭克雙手扭著便帽,同時避開勞森的眼睛。“也許有,也許沒有。”他說,“我不知道。”
勞森手指輕輕地敲著桌麵,“弗蘭克,如果你覺得某個警衛虐待你的話,你會向我報告嗎?”
“當然會。”弗蘭克抬起頭,然後又垂下來,“為什麼不呢?我在這兒已經很長時間了,一直規規矩矩的。”
“這麼說,如果有警衛或者警官和你過不去,你願意來報告。”
“是的,先生,我會的。”弗蘭克很明確地說,“我在這兒一直很規矩,我也希望獲得公平的待遇。”
“我明白,”勞森點點頭,“你和雷蒙隊長相處得還好嗎?”
弗蘭克搖搖頭,“隊長不太喜歡我。”
“為什麼?你和他有什麼過節嗎?”
“是的,監獄長,有過一次。不過,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什麼事?什麼時候發生的?說出來讓我聽聽。”
弗蘭克拉拉一隻耳朵,“讓我想想。大約五年前,我在洗衣廠當核對員,我的工作是確定某天收某棟某號牢房的床單。那一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二,雷蒙隊長來對我說,洗衣廠的值班人員沒有去收B棟5號和6號的床單,我告訴他,那兩個牢房要下星期二才收來洗,隊長說,牢房外麵全是床單,我說那天不是他們洗床單的日子,他說我不負責任,就解除了我的工作。”
勞森點點頭,“然後呢?”
“我認為那不公平,所以我就去找副監獄長,他是吉爾德先生的前任,他調查了這件事情,發現我沒有錯,錯的是雷蒙隊長。”
“你怪不怪他?”勞森問。
“我不怪他。”
“你向副監獄長申訴之後,結果怎麼樣?”
“副監獄長恢複了我的工作。”
“你認為,這件事使得雷蒙隊長對你產生成見了嗎?”
“不,先生。那隻是一件小事,當天就解決了,除了我、雷蒙隊長和副監獄長之外,沒有人知道。”
勞森微笑著說:“你的意思是說,你沒有向其他囚犯吹牛,說你戰勝了警衛隊的隊長?”
“沒有,先生。”弗蘭克說,“我才不去惹麻煩呢。”
勞森坐著想了一會兒,盯著眼前這位瘦弱的犯人,他認為那件事並不是一件小事,雷蒙隊長可能因此對弗蘭克產生了成見。“弗蘭克,我想就這樣了,我感謝你的坦率,謝謝你。”
星期三快下班的時候,監獄長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是上次那些人。
“我不會耽誤大家很長時間,”勞森說,“我已經看過各棟牢房的報告,寫得很好,大部分意見都可以采納。”說著將報告擱在一邊,“鞋廠的那八個人怎麼樣?”
“他們都出來了,監獄長。”吉爾德報告說,忍不住掃了雷蒙一眼,“他們是自動出來的,工廠的機器完好無損。”
“這八個人現在在哪兒?”
“隔離房。”
“好,”勞森轉向雷蒙隊長,“我知道,C棟6號房的絕食已經解決了。”
“是的,監獄長,”雷蒙說,“你那個用熱菜的主意很好。今天早餐時,隻剩下三個人拒絕吃,我們已經把那三個人送到隔離房,所以現在C棟完全恢複正常了。”
“牢房氣氛怎麼樣?”勞森問。
“很平靜,”雷蒙自信地說,“暴亂的火花已經全部熄滅了。”
“你認為它不會再燃起嗎?”
“那除非發生大事。”
“哪一類大事?”
雷蒙聳聳肩,“警衛殺死囚犯這一類的事。”
“我想不會發生那種事的。”吉爾德幹巴巴地說。
“我可不敢那麼肯定。”雷蒙說,冷冷地看著吉爾德,“去年一年裏,在四個不同的監獄發生過四次。一個囚犯和監獄官在辦公室,那個囚犯突然撲向監獄官,監獄官用槍打死了他。這種事情隨時可能發生。”
“讓我們假定不會發生這種事,”監獄長插進來說,“不要談那種意外的事。”
“是,先生。”雷蒙平靜地說。
“很好,”勞森轉向三位警衛官,“如果今晚和明天一切順利,從明晚起,就不必早鎖牢門,可以恢複娛樂,包括體育館、電視。但是,所有警衛留在控製室裏,各牢房門沒有上鎖之前,警衛不要在通道上走,明白嗎?”
“是,監獄長。”三位警衛官說。
“好,”勞森的手指又在敲了,“至於隔離房的那些人,把他們留在那兒。”他看看手表,“今天就到這兒吧。雷蒙隊長,你多留一會兒,好嗎?”
吉爾德和三位警衛官站起來,離開了辦公室。雷蒙板著臉留了下來。
“雷蒙隊長,”勞森說,“關於你對弗蘭克的看法,我做了一些調查,坦白地說,我找不到任何證據……”
“你不可能找到,”雷蒙隊長說,“弗蘭克是個聰明的歹徒。”
“他可能是全監獄裏最聰明的歹徒,但是,他不可能一點痕跡都不留。”
“你是說我需要證據?證明為什麼要把弗蘭克那樣的壞蛋扔進洞裏?”
“對,這就是我的意思,隊長。”
雷蒙靠在椅背上,“我以為你是來加強安全防範的,可是你的談吐好像要姑息這些壞蛋。”
“我不打算姑息任何人,囚犯或警衛都不姑息。”他站起身,開始收拾手提箱,“隊長,如果你沒有充分的證據,請你對弗蘭克和其他囚犯一視同仁,你告訴你的部下,絕不能虐待犯人,明白了嗎?”
“明白了,監獄長。”雷蒙也站起來,看著勞森鎖上手提箱。
“雷蒙隊長,”勞森從辦公桌後麵繞出來,“你再過四年就可以合法退休了,你最好考慮去幹別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拍拍雷蒙的肩膀,“我不是無情,隊長,隻是有些人不能適應變化。你是一個看守人的人,而我和吉爾德是改造人的人。你在你的那個時代是很有價值的,可是,我想你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希望你不要把這件事當做我們倆的私人問題。”
“不會的。”雷蒙平靜地說,說著,隨著監獄長走出辦公室。他們走出行政大樓,走下台階,來到監獄長的私人停車處。勞森把手提箱往汽車裏一放,上了汽車。
“隊長,你還是放聰明一點兒,”他警告說,“別再和弗蘭克那種人過不去了,他們有什麼問題,由我和吉爾德來處理,你隻要把這四年混過去,然後領退休金就是了。”
勞森倒車,向工作人員專用的門開去。
雷蒙站在空空的停車場旁,目送他離去。一位警衛官走過來,站在他旁邊,這位警衛官是值夜班的。
“隊長?”警衛官的聲音有些不安。
“什麼事?”雷蒙問,眼睛沒有看他。
“你認為新監獄長的說法對嗎?你認為暴亂已經結束了嗎?”
“可能,”雷蒙回答說,“除非發生囚犯被殺這類的事件。”
警衛官點點頭,顯然鬆了一口氣,“那種事不太可能發生。”
“不,”雷蒙說,“那種事很可能發生。”他看看警衛官,“你巡視過了沒有?”
“正準備去。”
“今晚的秩序是怎樣的?”
警衛官從襯衫口袋掏出一張卡片,“今晚是先B棟,然後A棟,最後是C棟。”
雷蒙隊長看看手表,“你巡視完之後,我在餐廳等你,我們一起喝杯咖啡。”
“好的,隊長。”那個警衛說。
雷蒙轉身走上水泥台階,而警衛官開始朝院子走去。雷蒙慢慢地爬上台階,重新進入行政大樓。沿著走廊行走時,他看看右邊,又看看左邊,察看是不是還有辦公人員在。他發現都下班了。他沒有理會監獄長的辦公室,因為他知道裏麵沒有人。經過副監獄長的辦公室前,他停了一下,輕輕敲門,然後推開門探頭進去,發現吉爾德已經下班了。行政大樓隻剩下他一人。
雷蒙隊長繼續向前走,進入自己的辦公室。他在辦公桌前坐了十五分鐘,一直到他肯定值日的警衛官巡邏過B棟,然後他掛電話找B棟的警衛官。
“我是雷蒙隊長,”他說,“把弗蘭克帶到我辦公室。”
帶弗蘭克進來的是一個新來的人。他和弗蘭克見麵後,站在辦公桌前,雷蒙隊長掃了弗蘭克一眼,然後,伸手接過警衛手中的簽收條。
“不用等了。”雷蒙隊長簽好收條後告訴警衛,“等一會兒我自己帶他回去。”
“是,隊長。”年輕的警衛接過簽收條,敬了個禮。
“出去的時候,請順便把門關上。”
“是,隊長。”警衛離開辦公室,隨手關上門。
在靜悄悄的辦公室,雷蒙隊長和弗蘭克對看了一會兒,然後,雷蒙漫不經心地打開底層抽屜,拿出一瓶威士忌和一個酒杯,往杯中倒了點酒,往桌麵上一推。弗蘭克急切地抓起酒杯,一飲而盡,然後深深地歎了口氣,跌坐到椅子裏。
“我需要酒。”他說。
“我知道。”雷蒙隊長說,蓋好瓶蓋,放回抽屜。
弗蘭克探身向前,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緊張地說:“好了,我們談吧。”
“你可以放心了,”雷蒙隊長說,“我們的新監獄長是一個改革家,他忙於改造人,不會注意監獄的欺詐行為。”
“真的嗎?”弗蘭克問。
“當然是真的。”雷蒙隊長輕鬆地說。他站起身走到窗前,他可以看見點著燈的牢房、警衛的守望塔、院子和牆壁,他知道這是他的王國。他點著一支昂貴的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我們這兒有兩千名犯人,每天至少有一半人在某件事上會多花兩三毛錢,比如把褲子燙平,多給一張日用品供應條,圖書館為他保留某本書,一封額外投寄的信,星期日晚餐多給一份甜食……”
雷蒙隊長轉身對著弗蘭克,微笑著說:“一天兩三毛錢,聽上去很少,可是整個監獄那麼多人,那可是不少啊。”
弗蘭克聳聳肩,“我們平均一天可以搞到二百八十到三百元錢。”
“對了,你我每天分一百元,其他的付給那些需要打點的人。不過,首先我們倆要先拿到我們的那一份,對不對?”
“當然,”弗蘭克說,聳聳肩,“我們該拿那錢,這是我們想出來的計劃。”
“完全正確。”雷蒙說,“弗蘭克,你知不知道我們在瑞士銀行存有多少錢?超過五十萬了!告訴你,單是利息,每個月就有一千多。弗蘭克,再過四年你就刑滿釋放了,我申請退休,那時候,我們就可以享受了。”
“如果這位新監獄長不放聰明一些,是不是也要像過去一樣整他?”
“對,”雷蒙隊長的微笑消失了,“我們就像對付上一任那樣,幹掉他。我們再策劃一次暴動,那些和他合作的人,趁著暴亂一起幹掉,就像我們幹掉那兩個多嘴的人一樣。弗蘭克,這地方我們經營了十四年了,絕不能讓人來破壞我們的心血。”說著拿起弗蘭克的酒杯放進抽屜裏,“走,我帶你回牢房。”
兩個男人離開辦公室,他們走到院子裏,雷蒙隊長深吸了一口氣,抬頭看天空。
“美麗的夜晚。”他說。
“是啊,”弗蘭克說,也抬起頭,“繁星滿天,這樣滿天星星的夜晚真是太妙了。熄燈之後,還有東西可看。”
“真有意思。”雷蒙隊長說。
他們繼續向前走著,一直到隻剩兩個黑黑的影子,從那兩個影子分不清誰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