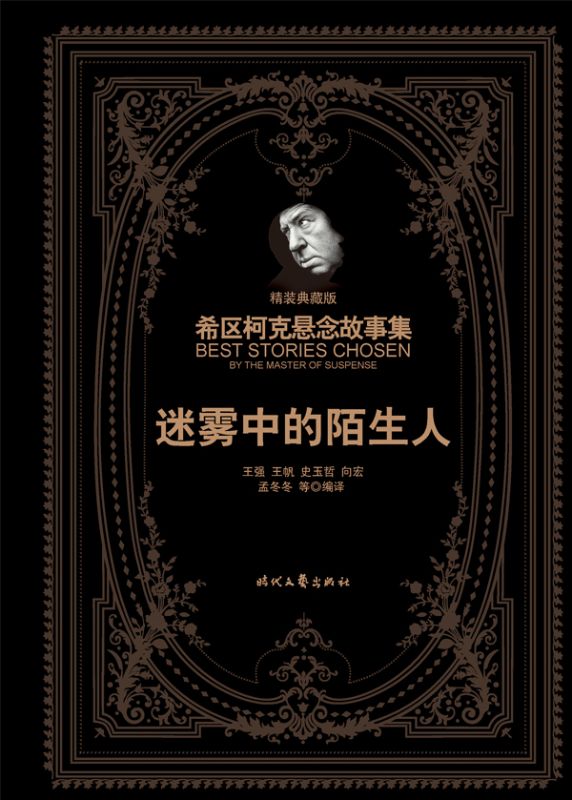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借刀殺人
我們來到路卡前時,已經快半夜了。大雨下個不停,在卡車車燈的照射之下,路麵像玻璃紙一樣發亮。
警察把路卡設在離急轉彎處大約五十碼的地方,所以人在遠處看不見,隻有轉過這個彎後才能看見它。兩輛警車成V形朝北停著,正對著我們,還有兩輛在二十碼外,成V形朝南停著。四輛警車都開著車燈,在潮濕、黑暗的夜空下,車燈的燈光像探照燈一樣互相交叉著。在四輛警車中央,放著兩個巨大的木製的臨時路障,上麵的紅燈一閃一閃的。
我輕輕地踩一腳刹車,我們的卡車慢了下來。那孩子從座位上探過身來,惡狠狠地用獵刀抵住我的肋骨,低聲說:“聽著!你要是敢亂說一句話,我就宰了你!他們會抓住我,但我會先捅死你!”
我扭頭瞥了他一眼,在路卡昏暗的燈光下,他臉色蒼白,腮幫和下巴上胡子拉碴的,顯然已有三四天沒刮了。實際上,他並不是一個孩子,但給人的印象卻像個孩子。他長得高大,瘦削,一綹黑發垂在額前,上身穿著一件皮夾克,下麵是一條沾滿泥巴的粗布斜紋褲子,腳下蹬著一雙高筒靴,看上去像是從貨車上跳下來的。
十五分鐘前,在距BC鎮四英裏的地方,他劫持了我。大雨已經持續了三天,路麵非常糟糕,有一段三百碼的路段,積水達兩三英尺深,我不得不放慢車速,緩緩通過。就在這時,卡車乘客座位那邊的門被猛地拉開,這孩子跳上車,右手握著獵刀,喝令我不許聲張,繼續開車。
我別無選擇,隻能繼續以四十公裏的時速慢慢穿越那段積水區,我在心裏揣摩,這孩子為什麼要劫持我和卡車呢?他犯了什麼罪?他是從哪裏逃出來的?他的神情很古怪,我可不想惹他用獵刀捅我。
現在,我把卡車停在離警車十碼的地方,右邊有一小片空地,可以在檢查完後倒車,但是,一位穿黑雨衣的警察正站在那兒,雙手插在衣兜裏,我認為他手裏正端著槍,不禁緊張得呼吸都困難了。
一輛警車的前門開了,兩個穿著同樣雨衣的警察下了車,朝卡車走來。一個走到車燈光線之外,站在黑暗中監視著我們,另一個圓臉的走到我的車窗前,手裏拿著一個小手電筒。
我搖下車窗玻璃,他打開手電照著車廂,我在燈光下眯起眼睛,裝著迷惑不解的樣子。
“警官,出什麼事了?”我的聲音很不自然。
“你們去哪兒?”他很嚴肅地問。
“去桑諾。”我說。
“這麼晚了,到那兒幹嗎?”
“我去接我太太,她的火車半夜才到。她媽媽上星期病了,她去照顧她媽媽了。”
他點點頭:“你叫什麼名字?”
“麥克。”
“帶駕駛執照了嗎?”
“當然帶了。”我說。我從屁股口袋裏掏出皮夾打開,高高舉起。他用手電照了一下,點點頭,然後把手電光照在那孩子身上,那孩子緊張地抿著嘴,把刀藏在右腿和車門之間相對隱蔽的地方。
警察問:“這是誰?”
“我侄子傑裏。”我立即回答。
“他也住在格蘭吉路嗎?”
“和我們住在一起。”
“格蘭吉在BC鎮的郊區,是嗎?”
“是的。”
“你們今晚出發後,有沒有碰到什麼人?”
“你指的是什麼呢?”
“有沒有看見有人在路上遊蕩或是要搭便車的?”
我吸了口氣。“沒看見。”我對他說。這時,我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念頭,但一想到它,我就渾身冒汗。盡管如此,我還是準備試試,我時刻記著那孩子手中的刀。
我的左手本來是放在肚子上的,現在,它卻慢慢地向車門把手移去,每次一寸。我努力裝出很平靜的樣子,問:“警官,為什麼要設路卡?發生什麼事了?”
“大約三小時前,有人在BC鎮搶劫,”警察回答說,“搶劫了一位從芝加哥來的鑽石推銷員,搶走了價值兩萬元以上的未切割的鑽石。那個搶劫犯一定知道推銷員的行程,或者可能從芝加哥開始就一直跟蹤他。”
“你知道那個搶劫犯是誰嗎?”
“還不知道,”警察說,“但我們知道是一個男人,單獨一個人,開著一輛偷來的車,那車停在推銷員住的旅館後麵。他用一根灌鉛的棍子擊倒推銷員,但活兒幹得不利落,推銷員蘇醒過來開始大叫,叫聲引來了旅館的經理和幾位旅客,歹徒從後門逃走了,但沒人看清他的長相,連推銷員本人都沒看清。”
現在,我的小指已摸到門把手了,我得讓警察繼續說話。“嗯,如果這位強盜開的是偷來的汽車,那你們為什麼要攔住我們這種普通的車輛呢?”
“他不開那輛車了,”警察說,“他逃離旅館二十分鐘後,我們發現汽車被扔在一片樹叢中。那裏沒有房屋,什麼也沒有,所以我們知道他至少要徒步走一會兒。但他也可能再偷一輛車,或者假裝搭車而劫車。”
“天哪!”我輕輕地呼了一口氣,但是我可以感覺到我的肌肉馬上抽緊了,我的整個左手都落在那個門把上,手指緊緊地扣住了它。我隻要向下按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那孩子的刀有多快,我注意到,在我和警察談話時,他一直緊盯著我。
“叔叔,我們該走了。”那孩子突然開口道,他的聲音充滿了緊張不安,“我是說,如果警察先生放行的話,我們得去接嬸嬸——”
他沒有說完,因為他說話時,視線從我身上移到警察那裏,看警察對他說話的反應,我需要的正是這一空當。我按下門把手,使盡全身力量衝出去。門猛地向外打開,將警察撞倒在雨地上。我左肩著地,順勢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嘴裏大聲喊道:“就是他!他就是你們要找的人!他拿刀劫了我的車!就是他!”
我滾離路麵,翻滾過路基,停了下來,轉回頭看那卡車。那小孩正從車門出來,手裏握著獵刀,那個圓臉警察側身躺在路上,伸手從雨衣裏往外掏槍,同時另一隻手打開手電筒。接著,又有兩個手電筒亮了起來,警車的門也猛地打開,人們在大雨中奔跑,大叫。
那孩子終於跳了出來,站在卡車旁邊,惡狠狠地朝四處張望,手裏揮舞著獵刀。圓臉警察開了兩槍,另一個警察開了第三槍,那孩子倒下去,不動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站起身,警察們圍在那孩子身邊,低頭看著他,我也走過去,站到那個圓臉警察身旁。我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在幾裏外的積水區慢慢開車時,他衝上我的汽車,拿刀對著我,不許我聲張,而且他的眼神非常古怪。”
圓臉警察嚴肅地點點頭,“麥克先生,你剛才很勇敢,”他一手搭在我肩膀上,“他很容易傷害到你。”
“從他的眼神看得出來,他過一會兒就會動手的,”我說,“我覺得,最好還是在這裏冒險拚一下。”
一位警察跪在那孩子身邊搜索。“什麼也沒有,連皮夾也沒有,口袋裏幹幹淨淨的,更不用說鑽石了。”
圓臉警察說:“吉爾,到卡車上瞧瞧。”然後他問我:“他跳上車時,有沒有帶什麼東西?”
“沒有。”
那個叫吉爾的警察用手電筒照照卡車,然後搖著頭回來了。圓臉警察問我:“你記得他劫持你的確切地點嗎?”
“當然記得。”我說。接著我告訴了他那個位置。
“那麼,他一定是把鑽石藏到那裏的某個地方了,雨小點後,我們派人去搜索一下。”
他們從一輛警車上拿來一條毛毯,蓋住那孩子,然後用無線對講機通知BC鎮的警察局,說他們已經抓到搶劫鑽石的人了,要他們派輛救護車來。
圓臉警察和我上了他的巡邏車,他錄了一份我的口供,我簽了字後,說:“我現在可以去桑諾了嗎?我太太一定已經等急了。另外,我還需要一杯酒,鎮定一下。”
“當然可以。”他說,“我們需要你的話,會跟你聯係的。”
我向他道別,上了卡車,慢慢繞過路卡,然後駛入大雨滂沱的黑夜中。過了五裏路後,我的呼吸才漸漸正常,情緒也不那麼緊張了。
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就這麼逃脫了。
首先,我打那個推銷員打得不夠狠,他醒來後尖叫。其次,那輛該死的轎車出了問題,我不得不扔掉它。最後,我來到一家農舍,綁住那位真正的麥克,塞住他的嘴,偷走他的皮夾和卡車,接著,半路殺出了那個傻小子。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但現在這已經無關緊要了。我確信不疑的是,他遲早會向我動刀子的,所以我才要,在路卡邊冒險。正如我向那個圓臉警察所說的那樣,最好在那裏冒險拚一下。
價值兩萬元的鑽石就係在我的腰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