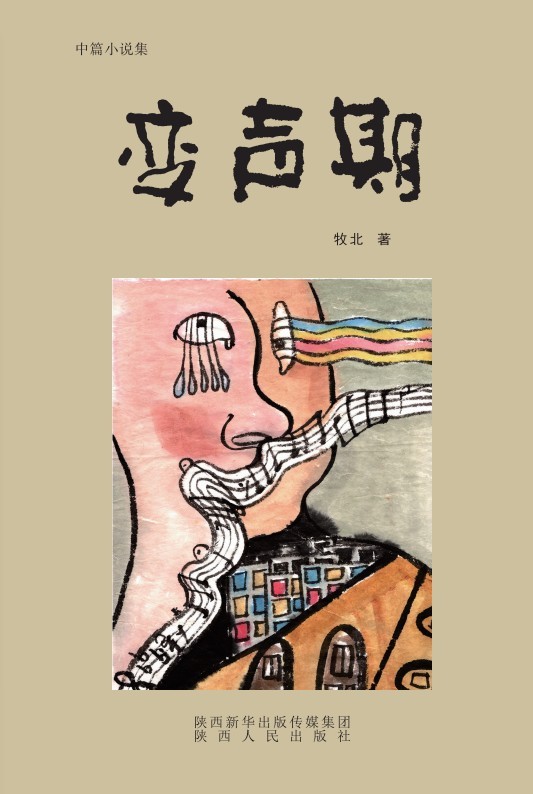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尾 聲
一年後,張家圪嶗的棉花超倍完成了縣政府下達的種植和收獲任務,張能能成了邊區有名的 “棉花大王”,姚廣德曾經誇下海口,這陝北,除了他姚廣德,沒有人能種出棉花!當然,姚廣德誇下的海口比較多,這算是很小的一個。他的話,後來就沒有人願意再聽了。
姚廣德自己偷偷去膚施城找過幾次巧巧,巧巧在膚施城的陶瓷廠當工人,巧巧不願意見姚廣德,姚廣德左等右等,半個月才遠遠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兒。從此回到張家圪嶗就病倒了,張能能種的棉花地,也算姚廣德的份,姚廣德問張能能,你婆姨在城裏,尋了別的男人,你就不曉得去找一找?你去,把她找回來,我就算把她打死,也要讓你們成婚哩!張能能說,強扭的瓜不甜,政府有規定,虐待婦女也犯法。姚廣德說,你別動不動跟我提這個法、那個法,啥年月都有王法。張能能說,我說的就是王法。姚廣德張大嘴巴不敢再說。過了年,姚廣德的病好點了,張能能看他能動彈,就想跟他敞開談一談。姚廣德躲閃著不見他,張能能半夜裏跪在姚廣德的窯洞外說,大,去年的莊稼我都給你種成了,也收成了。
姚廣德說,好。
張能能說,大,我給你磕個頭,咱這事就算完了。 姚廣德說,你要走就走,別一副假惺惺樣子讓我可憐。張能能說,我是個攢年漢,攢了多少,你心裏明著哩,我都不要了。
姚廣德說,你還曉得自己是攢年漢? 張能能說,一輩子都忘不了,這事我不爭了,你要麵子哩。姚廣德說,我要是不要麵子咋弄?
張能能說,邊區到處都是說理說法的地方,你難堪,我也不好受,新社會,誰也不敢提攢年漢,要不然,你還得受一次罪,最後雞飛蛋打一場空。
姚廣德說,那你跟我說這是啥意思?
張能能說,以後,出山受苦,都是你的事。我要走了,契約你拿著,我這就給你磕三個頭,咱倆還是父子,若是你不認,咱倆以後各走各路。
姚廣德說,這有啥區別麼?
張能能說,我以後不知是死是活哩,巧巧跟別的男人好去了,我也曉得哩,你要是不服,契約你拿著隨時告我。
姚廣德說,我自然要告,我去閻王爺那兒也要告哩。 張能能說,那我就磕頭了!
姚廣德罵,去給你先人磕去,去給驢磕去,我還沒死呢,你磕個啥頭!滾!
張能能也不管姚廣德願意不願意,跪在窯洞門口,對著窯洞磕了三個響頭,而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張能能走的時候,剛好是桃花杏花開放的時節,山坡上滿地的粉紅,荒山的心情是粉紅的,小河的心情是粉紅的,藍天的心情也是粉紅的。馬幹部將他送到二郎廟下的岔路口,馬幹部說,能能,你這麼走了,你大曉得嗎?張能能說,曉得,他是他,我是我!馬幹部又說,姚廣德就你一個兒子,按邊區法規,你不去應征入伍也可以。張能能說,想了一年,時間夠長了,我不是牲口,我要跟崔幹部一樣去當兵哩,像他一樣活成一個男人!馬幹部笑著點點頭,看著張能能盯著二郎廟出神,就問他,能能,你看啥呢?張能能說,姐,那廟看起來也沒那麼嚇人。馬幹部說,廟有啥嚇人的?你是從小被嚇壞了。張能能說,姐,你看,這廟咋也變成紅色了?馬幹部順著張能能的目光看去,二郎廟的周圍倒是桃花一片,看起來粉紅粉紅的……張能能又說,跟 “是岸寺”一樣的顏色,都是彤紅彤紅的……一邊說一邊已經走入了粉色的山巒之中。
山巒是彤紅的,空氣和天空也是彤紅的,彤紅的春天裏,一支張能能唱的彤紅的信天遊回蕩著:
大江大河水長流,有誌氣咱要看前途,沒出路。
樹木成長有用材,莫說男兒離不開,放心懷! 摘個水果嘗新鮮,攢年漢要當兵去,人稱讚!
穀鄉六年如局尋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