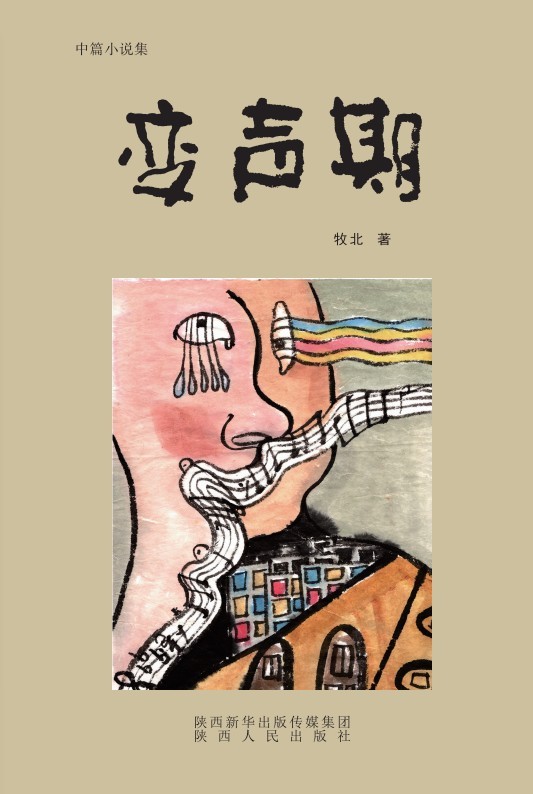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下 部
從川道口繞過山梁,腳下的水汪起來,川道更寬闊了,人來人往,牲口車輛,還有那些灰布軍裝的人也多起來,南腔北調的塵土飛揚著,似乎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春天的訊息,他們的表情是活泛的,生機勃勃的,萌動的,而不像姚廣德這樣呆板木訥的,老氣橫秋的;每個人都有生活的奔頭和想法,而不像三天前的張能能麵如死灰,死氣沉沉;每個女人的臉都揚起來,迎接著陽光的照耀,隨時會哭起來或者笑起來,隨時都會抽芽展葉,隨時都會開花綻放……
這是張能能第一次來膚施城,從東關紛雜錯落的騾馬店、小館 子穿過去,下了一道坡,再越過一條河,就到了大東門,城牆低矮,大多被炸得七零八落,但是路和街道都收拾得幹幹淨淨,沿著青石板路麵,兩旁的內容就多起來了,從大東門一直走到二道街,商鋪林立,從南到北,一家挨著一家,吆喝聲、騾馬叫聲、大人娃娃的吵鬧聲,比張家圪嶗趕廟會的情景要熱鬧幾十倍。
姚廣德指了指前麵的大山說,那是鳳凰山,山前是鐘鼓樓和衙門府,衙門府前是頭道街,是條公道,也是官道,以前的衙門、郵局、學校都在頭道街,這是二道街,是私道,也是民道,老百姓做買賣的地方。姚廣德胸有成竹地說著走著,到了一條巷口,頭道街和二道街之間的巷口人來人往,擁擠起來。顯然姚廣德的話不足信,現在二道街和頭道街,那是處處相通,沒什麼官道民道之說。那些穿著灰布軍裝的人,操著各種不太清楚的口音,與街道邊上的夥計們討價還價,言笑晏晏,他站在那兒有點尷尬地咳嗽了一聲。
姚廣德拉著巧巧,轉到馬記布莊門口。張能能愣神看著那些忙碌的人,不禁有些拘謹,轉過頭,姚廣德已經不見了,隻好挨著一家一家地找,總算看到馬記布莊的掌櫃正在給巧巧量衣服。姚廣德對老板說,結婚的衣服,你看著給裁剪。老板一喜,慌忙記了下來,巧巧突然攔住姚廣德的話說,我不要這個,我要那個!巧巧指著旁邊試衣的一個女人的旗袍。巧巧的話,姚廣德好像沒聽到一樣,繼續對老板說,別聽她的,你裁你的。老板覺得詫異,但是,手下的活沒有停。巧巧瞪著姚廣德說,我說,不要那些大綠色,要這個!巧巧指著那些素色的花布,姚廣德哄她說,結婚哪有穿這個的?巧巧說,誰說我要結婚了?姚廣德被哽在那兒,不知所措地看了一眼張能能,張能能蹲在布店的門口不說話,隻能看到木桶,看不到他的人。巧巧的話,顯然他都聽到了。
姚廣德原想,有些話還是張能能先說出來,他也好有個台階,有個麵子。沒有想到巧巧先說出了不願意結婚的話,這讓他半天沒有想出應對的話來,就衝巧巧吼著,你不結婚?我咋辦?二能子咋辦?就算是新社會,也不能由你咋樣就咋樣!巧巧也來了勁說,新社會就是自己做主,我不想結婚就是不結婚!二能子,你想結嗎?巧巧把話扔給張能能,這話是姚廣德故意引過去的,巧巧上當了。張能能看了看姚廣德,又看了一眼巧巧說,結不結,看你!巧巧說,我不結!你要結,你跟他去結!巧巧說著,摔下手裏左右揣摩的布匹。姚廣德說,既然都不想結,那我來這一趟為啥麼?二能子,巧巧小,不懂事,你也跟著起哄?
張能能看了一眼姚廣德偽善的樣子,不由得有些發嘔。但是,這一趟不能白來,從張家圪嶗到膚施城,那得費多少腳力?來了也不能白逛,得有點收獲,姚廣德拉住巧巧說,要不先吃點。巧巧走了一路,早就餓了,喊了幾次,姚廣德一直說堅持,堅持不下去了,自然就冒火。在路邊的攤位上,姚廣德要了三碗^,肉湯的給巧巧,他和張能能是素湯,主要是穩住巧巧,也安慰張能能。巧巧倒是穩住了,張能能警惕起來,從張家圪嶗到膚施城,姚廣德的臉倒是一天三變。有一天,姚廣德聽說馬幹部選了張能能去學習種棉花,姚廣德的內心是複雜的,他開始打罵張能能和驢,他把這種壓抑的心情發泄在牲口身上,也發泄在張能能的身上。張能能明顯感覺到,他突然在姚廣德麵前成了一種威脅,這種威脅讓張能能找到了存在感。張能能眼看著要翻身了,姚廣德從複雜的淩駕,變成了平視,從這兩碗素^張能能感覺到,他在這個家裏的位置,從門外被請進了門內,從牲口變成了人。他第一次和姚廣德、姚巧巧坐在桌子上吃飯,讓他莫名生出了一頭的汗水,張能能連連喊,辣!
張能能很清楚姚廣德的想法,如今擺在他們三個人麵前的路,到處是岔口,稍不留心,都會走成差錯。因為選擇的路多了,每個人的心裏都在彷徨和踟躕。尤其是姚廣德,當前和以後,他要處理好與張能能的關係,從馬幹部對待張能能的態度來看,他隱隱感到,張能能已經和張家圪嶗那幫窮人一夥了,而巧巧此時不想結婚,那絕不是一句玩笑話,他了解自己這個女兒,她的心野了,她離開的一整天時間,那個崔幹部跟他說了什麼?男人就不該跟女人瞎亂騷情,第一次見了崔幹部,巧巧就要把剛剛纏了一半的腳放開了。因為這事,他差點成被批鬥的對象。他現在必須麵對一個事實,巧巧和張能能這兩個人,很難捏到一塊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先用時間拖著,然後像今天一樣,安撫地坐在一起,不管用什麼辦法。他現在唯一不能拿捏準確的是張能能,他是怎麼想的?他會不會像老張家人一樣,跟他清算?會不會反目成仇?會不會把他打倒在地?這種事,他必須有個心理準備,而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他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去拉攏。
吃完了^,張能能看到姚廣德要給自己買皮帶和帽子,他已經選好了,就在剛才追巧巧路過的時候。姚廣德說,這膚施城大是大,但是也要曉得自己要往哪兒走,回哪兒去。張能能沒說話,巧巧倒是先搶了話說,我不回去了,你們倆先回去。姚廣德說,你不回去,這兒能容得下你?巧巧說,大家都能容得下,憑什麼容不下我?二十裏鋪我那姑家姐姐,她就在膚施城做事哩!姚廣德說,那哪兒是做事,那是給人跑腿,發個報紙,咱家的驢也是跑腿的!巧巧說那不一樣。姚廣德緊接著就問,哪兒不一樣?巧巧急紅了臉,一時答不上來。姚廣德得意地白了她一眼說,吃了喝了,東西買了,咱就回!巧巧說,就不回!你虐待婦女,我哪兒都能告你!這話就像炸彈一樣,把姚廣德給炸蒙了。張能能也沒有想到,巧巧能說出這種話來,這種話按照姚廣德的推算,應該是張能能先來提。姚廣德心裏很清楚,不管這兩個人,誰去告狀,他都得折了女兒又丟人!這世事,他能看得清,隻不過,他還想挽留住自己的那點體麵。
張能能看到姚廣德氣得屁都竄到臉上了,不由得湊了一句說,要不待一天,明天回去。張能能這句話在姚廣德看來,既解了圍,又讓他難受。巧巧顯然同意了張能能的話。姚廣德狠了狠心說,住一天也可以,但是明天必須都回去!巧巧說,到明天再說吧!姚廣德看了一眼張能能說,先把皮帶和帽子買了!走到皮革店,姚廣德給張能能挑了一條皮帶,從包頭進來的好皮子,姚廣德識貨,試了一下,也合適,問了價錢,也不貴。張能能說不要,姚廣德綻出笑臉說,再看看。離開皮革店,姚廣德說,不是啥好皮子,老牛皮了,硬得很。又說,我年輕的時候販賣過這東西,你放心,給你挑好的!你倆結婚的時候,不能寒酸!張能能故意看巧巧的臉,巧巧的眼睛隻顧直溜溜地看街邊路過的女八路。
女八路個個高挑身材,短蓋蓋頭發,走起路來,比扭秧歌還好看,巧巧這麼說,引得張能能和姚廣德也多看了幾眼。又說,你看她們,該笑的時候,笑得好看,不像咱張家圪嶗的女人,就一個臉色。姚廣德說,人是生就了,你下輩子投胎做女八路。巧巧不服氣,但是,沒有強嘴。姚廣德打聽了一下,說新市場的東西又多又便宜,就說去新市場。
出了南關,從南門坡沿著路過去,到了新市場,新市場在一條淺溝裏,人來人往,進進出出,吆騾子趕馬,比那二道街還要熱鬧。巧巧像進了天堂一樣,一頭跑進新市場,左看右看,那貨物多得數不清。還沒等兩個人攆上她,巧巧已經在絲綢店裏挑選了半天,非得要買一條圍巾,姚廣德跟她磨了半天嘴,才不得不掏了錢,巧巧的氣也撒了一半。
巧巧又說要去找她送報紙的姐,姚廣德隻說下次。巧巧說, 那給我買衣服!還是光華商店那些旗袍,姚廣德看了一眼張能能說,買還是不買?這話問得蹊蹺,張能能摸了摸自己的頭,覺得姚廣德這個老狐狸確實精明得很!他要說買,這等於是他的主意,以後得算他頭上;要是說不買,巧巧的槍口立刻對準他,再者,姚廣德是在揣摩他是不是真的尾巴翹上天了,他得把尾巴夾住,以免姚廣德對他防範過甚!張能能說,錢是你的,你自己看!姚廣德笑了笑說,咱也沒多少錢,就帶這點,讓她這麼花,咱非得虧空了!姚廣德嘴上這麼說,但還是從褡褳裏摸了錢,然後交給老板,拿了旗袍,巧巧一下子安靜了,乖巧了。
眼看著日落西山了,要回縣政府落腳有點遠,二十裏鋪也不夠現實。姚廣德說,那就找個旅店,歇個腳,明天回去。
旅店在新市場的中部,連著七八孔窯洞,不遠處能聽到民眾劇團的戲班子在唱戲,什麼戲,姚廣德也聽不清。付了店錢,姚廣德跑到新市場的街口,買了六個幹餅,晚上湊合一下,剩下的還要當明天一早的飯。三個人付了一個窯洞的店錢,姚廣德乏累得很,走了不少路,張能能在門口磨蹭著,猶豫了很長時間,而後聽到巧巧叫他趕緊去打洗腳水,張能能跟店主人要了熱水,打了半桶熱水進來,巧巧已經把旗袍穿在身上了,姚廣德嘿嘿嘿地笑著問張能能,好看不?張能能今天很多話,過去是不會講,今天卻意外講出來。張能能說好看!姚廣德伸出腳來,叫了一聲,張能能下意識地跑過去給他別褲腿,姚廣德說,你別動手,你現在是半個幹部了,哪有給我洗腳的道理,我自己來。又對巧巧說,以後你也不準對二能子吆五喝六,聽到沒?哪有女人對男人苛責的?!巧巧正穿得高興,用那種八路軍的步子在腳地上走來走去,走得跟鴨子一樣,隨口應了一聲。張能能看著姚廣德說完,又盯著他的表情,張能能心裏一慌順口就說,這是家裏的事情!
這話引起了姚廣德的注意,姚廣德吸了口旱煙,悠悠地噴出去,看著張能能說,今天就在炕上睡!張能能沒有應,這話不能再明了。張能能拿不住他下一句是什麼。吸了幾口旱煙,姚廣德終於又說,二能子,你剛才說,這是家裏的事,那外頭的事是啥?你不說,我心裏沒數。張能能知道姚廣德心裏打鼓了,這一天,他就等這時候套張能能的心思。張能能也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思慮了一會兒,看著姚廣德的腳在木桶裏不自覺地滑動著。過去的日子,就像這洗腳水一樣,始終在這洗腳桶裏,總顯得油膩又肮臟,卻又沒法一下子傾倒。張能能想著這洗腳水,姚廣德又提醒他,問你個話,也難了麼?張能能說,外麵的事,我也不懂。姚廣德說,你不是不懂,隻是不想說,等你想說的時候,怕是已經做出來了。姚廣德這是要逼他說些什麼。張能能就說,我就是個受苦人,外麵的事情,你比我懂。姚廣德雖然笑起來了,但是顯然對張能能的話不夠信任。姚廣德說,你也別跟我打哈哈了,你心裏想啥,我也曉得,你還是年輕,等你到了我這年齡,就曉得世事,也是輪流轉嘛。這話,張能能沒聽太明白,但是感覺姚廣德高深莫測,感覺這句話裏,明顯的警告意味,他還記著姚廣德說要秋後算賬的話。
張能能並不是害怕姚廣德,從得知巧巧的想法後,張能能莫名的有了一種十足的底氣,如果說馬幹部給他打開了一道大門,那麼巧巧的想法,就是突然之間把他心裏的那道窗戶紙給撕開了。所有的事情都敞亮了,敞亮了,他也該邁步走了,隻是這第一步,不是靠和姚廣德爭論這個閑氣。他很規矩地倒了洗腳水,然後在院子裏把洗腳的木桶洗了三遍,他怕洗腳水的氣味沾染了他的軍用被子。
他沒進窯洞,而是蹲在旅店的牲口圈旁邊。牲口圈在旅店的最裏麵,住店的人少,這家旅店地勢比較高,價錢比青年旅社便宜,住的人卻很少。旅店牆頭不高,可以看到溝底的新市場依然燈火點點。他從出了張家圪嶗以後,夜裏總是睡不著,他腦子裏的想法多起來了,很多事情還想不明白。白天看到的聽到的人和事,一時讓他很難一下子想明白、消化了。比如今天姚廣德突然的變化,從買皮帶到吃^,再到晚上的談話,姚廣德的客氣和示好,讓他曾經產生的決裂念頭,一下子有些動搖了。姚廣德當然不是簡單的小地主,他是一個飽經生活磨難的老狐狸。他對姚廣德的想法,總是開始堅定,最後變得動搖———這個世界永遠不會是非黑即白或者非愛即恨的二元體,隻有承認了這點,才能承認作為人本身的複雜性。
張能能一時想不明白世界,更想不明白他自己。
月亮爬上來的時候,他突然有了那麼一點涼意,過去在牲口圈裏睡覺的時候,也沒有覺得這樣的涼意,他卻舍不得用馬幹部送給他的被子。他摸著被子、水壺和那個印著紅五星的瓷碗,心裏莫名的暖和。一抬頭的時候,他才明白那涼意是從姚廣德的目光中散發出來的妒意和冷眼。
張能能一個激靈坐起來,姚廣德十分和善地看著他,然後湊過來笑了笑說,二能子,不是讓你回去睡嗎?張能能一時沒有明白姚廣德的意思,好像突然大半夜遇到了鬼一樣瞪著姚廣德。姚廣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說,二能子長成男人了,哎呀,大是粗心大意,沒有想到你長這麼快。這句話是感歎,也是一種示弱。張能能沒法回應他,姚廣德又說,二能子,眼下的情形你也清楚,大這輩子最後一樁心事,就是你和巧巧了。張能能點點頭算是認同。姚廣德說,你曉得不?你來咱家啊,那個可憐,你親大親媽不要你了,我這個人心善,才勉強把你留在咱家,簽了攢年漢的契約,我是把你當親兒子哩。張能能聽出姚廣德的意思,這是攻心,攻心的目的,張能能還無法預料,隻好耐心地聽著。姚廣德說,你從小也調皮麼,我不能不管你,咱這麼大的家業,以後要你頂梁立柱哩,你說是不是?張能能應承著 “嗯”了一聲。姚廣德沉默了,又拍了拍張能能的肩膀,很感慨地問,二能子,過去我沒把你當人啊,這是實話,那是曆練你哩,這是大的一片苦心呐,你恨大不?這話轉得有點快,張能能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姚廣德也沒看清他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笑了笑說,男人嘛,啥難活事,邁過去,就是頂天立地的人了!你也一樣。張能能點頭。
姚廣德又感慨地歎了口氣,半天又問張能能,二能子,巧巧可是你婆姨哩,你總不能不要吧?張能能低下了頭,他不想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姚廣德顯然為此很生氣,突然喘著粗氣揪住張能能說,二能子,你當了快二十年的攢年漢,為了啥?不就是為了巧巧嗎?你要是個男人,你就回窯裏去!我現在是你大,那窯裏的是你婆姨!你還在這驢圈裏幹啥麼!
張能能聽到姚廣德說得熱血沸騰,不由得也跟著有些激動了,使勁地點著頭。姚廣德看到張能能終於點頭了,再次火上澆油地說,你婆姨就在眼前,過了今天,她就敢跑了!你信大的話不?張能能說,信!姚廣德就說,你要是信,大給你說女人是咋回事,你倆今晚就算成親了!你進窯裏去睡!你要是不去,大我這輩子也不認你,你這輩子也別想回張家圪嶗!去啊!
姚廣德說著,狠狠地提起張能能,然後又推了一把,踢了一腳。張能能站在院子裏,猶豫不決地看著姚廣德,姚廣德氣得不得了,想要去再踢他一腳,又覺得不合適,回頭在驢圈裏將那個印著紅五星的瓷碗捧在手裏,威脅張能能。張能能嚇壞了,跑過來要奪。姚廣德突然一個飛腳踢過來,張能能一個踉蹌,姚廣德恐嚇他說,二能子,你要是今天不進去睡,你這碗我立刻打碎了,你的被子,我一把火燒了!你的水壺,我兩腳就踩爛了!姚廣德的話一點都不帶含糊,張能能急紅了眼,隻好依著他,一步三回頭地向巧巧的窯裏走去。最後姚廣德還不忘壓低聲音補他一句,你的皮帶和禮帽,大明天就給你買!放心!
張能能輕輕地推開門,窯裏的腳地上,月光灑下一片心跳。緊接著,他聽到門口姚廣德將窯洞的門從外麵反插了,這動靜似乎在告訴張能能,就算天塌下來,也不會有人管他和巧巧的事情!
張能能沿著那些心跳的月光,一步步走到炕欄前。巧巧在熟睡,呼吸在這夜裏都能聽得到。巧巧穿著那套新買的旗袍,整個胳膊和半個身子都露在外麵。張能能看了一眼窗外,姚廣德的影子在窗戶上消失了。張能能下意識地坐在炕欄上,覺得自己坐的位置不對,又坐在炕上,還是覺得不對,索性站在腳地上,悄悄地走來走去,又覺得這麼走來走去,巧巧要是醒來,會被嚇壞了。他就貓在炕欄下麵,這樣就能聽到巧巧的呼吸和她的甜蜜的夢想。他在想,巧巧的夢想應該與他沒有任何關係了,他想起第一次來到姚家的時候,折老二把他送到姚家,他已經記事了,他大不要他了,要把他給了姚家。姚家那時候財大氣粗,他大說,你去了就是享福哩,這輩子坐享其成了,姚家有的是錢有的是糧,怎麼都能活下去。張能能開始不懂他大的話,臨到跟前了,突然看到他大要走,哭天喊地要回去。他大頭也沒有回,藏在姚家的牆後麵,聽著他哭喊,自己不敢放聲哭,抓了一把黃土塞了自己的眼淚……從此再也沒見過折老二。到了姚家院子哭夠了,姚家的一個長工勸他,給他半個饃,才把他哄停住哭。第二天他才見了巧巧,姚老婆抱著巧巧,才兩歲多點,嘴巴子巧得很,那些長工就開玩笑說,能能,那是你婆姨麼!張能能還不懂啥是婆姨,站在院子裏傻待著。姚老婆和姚廣德看了他一眼,聽到巧巧說,馬馬……姚廣德吸著旱煙,聲音洪亮,不容別人插口氣的樣子指著他說,你過來!趴下來!張能能不願意,姚廣德指使旁邊的兩個長工說,摁住了,娶個媳婦還不高興?姚廣德說完,兩個長工就把張能能摁在地上,張能能不明就裏,哭嚎起來。姚廣德把巧巧架在張能能的脖子上,張能能這才明白了什麼,止住了哭。趴在冰冷的地上像驢一樣轉著圈,轉了兩圈,巧巧尿了張能能一脖子,脖子裏的尿把張能能的棉襖都濡濕了,張能能這次不敢哭了,巧巧反而哭了。姚廣德就罵道,跟死人一樣,尿了也不哼一聲,給娃換褲子去!最後這句是對姚老婆說的。
後來,巧巧長大點了,少不更事的兩個小孩是純真的,經常會在一起玩耍,巧巧雖然霸道一點,至少她沒有惡意,有時候還會同情可憐張能能。張能能內心很清楚,在這個家裏,他甚至不如那些長工,吃飯穿衣,處處不占理,在姚家人的嗬斥聲中,逐漸變得懦弱和沉默寡言。巧巧過了七八歲的時候,這種 “等級”更加明顯,巧巧雖然是張能能名義上的婆姨,但是他要經曆身體和心理上的 “磨礪”,在 “磨礪”中,他成了姚廣德眼中的 “牲口”,從剛剛萌動青春期,摸過巧巧後,張能能就徹底被姚廣德踩在了腳底,這種壓抑讓張能能徹底對巧巧失去了心理上的占有興趣,逐步轉化為一種莫名的仇恨。
月亮漸漸遠了,那些如月光一樣的心跳,慢慢平複下來,他試圖摸了摸巧巧的胳膊,沿著胳膊向上摸去,他的動作輕柔,他害怕弄醒了巧巧,他能看到巧巧起伏的胸部和大腿的延伸———他還是沒有覺得眼前的女人就是他的婆姨,他一閃而過的是這個女人與自己的未來,他一念之間想到巧巧驚懼而憤怒的目光,以及未來生活的晦暗和煩惱。他的手猛地縮了回來,好像被蠍子蜇疼了一般,她的皮膚瞬間粗糙而冰涼,就像她的聲音一樣,脆生生地毫不留情。
他閉上眼的時候,姚廣德攛掇他的話都變成了陰謀,他開始恨姚廣德,他覺得姚廣德這麼做,不但把他變成了牲口,也把自己的女子變成了牲口。他輕輕歎了一口氣,覺得這輩子不該活得這麼輕賤,盡管曾經無數次憤恨地提醒自己,但還是沒有經得住姚廣德設下的陷阱。他下了炕走到門口,企圖拉開門卻拉不開,他隻好蹲在門口,裹著炕上的被子,在門口睡著了。
他做了個夢,他夢到小時候,他和巧巧一起在張家圪嶗玩耍的情景。他跟著長工放羊,回到家,巧巧是快樂的,巧巧纏著他要吃杜梨,要吃馬茹子、蛇梅子,夢裏的張能能心裏藏著一個叫巧巧的妹妹。
張能能醒來的時候,一頭就栽在了姚廣德的腳下。姚廣德進門的時候,巧巧也醒了,看到倒在門口驚慌失措的張能能,姚廣德的目光充滿了鄙視和輕蔑。巧巧問他大,他怎麼在這裏?姚廣德說,他是你男人,不讓他在這裏睡,讓他去哪裏?張能能拍了拍土,站起來,奇怪地看著姚廣德。巧巧大聲問,他昨晚就在這兒睡的?姚廣德不等張能能說什麼,就吼著張能能說,舀在碗裏的飯你都等不及了,她遲早是你婆姨麼,牲口就改不了本性!姚廣德的話,讓張能能蒙了一下,而後笑了笑也不著急解釋。巧巧倒是反應快,裹著被子,撿起炕上的東西就往門口扔,一邊仍一邊罵張能能,二能子,你個畜生,好驢都不生養你!罵著扔著,張能能被姚廣德推出門去,巧巧就大聲哭了起來。
張能能在門口聽著姚廣德勸他女子說,嚎啥麼?你遲早也是二能子的婆姨,回頭大好好抽他鞭子!這孫子,來一趟膚施城,膽子大了。咱先別哭,大給你做主,咱回家好好商量商量!巧巧說,你也不管他,他害我這輩子,我這輩子就這麼完了……姚廣德說,沒完沒完,這牲口昨天吃了點好飯,那就張得不行,等我回去好好教訓他!孫子唉,巧,你別聲張,多大的事,咱先回家!
姚廣德反複勸說巧巧,巧巧慢慢地抽泣完了,一會兒聽到了收拾行李的聲音,他們出了門,張能能也早就把木桶背在身上了,就等一塊回家了。巧巧看到張能能,突然憤怒起來,拿起門口的鐵鍬要打,姚廣德使命地攔住,瞪著眼珠子說,有啥事不能回家說嗎?丟人不?姚廣德的話帶著很有威懾力的氣勢,巧巧扔了鐵鍬,獨自一個人向坡下走去。
姚廣德結了旅店的錢,心疼得不得了,看著巧巧一個人在前 麵走,對張能能說,二能子,咱這住一宿,花了不少錢,但是也值,我睡得挺舒服,還是牲口的日子舒坦!這話,張能能沒法接,但是心裏在想,牲口的日子好過,你狗日的咋不當牲口哩?姚廣德又說,二能子,皮帶和帽子咱先不買了,不是因為巧巧,是家裏還有,我結婚那會兒用過的,一次都沒有用,我做生意那會兒,皮帶多得很,有你用的。你要曉得,那東西現在都不時興穿戴了,裝個樣子嘛。你放心,你裝新的時候,就用這個!“裝新”這個詞,在陝北方言裏,意思就是結婚的儀式。新社會都說結婚,不說 “裝新”了,姚廣德突然冒出這一句,顯然是給張能能傳遞的是 “裝新”就是裝裝樣子。張能能說,大,我沒睡她!姚廣德停住腳步,一個耳光過來,張能能愣了一下,但是腰直溜溜地挺著,臉揚起來,目光直視著姚廣德。姚廣德說,這個時候你說這話,神鬼都不信!你騙誰呢?說得比唱得還好聽,你再說一遍試試!張能能說,我就是沒睡她!這一次,張能能的聲音硬朗得很,還帶點委屈。姚廣德想再來一個耳光,胳膊揚起來,又落在自己的腰後,一邊走一邊氣呼呼地說,做人不能提了褲子就不認賬!你現在說啥都沒用,狗屙下的都是你屙下的!
這話,姚廣德不講理了,但是,這種情況下沒法和他講理, 起碼姚廣德還是對他動用了心思。說明在姚廣德的心裏,他在擔
憂,在恐懼……出了大東門,一眼便看到了河對麵的山上,有座寺廟,寺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寺廟周圍的小道上,都是那些穿著土灰色軍裝的人。姚廣德下了小東門,看到張能能怔怔地看著對麵,奇怪地吼了他一聲,張能能沒有動彈,還站在那兒。姚廣德說,你看啥麼,喊你半天不應聲,狗看星星明上明!走!張能能說,大,那是啥?姚廣德轉過身看著對麵的寺廟說,那是 “是岸寺”!四月初八的時候,年年有廟會哩!張能能說,“是岸”?姚廣德說,對,回頭是岸!這地勢,回不回頭都沒岸!張能能說,大,你說得不對,這地勢,回頭是岸,低頭是岸,抬頭也是岸!姚廣德一時不知道該怎麼應對張能能,看他魂不守舍的樣子,索性不想理他,準備走,突然張能能又問,大,你看那寺廟是啥顏色?姚廣德說,能有啥顏色?啥顏色都沒有啊!你狗日的中邪了?張能能說,不對!大,你看滿山上下都是紅色!你仔細看!全是紅色!姚廣德順著張能能指的方向看去,山還是山,廟還是廟,山上的人還是那些人。姚廣德還想罵張能能,張能能已經下了坡,向石板路的河麵走去。
過了河,姚廣德就找不到了巧巧,返回去又找,還是不見, 再跑到東關路口等,等到下午,還是不見人。姚廣德著急,張能能也著急,他著急這會耽誤了馬幹部約定的時間。又說,要不你先等著找著,我去縣政府找馬幹部拉棉花籽。姚廣德突然想到,想去二十裏鋪找他姐,詢問一下巧巧的下落。去了二十裏鋪,他姐說,巧巧來過了,就一句話,誰也別來找她,誰找她,她就去死!巧巧這話說得斬釘截鐵,他姐又勸了一會兒姚廣德說,娃娃們的事情咱不懂,好賴活著就行,她肯定去找我家女子,兩個人也有照應,有了消息,我給你捎話。姚廣德像被霜打的茄子,半天沒說話,悶著頭離開二十裏鋪,一路上更不說一句話,一直到了縣政府的路口等著。張能能找到馬幹部,拉了驢和棉花籽,然後從懷裏掏出一個幹餅遞給延河,延河喜歡得不得了,馬幹部埋怨張能能說,怎麼又給她?張能能說,我大好容易大方一次,拿著!於是硬塞給延河,延河看著馬幹部,張能能反過來埋怨馬幹部,咋了?我還是群眾?我都學習過了,算半個幹部了,怎麼也算同誌了!被張能能這麼一說,馬幹部突然笑了起來說,當然是同誌了!好了,說好,以後不準再買了!張能能說,以後想買也買不著。馬幹部說,她這幾天要開會,過兩天再回張家圪嶗,你要按照崔幹部教你的辦法,趕快教大家種棉花。張家圪嶗的人都等著棉籽哩。又從窯洞裏拿出一套衣服和鞋來遞給張能能說,這是崔幹部送你的禮物,他上前線了,讓你穿著,當個念想!張能能看著那衣服和鞋,突然流出了眼淚,轉過身去,不看延河和馬幹部。馬幹部拍著張能能的肩膀說,你個大男人哭啥啊?說好了,是同誌,是同誌流血不流淚!張能能哭了一會兒,擦幹眼淚轉過身來,紅著眼圈說,姐,我回去一定按照你和崔幹部的指示,給咱張家圪嶗種出最好的棉花來!
馬幹部點點頭,突然笑了笑說,你剛才叫我啥?張能能說, 姐!馬幹部笑了笑說,這還差不多。你別嫌棄,這些也都是縣裏的老百姓給咱捐來的衣服和鞋,崔幹部舍不得穿呢,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等你種出了棉花,再還回來!張能能認真地點著頭,拉著驢轉身就走,遠遠地還能看到馬幹部抱著延河向他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