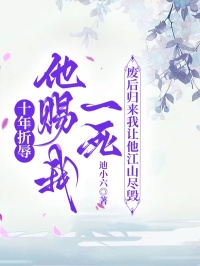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我曾是燕國最尊貴的公主,為了他蕭宇,甘願以質子妃的身份,在敵國受盡十年折辱。
助他登基那日,他卻下旨廢後,立了丞相之女。
他說:“朕的皇後,必須是清白的。”
我被賜毒酒那天,我的人拚死將我救出。
三年後,我帶著北狄的鐵騎,兵臨城下。
新後跪在我馬前,求我念及舊情,放過燕國百姓。
“他已經是一國之君,身不由己,你何苦要毀了他?”
我看著城牆上,那個身穿龍袍、臉色鐵青的男人。
我拔出長劍,架在新後的脖子上:
“蕭宇,開城門,我隻要她死。或者,我屠城。江山和美人,你選一個。”
他沒有猶豫,嘶吼道:“開城門!”
我笑了,收回劍,扔到他麵前:
“不,我要你親自下城樓,用這把劍,殺了你的新皇後。”
......
我話音落下,整個戰場死寂。
那把曾隨我征戰,飲過無數敵人鮮血的劍,就那樣躺在蕭宇與柳如月之間,劍身映著天光,也映著城牆上他鐵青的臉。
柳如月癱軟在地,梨花帶雨的臉轉向城樓。
“陛下!不要聽她的!她瘋了!她就是要毀了你,毀了我們大燕!”
她聲淚俱下,轉向我時,聲音卻壓低了,帶著一絲惡毒的挑釁。
“溫姐姐,對不起,這個事是我的錯,要打就打我吧,別怪......別怪陛下了。他是一國之君,身不由己啊。”
我居高臨下地看著她。
這套綠茶話術,十年了,一點長進都沒有。
“身不由己?”
我笑了。
“是身不由己地廢了我這個舊後,還是身不由己地立了你這個新後?”
“是身不由己地賜我毒酒,還是身不由己地睡在你床上?”
我的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傳到城樓之上。
蕭宇的身體明顯一僵。
“溫姐姐,你怎麼能這麼說......我與陛下的情意,日月可鑒。你不要因為恨我,就汙蔑我們。”
柳如月哭得更凶了,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汙蔑?”
我像是聽到了天大的笑話。
“行啊,那你倆現場表演一個情比金堅我看看。”
“蕭宇,下來。”
我用馬鞭指著地上的劍。
“殺了她,證明你對我的情意,才是真的。”
“你敢嗎?”
城牆上的蕭宇,拳頭緊握,一言不發。
他當然不敢。
柳如月的父親是當朝丞相,朝中一半的勢力都握在他手裏。
殺一個柳如月,等於動搖他一半的江山。
我太了解他了,這個男人,最愛的永遠是他的皇位。
“姐姐,你何苦要這樣逼陛下?”
柳如月楚楚可憐地開口,“我知道你恨我,你殺了我就是了,求你不要為難陛下了,他心裏是有你的......”
她說著,竟真的顫巍抖抖地伸出手,去拿地上的劍,作勢要往自己脖子上抹。
動作慢得,生怕別人攔不住。
“夠了!”
城樓上的蕭宇終於嘶吼出聲。
他死死盯著我,眼睛裏全是紅血絲。
“燕姝!你到底想怎麼樣?財富?地位?除了皇後之位,我什麼都可以給你!你何必非要如此咄咄逼人!”
“哦?是嗎?”
我挑眉,“那我想要你這身龍袍,你給嗎?”
“你!”
他氣得說不出話。
“你看,你又給不起了吧。”
我攤手,一臉“我就知道”的表情。
“說到底,你所謂的‘什麼都可以’,不過是你指縫裏漏下的殘羹冷炙。蕭宇,收起你那套虛偽吧,老娘不吃這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