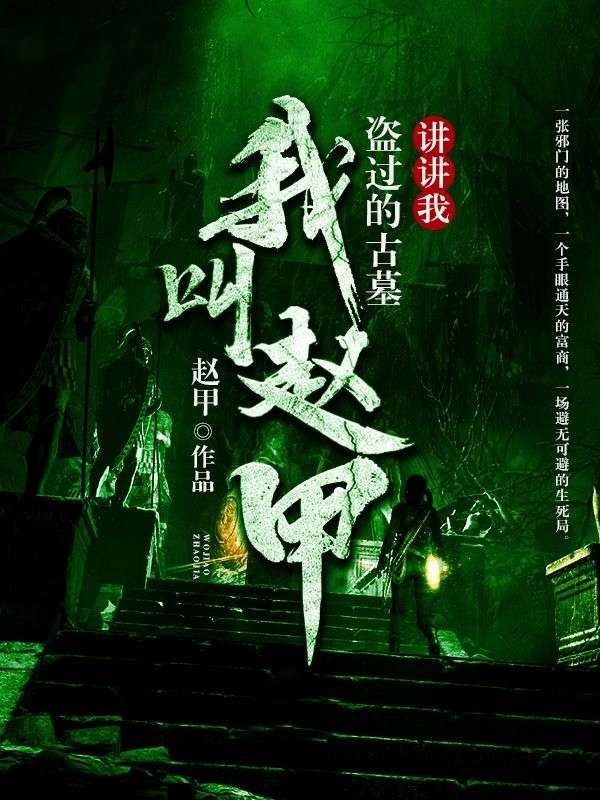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7章
“這是?”我抬起頭。
“這是我從一個收藏家手裏高價買來的。”錢宏業說道,“據他所說,照片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個探險家在中國西南部拍攝的。”
“那個探險隊,除了他一個人重傷逃回來之外,其餘的人,全都死在了那座古墓裏。”
“而他帶回來的,隻有這幾張照片和一些關於巴王詛咒的隻言片語。”
我看著照片上那口詭異的青銅棺,心裏沒來由地升起一股寒意。
陳瞎子說得沒錯,這趟活兒,是真正的硬活兒。
“好。”我收起照片和地圖,“三天後,早上五點,我帶人等你。裝備和車,你來準備。”
“一言為定。”錢宏業站起身,整了整西裝,“趙老板,別讓我失望。我這個人,對朋友向來慷慨,但對敵人,手段會比較難看。”
說完,他不再看我,轉身拉開卷簾門,消失在了夜色中。
鋪子裏又隻剩下我一個人。
我沒有時間去感慨,立刻拿出手機,撥通了幾個爛熟於心的號碼。
“胖子,是我,趙甲。別睡了,有大活兒,你幹不幹?”
“九川,手上的零活兒先放一放,來山城找我,有筆買賣,夠你吃十年。”
一夜之間,幾個電話打了出去。
我那些曾經一起在刀口上舔血的兄弟,無論他們現在身在何方,在做什麼。
我知道,他們接到我的電話,一定會來。
因為,我們是過命的交情。
三天時間,轉瞬即逝。
這三天裏,我吃住都在鋪子裏。
錢宏業很守信用,一百萬很快就打到了我一個幹淨的空賬戶上。
錢一到賬,我就像一台生了鏽的機器,重新開始瘋狂運轉。
第一個到的是胖子。
他是我在道上認識的第一個朋友,大名王德發,因為體型敦實,大家都叫他胖子。
這家夥是安徽人,祖上是搞土方工程的,說白了就是挖墳的。
他到的時候是第二天下午,背著一個比他人還高的登山包,一進門就把包往地上一扔,震得地麵都顫了三顫。
“甲哥,你這回是捅了多大的婁子,這麼急著叫我過來?”
胖子一屁股坐下,拿起桌上的茶壺,對著壺嘴就咕咚咕咚灌了個底朝天。
他抹了把嘴,眼睛卻盯著桌上的羊皮地圖和那幾張黑白照片。
我沒說話,隻是把信封推了過去。
胖子拿起照片,一張一張地看,臉上的嬉皮笑臉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臉凝重。
“乖乖,這是商周的青銅槨啊。”他拿起放大鏡,湊到照片前仔細端詳。
“甲哥,這紋飾是巴人的饕餮紋,不對,裏麵還混著......是鳥圖騰,這是蜀地的東西!巴蜀一體,這玩意兒邪門得很啊!”
“再看看這個。”我把羊皮地圖遞給他,順便將巴王墓和詛咒和他簡要說了一遍。
胖子倒吸一口涼氣。
“甲哥,你玩兒真的啊?這玩意兒要是真的,沾上的人都沒好下場!”
“沒得選。”我給他點了根煙,“有個大老板盯上我了,不做也得做。”
胖子抽了口煙,沉默了。
他知道我的脾氣,要不是被逼到份上,我絕不會碰這種要命的活兒。
“幹了!”他把煙頭往地上一扔,狠狠地踩滅,“媽的,大不了就是個死!甲哥你一句話,上刀山下油鍋,我胖子要是皺一下眉頭,就不是你兄弟!”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心裏一陣暖流。
這就是過命的交情。
第二天晚上,九川也到了。
九川,真名張九川,平時話不多,但心思比誰都細。
他是山西人,家裏世代都是礦工,對山石結構,地質走向的了解,比大學教授還厲害。
更重要的是,他是個玩炸藥的好手,能把爆炸的威力和範圍控製得分毫不差。
下地的時候,遇到死門或者塌方,全靠他來開路。
我把情況跟他一說,他連眼皮都沒抬,隻是淡淡地回了兩個字:“幾時走?”
人齊了,剩下的就是準備家夥事。
我和胖子跑遍了山城的五金市場和勞保用品店。
洛陽鏟、繩索、攀山扣、防毒麵具、氧氣瓶、強光手電、固體燃料......能想到的,一樣不落地備齊。
我們沒買新的,專挑那些半舊的買。
這行當裏,一身嶄新的裝備下地,跟在腦門上寫著我是新手,快來坑我沒區別。
九川則把自己關在鋪子的後院裏,搗鼓他那些瓶瓶罐罐。
我知道,他是在根據那幾張照片裏的地質環境,調配最合適的炸藥配方。
三天時間,就在這種緊張而又有條不紊的準備中過去了。
第四天淩晨四點,天還沒亮,山城還沉浸在一片濃霧之中。
我們三人收拾好所有的裝備,裝上了一輛事先買好的二手五菱宏光。
“甲哥,真就咱們仨?”胖子一邊把一個沉重的裝備包往車上扔,一邊問道,“對方可是大老板,人多勢眾,咱們這點人手,不夠塞牙縫的。”
“人不在多,在精。”我看著遠處還未蘇醒的城市輪廓,說道,“這次下地,靠的不是打架,是本事。”
“錢宏業的人再能打,到了地底下,也是睜眼瞎。我們才是主導。”
我發動了汽車,破舊的五菱發出轟鳴聲,像一頭老黃牛,載著我們三個,和一車的裝備,駛入了黎明前的黑暗。
車子一路向南,在五點鐘準時抵達了山水碼頭。
江邊的霧氣比城裏更重,能見度不到十米。
碼頭上空無一人,隻有幾艘破舊的漁船在渾濁的江水裏輕輕搖晃,偶爾能聽到幾聲嘶啞的汽笛聲。
我們把車停在碼頭邊上,熄了火,靜靜地等待。
胖子有些沉不住氣,摩挲著手裏的工兵鏟:“那姓錢的不會放咱們鴿子吧?”
“不會。”我搖了搖頭,“他比我們更急。”
話音剛落,遠處濃霧裏,亮起了兩道刺眼的白光。
一輛黑色的奔馳越野車,悄無聲息地滑到了我們旁邊,穩穩地停下。
車門打開,錢宏業從副駕駛上走了下來,依舊是那身筆挺的西裝,在這荒涼的碼頭上顯得格格不入。
他身後,跟著下來四個穿著黑色作戰服的壯漢。
這些人跟之前的保鏢不同,身上沒有那種市井的痞氣,而是從屍山血海裏爬出來才有的殺氣。
他們每個人都背著戰術背包,手裏拎著武器箱,動作幹練,眼神像狼一樣警惕地掃視著四周。
錢宏業走到我的車窗前,敲了敲玻璃。
我搖下車窗。
“趙老板,很準時。”他臉上帶著微笑,“看來,我的合作夥伴,已經準備好了。”
我沒理會他的客套,目光越過他,看向那四個壯漢,最後落在他身上,緩緩地說道:“錢老板,出發前,我得先跟你立個規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