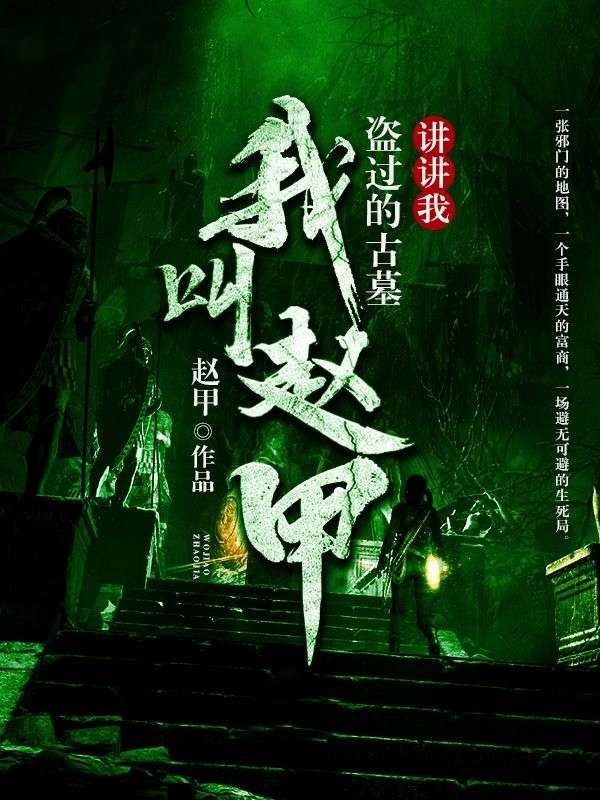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5章
電話那頭的女人,阿蓮,全名陳雪蓮。
她不是我什麼舊情人,她是我師父劉半尺的親閨女。
我和阿蓮的關係,很複雜。
我剛跟著師父那會兒,還是個十六歲的毛頭小子,愣頭青一個。
阿蓮比我小兩歲,紮著個馬尾辮,眼睛又大又亮,就像是那個烏煙瘴氣的江湖裏唯一的一抹亮色。
師父是個老派人,覺得幹他們這行的,都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不想讓女兒跟著摻和。
所以阿蓮從小就被寄養在親戚家,隻有放假才回來。
那幾年,是我這輩子最快活的日子。
白天,我跟著師父學本事,學怎麼看土,怎麼使鏟,怎麼辨認明器。
晚上,猴子出去鬼混,我就留在家裏,聽阿蓮給我講學校裏的事。
她會給我講那些我一輩子都搞不懂的函數和公式,會嘲笑我連英文的ABC都認不全。
那時候,我總覺得,等我學成了本事,賺夠了錢,就金盆洗手,帶著她離開這個鬼地方,去過安安穩穩的日子。
可我忘了,江湖是個大染缸,進來容易,想幹幹淨淨地出去,比登天還難。
師父出事那天,阿蓮就從我的世界裏消失了。
我隻知道她輟了學,跟著一個南方的老板走了。
我給她打過幾次電話,她要麼不接,要麼就冷冰冰地說,讓我以後別再找她,她不想跟我們這種陰溝裏的老鼠有任何關係。
我知道,她恨我們這些盜墓賊。
這些年,我偶爾會從道上的朋友那裏聽到一些關於她的消息。
說她成了好幾個大老板的紅人,手腕了得,人稱蓮姐。
我沒想到,她會接到我的電話。
更沒想到,她會用那種輕佻的語氣跟我說話。
“阿蓮,幫我給錢宏業帶句話。”我壓下心裏的翻江倒海,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
電話那頭又是一陣沉默,然後阿蓮的笑聲傳了過來。
隻是那笑聲裏帶著一絲涼意:“錢宏業 可是咱們山城的大人物,我可高攀不上。”
“你攀得上。”我打斷她,“我聽說,觀山茶樓的幕後老板,是你現在的幹爹。”
阿蓮的笑聲戛然而止。
“你調查我?”她的聲音冷了下來。
“我沒那閑工夫。”我說道,“道上的消息,傳得比風快。”
“阿蓮,我不是在求你,我是在跟你做一筆交易。你幫我帶話,這個人情,我記下了。以後但凡有用的著我的地方,我趙甲萬死不辭。”
“你的人情?”阿蓮, 嗤笑一聲,“你的人情值幾個錢?能讓我死去的爹活過來嗎?”
這句話像一把刀,狠狠地紮在我的心口。
我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
“阿蓮,算我求你。”我的聲音有些沙啞,“這次的事情,關係到我的身家性命。不然我絕不會來找你。”
電話那頭,長久地沉默了。
我甚至能聽到她那邊傳來的,輕微的呼吸聲。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才緩緩地開口,聲音裏帶著一絲疲憊:“說吧,什麼話?”
我心裏一塊巨石落了地。
“你告訴錢宏業,就說巴王咒的鑰匙,在我手上。”
“他要是想要,讓他明天晚上十點,一個人來我鋪子裏。記住,隻能他一個人。要是多帶一隻蒼蠅,我就把那張圖燒了。”
“巴王咒?”阿蓮的聲音裏帶著一絲疑惑。
“你不用管這是什麼,把話原封不動地帶到就行。”
“好。”她答應得很幹脆,“話我幫你帶到,這次之後,我們兩清了。”
電話被掛斷了。
我聽著手機裏的忙音,心裏五味雜陳。
我掐滅了煙,從床上站了起來,走到窗邊。
外麵的天色已經完全黑了。
山城的夜景,燈火璀璨,像一條流光溢彩的銀河。
明天晚上,錢宏業會來嗎?他會來嗎?
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回了雜貨鋪。
鋪子還是老樣子,一股子塵土和老木頭混合的味道。
我把卷簾門拉下一半,擋住了外麵的光線,也擋住了窺探的視線。
我沒打算坐以待斃。
這裏是我的地盤,就算是龍,來了也得給我盤著。
我從床底下拖出一個沉重的鐵箱子,打開來,裏麵是用油布一層層包裹著的東西。
我解開油布,露出裏麵冰冷的鋼鐵光澤。
一把五四式手槍,還有一個滿倉的彈夾。
這東西是師父留下的,壓箱底的玩意兒,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能動。
但現在,就是萬不得已的時候。
我把槍別在後腰,用衣服蓋住,那冰冷的觸感,讓我心裏稍微踏實了一點。
夜,很快就來了。
我沒開燈,就坐在那張油膩的八仙桌後麵。
桌上放著一盞老式的煤油燈,豆大的火苗在昏暗中搖曳,把我的影子投在牆上,張牙舞爪。
那張羊皮地圖就攤在桌上,在燈光下泛著詭異的黃光。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每一次門外有汽車經過,或者有野貓的叫聲,都會讓我的神經繃緊一下。
我不知道阿蓮是怎麼給錢宏業帶的話,也不知道錢宏業到底信了多少。
這就像一場心理戰,比的就是誰先沉不住氣。
晚上九點五十分,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十分鐘。
就在這時,一陣輕微的汽車引擎聲在鋪子門口停了下來。
是好車。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房門。
車門打開,又關上。
然後是一陣腳步聲,正對著我的鋪子走來。
腳步聲在門口停住了。
幾秒鐘後,那拉下一半的卷簾門,被人推了上去。
一個人影,逆著門外的路燈光,站在了門口。
他身形高大,擋住了大半個門框,雖然看不清臉,但那股迫人的氣勢,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錢宏業,是一個人來的。
“趙老板,好雅興。”錢宏業的聲音在安靜的鋪子裏響起,帶著一絲嘲弄,“怎麼把自己家搞得跟個老鼠洞一樣?這麼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