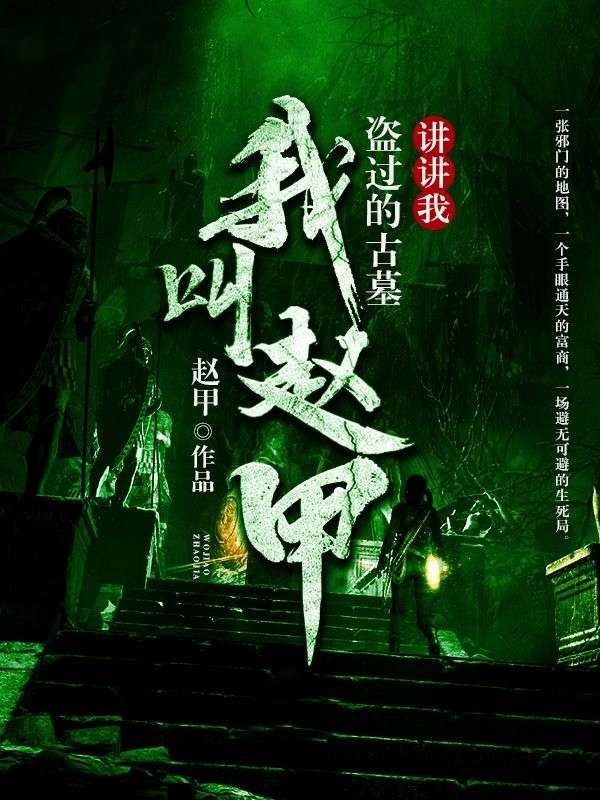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3章
我心裏咯噔一下。
硬活兒的意思是這趟買賣不簡單,風險極大。
“陳先生,您給說道說道?”我趕緊又給他續上茶水。
陳瞎子指著地圖上那些鬼畫符一樣的符號,說道:“這東西,不是地圖,至少不全是。”
“那是什麼?”
陳瞎子的臉色變得有些嚴肅,“你看這幾個符號,這是古時候巴人的文字,早就失傳了。”
“我也是早年在一本殘缺的古籍上見過。這種文字,是專門用在祭祀和巫術上的。”
“巴人?”我愣住了。
巴國是戰國時期存在於川部地區的一個古老王國,充滿了神秘色彩,傳說他們的巫術非常厲害。
“沒錯。”陳瞎子, 手指點在地圖中央,那裏畫著一個類似眼睛的圖案,“這個圖案,在巴人的文化裏,代表著祖靈之眼,意思是祖宗的眼睛在盯著你。”
“畫這個圖案的地方,通常都是禁地,要麼是祭祀的聖壇,要麼就是王族的陵墓。”
他接著說:“這上麵畫的,是巴王咒。意思是說,擅自闖入禁地的人,會受到巴王的詛咒,永世不得安寧。”
聽得我後背直冒冷汗。
幹我們這行的,雖然嘴上說不信鬼神,但心裏多多少少都有些忌諱。
尤其是這種跟古老巫術扯上關係的東西,更是讓人心裏發毛。
“那這圖上標的地方,到底在哪兒?”
陳瞎子搖了搖頭:“這我就看不出來了,這圖畫得太寫意,沒有參照物。”
“不過,既然寫了蜀南,又跟巴人有關,我猜,應該是在川南涼山一帶。”
“當年巴國被秦國所滅,有一部分巴人就逃進了涼山,和當地的部族融合了。”
他把地圖推回到我麵前:“趙甲,聽我一句勸。這趟活兒,水太深,你把握不住。為了點錢,把命搭進去,不值當。”
我沉默了。
陳瞎子的話,把我心裏那點貪念澆滅了一大半。
我收起地圖,從口袋裏掏出五百塊錢,放在桌上:“謝了,陳先生。”
“錢就算了。”他擺了擺手,“你師父劉半尺,當年跟我還有點交情。”
“我不想看到你也走他的老路。這行當裏,最可怕的不是地下的東西,是人心。”
我沒再堅持,衝他拱了拱手,轉身離開了。
雨越下越大,我沒有打傘,任由冰冷的雨水澆在身上。
腦子裏亂糟糟的,一邊是劉疤子許諾的巨大利益,一邊是陳瞎子的警告和師父慘死的畫麵。
我回了鋪子,渾身濕透,卻感覺不到一絲寒冷。
我把那張羊皮地圖扔在桌上,心裏煩躁到了極點。
去,還是不去?
這個問題,像個魔咒一樣,在我腦子裏盤旋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頂著兩個黑眼圈,做出了一個決定。
我得去會會劉疤子。
不是去答應他,而是要去探探他的底。
他到底是從哪兒弄來的這張圖?那幾個小崽子又是誰?
不把這些事情搞清楚,我寢食難安。
要找個存心躲你的人不容易,但要找劉疤子這種滾刀肉,太簡單了。
他這號人,離不開兩樣東西。
酒和賭。
我直接去了紅泥坡,那是山城棚戶區裏出了名龍蛇混雜的地方。
裏麵的小茶館、棋牌室、錄像廳,都是些不見光的生意。
劉疤子隻要在山城,十有八九就泡在這裏。
果然,我在一家叫兄弟茶館的麻將館裏找到了他。
所謂的茶館,其實就是個煙霧繚繞的賭檔。
我進去的時候,裏麵嘩啦啦的麻將聲震得人耳朵疼。
劉疤子赤著上身,露出精瘦的排骨和幾處歪歪扭扭的紋身,正唾沫橫飛地跟人爭論牌局。
我沒吱聲,走到他身後,拉了張椅子坐下,給自己點了根煙。
一圈牌打完,劉疤子輸了錢,罵罵咧咧地把牌一推,這才注意到我。
他看到我,先是一愣,隨即臉上堆起了笑。
“哎喲,這不是趙老弟嘛!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他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怎麼,想通了?”
我沒理他這茬,把煙頭往地上一扔,用腳碾滅,淡淡地說道:“劉哥,借一步說話。”
劉疤子的笑容僵了一下。
他打量了我兩眼,大概是看我臉色不對,也沒多說,跟著我走出了麻將館。
我們走到一個僻靜的巷子口。
巷子裏堆滿了垃圾,一股子餿味。
“趙老弟,有話就說吧。”劉疤子靠在牆上,從口袋裏摸出一包皺巴巴的朝天門,遞給我一根。
我擺了擺手。
“劉哥,那張圖,我找人看過了。”我開門見山。
“哦?怎麼樣?”劉疤子眼珠子一轉,故作輕鬆地問道,“是不是個寶貝?”
我冷笑一聲:“寶貝?劉哥,你別跟我揣著明白裝糊塗。”
“我現在就想知道一件事,這圖,你到底是從哪兒弄來的?別跟我提那幾個小崽子,我不信!”
巷子裏的氣氛一下子就降到了冰點。
劉疤子的額頭上開始冒汗,眼神躲躲閃閃,不敢跟我對視。
這家夥果然沒說實話。
他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鐘,最後像是泄了氣的皮球,把手裏的煙狠狠地摔在地上。
“媽的!”他低聲罵了一句,抬起頭,眼神裏帶著一絲恐懼,“趙老弟,算哥哥我錯了,不該瞞你。這圖不是我收來的,是我偷來的。”
我眉毛一挑,示意他繼續說。
“前段時間,我手頭緊,在道上接了個水活兒。”
水活兒指的不是下水,而是入室盜竊。
“主家是城西一個姓錢的富商,家裏收藏了不少古董。”
“我踩好盤子,半夜翻進去,東西都得手了,準備走的時候,無意間發現他書房裏有個暗格。”劉疤子的聲音壓得更低了,“我當時就動了貪念,把暗格撬開了。裏麵沒金沒銀,就一個鐵盒子,這圖就在鐵盒子裏。”
“姓錢的富商?”我心裏琢磨著這個名字,沒什麼印象。
“這人不是道上的,是個正經生意人。”
“我偷了他家東西,第二天新聞都報了。”
“但我看他報失的單子上,根本沒提這個鐵盒子和這張圖。”劉疤子咽了口唾沫,“我就覺得這玩意兒肯定不簡單。”
“可我找了好幾個人看,都看不出個所以然。後來聽人說這圖可能是從土裏出來的,我這才想到了你。”
“至於那幾個小崽子和那個爵,”他苦笑了一下,“都是我編出來的。那個爵是我從別處收來的,就是想讓你相信,這圖下麵有貨,引你入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