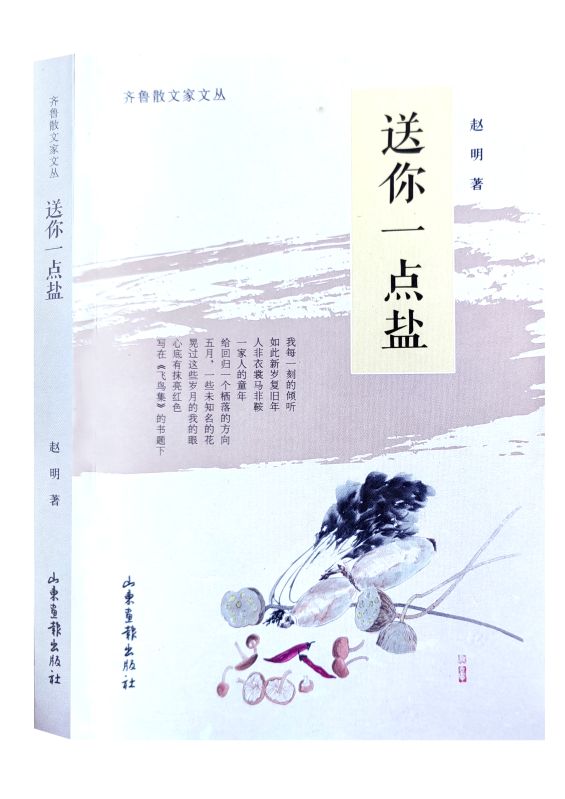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祝 福
祝 福
文文還是小嬰孩的時候,長得挺胖的,憨憨地笑,彎彎的眼睛,圓嘟嘟的臉,小彌勒佛似的,偏偏那時候我在打扮孩子的想法上,主張花團錦簇的熱鬧,願意讓她帶著世俗的歡樂喜慶與萬物眾生同喜同樂,大紅花的棉襖、棉褲,還千方百計的找到碩果僅存的民間高人繡上一個老虎頭的小襪登,左看右看如同吉祥物一般的這個孩子,覺得這才是胖娃娃應有的形象,所以回娘家的時候,也就無需左手一隻雞,右手一隻鴨,隻這一個便是大寶貝,足以叫姥爺、姥娘眉開眼笑的。可是,那天又和大家欣賞玩話,喜不自勝之時,這孩子她舅舅突然斜我一眼,來了這麼一句:
“姐,你家寶貝可以有一稱。”
“什麼?”我聽慣了大家的讚揚,可是仍然樂此不疲。沒成想聽到了這樣的一句:
“村長!”
嗨,當初這小子上學的時候,最怵頭的就是寫作文,沒想到後來卻屢有驚人之句,他這句話一出口,一家人哄堂大笑,從此,“村長”倒是成了文文的昵稱,到現在仍然時常夾雜在一家人的玩笑話裏。
村長就村長,你還別把村長不當幹部,中國現行的行政體製,隻有村長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你也許可以當上個別的什麼長,這個村長,還真不是想當就能當得上。
轉眼就是14年,“村長”出落成了大姑娘,整天忙忙碌碌,雷厲風行的,還真的不亞於真正的村長,當媽的我,伺機“村長”不忙的時候,和她一起出去逛逛街,遊遊景,聽著左鄰右舍、親戚朋友,驚奇的說著差不多同樣的話:
“這才幾天啊,這閨女怎麼一轉眼就長大了呢?看這個子,都趕上媽媽了!”
每當這時,我會自豪的側目身旁的這位花季少女,感覺到自己這麼多年的忙碌,也算是成績顯赫。
隻是,當年的“村長”,卻沒有承襲那種大紅大綠的審美,穿衣服就愛黑與白,我倆逛商店,我對衣服也是百般的挑揀,好歹看上一件上眼的,剛剛一留意,這孩子冷不丁的就會來一句:
“給誰買啊?我姥娘,還是我奶奶?”
嗨,就她這一句話就足可以讓我放棄了,外甥真的隨舅?
又一次,我想,不妨順其道而行之,買去給了她姥娘,不想我媽這次倒真的滿意的不得了,說這回買的還算是稱心,我也不好再說什麼,隻一句話說的她莫名奇妙:
“謝村長!”
這說著說著,“村長”她姑姑就有了孩子,而且是龍鳳胎,昨天這對寶貝滿了一百天,當地的風俗這一天要慶賀一下,孩子長命百歲,大富大貴,叫做過“百歲”,親戚朋友大歡聚,隆重慶賀,讓我們開眼的是,見到了老家親戚手工繡成的小老虎玩具,還有貓頭枕頭,我和文文對這些東西都很“感冒”,看來看去的隻覺得祥和喜慶、好玩有趣,這一刻,我知道當初我給那個小嬰孩埋下的審美種子,發芽了。
再看看那對龍鳳胎,人家穿得那叫一個素雅,我和文文打趣:
“你看弟弟妹妹,穿得多洋氣,你小時候是村長,他們該叫?”
文文嘻嘻地笑了起來,那一種默契就那麼響亮:
“市長!”
哈哈,讓我們一起祝福兩位“市長”健康成長。
(寫於2010年3月)
###找回感覺 再過年
早晨醒來,望向窗外,才知道下雪了。窗玻璃上飛著一條條白色的長線,斜斜的畫著,似乎在強調著年節的氣氛。
還沒有放假,踏雪上班,白色的雪線,悠著路邊大紅的燈籠,輕輕地晃動,冰冷的時光裏,流動著熱烈。
每當這個時節,就會覺得,自己與周圍的景色,有了一種融合的親切,找到了家園的感覺,人會變得單純而熱情,仿佛回到了童年。
真的很奇怪,常常感覺,童年的時光,與現在分布在兩個空間裏,盡管還是同一個地方,可是人也不是那些人,景也不是那些景。
可是每當年節裏,我會在空氣裏,嗅到那一種來自時光裏的傳承,靜靜的古老,從城東的那個老家所在的院落裏,散發出來,那棵老石榴樹,還在酣然冬眠,祖母拿著祭天用的香供從大西屋的台階上緩緩地走下,空氣中摻雜著新炸鞭炮的硫磺味道,混著過年大菜酥鍋的香氣,大黃狗汪汪地叫著,迎接我們全家的到來,團圓了,過年了。
我知道,這種感覺就在我的血液裏沉寂著,隻是,在忙碌的腳步裏,在茫然的日常中,在虛浮的世事中,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雪,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有鞭炮聲在周圍零零落落。
想起,文文昨天的一個問題:“媽,你知道我們現在住的這小巷的名字嗎?”
非常應該回答的問題,而我真的惘然。
“叫做"花枝巷"。是個老名字呢。”她也隻好自問自答。
是的,好像聽說過這兒從前一片果園,每到春天,春色滿園。
在習慣了幾棟幾單的叫法的現今,我竟然住在這樣一個有些曆史的像春天一樣美麗名字的地方,而且不知不覺,真不知這日子是怎麼過的。
更不用說,門口的小銀杏樹,小巷深處的幾戶平房的幾戶人家,還有理發的、買飯的那些小小的門頭,他們一直都在這裏嗎?文文長大以後,海闊天空的世界裏,還會有這條小巷的影子嗎?
世界這麼大,時光那麼長,而我們的坐標在哪裏呢?在這些文字中嗎?
如果沒有了感覺,什麼都沒有了。
我覺得應該就在那些找回的感覺裏了。
找回感覺,再過年。
(寫於201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