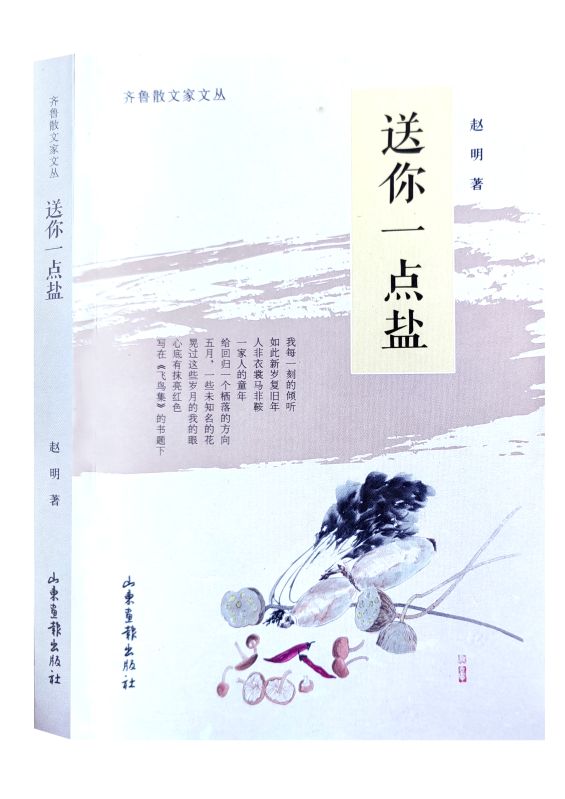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心靈的熱望
7月11日,季羨林走了。
98歲的這位老人,走在這樣一個荷花盛開的季節。北大朗潤園的那一塘季荷,不知是否也有靈犀一點的憔悴。
而我的眼前,卻總是晃動著這樣的一個身影:一位清臒的老人,走在荷花盛開的水塘邊,與那些兀自盛放的荷花相對,那兩句據老人說對仗並不工整的詩句忽然現於腦際:池花對影落、沙鳥帶聲飛。現在,荷花依然盛放,那個與荷相對低語的身影,哪裏去了?
我想起了山東臨清老人老家屋後的,那一個水塘,6歲的季羨林“撲通”跳入水中,就像一條自在的魚,隻為躲掉母親因為他偷吃了白麵饅頭的追打,而就在入水的那一刻,母親卻笑了,季羨林也笑了。這笑聲,一直陪伴著老人走過對母親的追思,笑成湧不完的兩行熱淚。90多年以後,老人說了這樣一句話:“我這一生,最後悔的事情就是太早就離開了老家臨清,沒有陪伴自己的母親。”作為國學大師的他,總結自己的一生,其實最願意過的卻是普通人最普通的日子,隻要這樣的日子裏,伴隨著至親的情義。子欲養而親不在,這是一樁多麼大的憾事。
我想起,在德國小鎮哥廷根的老街舊巷裏,那個懂得“土火羅”語的青年,對遙遠的東方故裏的深深的思戀,而在毅然返回祖國後,哥廷根又成為他記憶中的第二故鄉,他每每說起這種感受,都會想起這樣的一個句子:客樹回看成故鄉。
我想起,那一年北大開學之際,那個為新生看行李的老人,那位被那個粗心的學生連同行李一起忘在了荷塘邊的那位老師傅,一直守候在那一堆行李旁,那時的他,除了默默的守候,好像別無選擇,就是這樣的一則季羨林的故事,讓我對北大的精神內蘊,有了更深的崇慕。
我想起了那些與老人相伴一生的貓,那個因為愛搶食而被老人稱為:“大強盜”的大白貓,出現在老人的《清塘荷韻》中的矯健的身影,大概此時還在荷塘邊盼望老人的親切的重歸,我想起,老人說起那隻叫做“虎子”的老貓,為了不讓老人看見它的“老死”,而離家出走的那一種自尊和倔強,老人說起這件事的那一刻,眼中又一次蓄滿了淚光。我想,在這一刻,老人與那隻老貓息息相通。
真的,我喜歡這個老人,就像仰慕一種平淡卻深遠的精神,雖然老人不在了,雖然有時候在繁忙的雜事的纏繞裏,好像記不起來什麼來了,雖然這位老人一點都不平淡,但是,他卻真的有一種言猶在耳的親切,跨越了如天書般土火羅文和印度梵語的神秘,走過了大半個世界的近一個世紀距離,就在身邊。我知道這種精神是最質樸和最真實的,它是我不能忽略的。
(寫於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