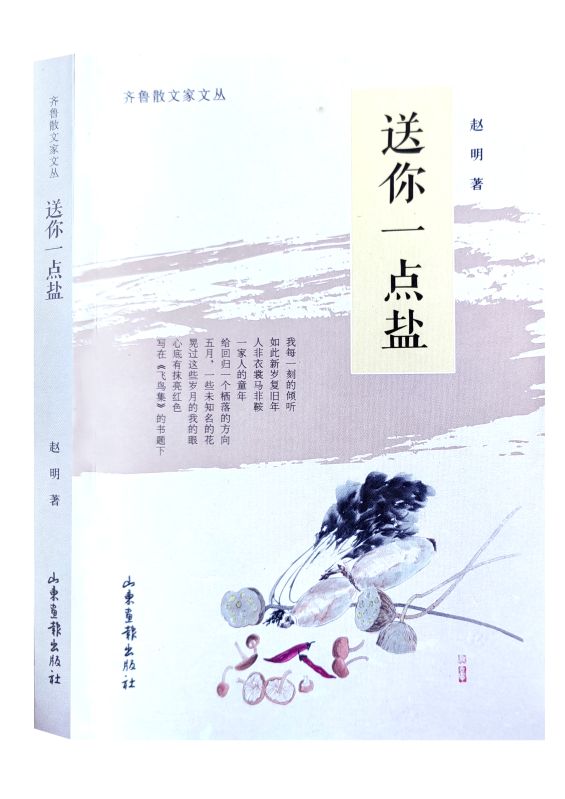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心意
曾用筆名叫怡悅
初春的一天,木蘭花開滿了萌山水畔,我們幾位當年報社的同事相約在那裏看春天。
夕陽下,春水在遠方半江瑟瑟半江紅,突然感知時光的風馳電掣是因為,其中的一位,想來竟至20年不曾謀麵。
“還記得,你那時有一篇寫華洋街元宵燈會的文章,題目叫做《傾城觀燈》!”這是這位當年的同事,對我的第一句寒暄,我一時有點發懵,“對了,你那時用的是筆名,叫做怡悅。”
繼而,我記得了這篇文章,當時也是非常得意這個題目所傳達的那種過元宵的隆重狀態,也還記得這個題目是來自清代黃遵憲寫櫻花的詩句:“傾城觀花奈花何,人人同唱櫻花歌。”
說起來,生活中的這些小喜悅真的是很多,比如對一個場景一句話的記憶,比如,在一些所思所想有了些微應和以後的那份篤定,比如於多年以後你的辦公室同事還記得你曾經用過的筆名。
就此想起了我的那些筆名。
怡悅這個名字隻是我眾多的筆名之一。“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雁飛滅”,這是唐朝孟浩然的詩句。怡悅這兩個字,正是從此處而來。既然是筆名,就不同於真名,把自己隱在北山白雲裏,就如同真的做了神仙,下筆也要有仙逸之氣了吧。那時的想法是,你的文章入得堂堂大雅,你就不該是吃喝拉撒的凡人,用的也就不該是你世俗生活中的名字。所以,一向羨慕古人有名有字有號的那一種自我的認知,比如我的老鄉,清代文人蒲鬆齡,姓蒲名鬆齡諱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自稱異史氏別號聊齋先生,隻此一人,先不用看那本著名的《聊齋誌異》,隻這些名號,好像就要占盡天下風華之辭筆。你可以無功名利祿,你可以潦倒窮困,你可以清雋孤冷,但這名字確實不可略缺一二,它是你為讀書人的狷狂疏放傲然自持獨立風骨,春風大雅,秋水文章,在你的名號裏先就略知了一二,也就如同你的亮嗓音美衣冠,你的雅思尋真性情。
名字有了,就要用,我那時是我們當地日報的副刊編輯,卻也同時兼作要聞記者,一邊用真名在一版發新聞稿,一邊用筆名在四版發些小詩歌、散文,所以就常有人問我:“怡悅是誰?”這樣的時候,總是怯怯的,不知人家以下的話是什麼,就仿佛以此名拉上了一道幕嶂,垂了簾,聽聞關於自己的說道,褒貶由之,也就獲得一種跳脫的從容掩飾下的忐忑,那是很新奇的感覺,我想,這也是有個筆名的好。
在一個風花雪月的名字裏,你且安逸地飲一杯香茗寫幾行文句,放飛你的思路如同全新的自己,行吟放歌清高灑脫一如行雲流水,清風雅墨哪沾人間煙火。但是名字總歸是名字,它從無中而來,一路跟隨,不管你的文章是否真的能夠入得大雅,卻總要與你本身的真實融為一體。你還是要上班頂著壓力,下班洗衣做飯,老人要照顧孩子要監護,想著職場風雲人際繁雜晚上的應酬如果不去會是什麼後果……五花八門的小煩惱和小快樂一樣鱗次櫛比,真實的感受和感動都在生活的細節與現實中,再風雅的名字也帶不來形而上的生活。所以,筆意在你的筆名下有了一些經曆的滄桑,漸漸地回歸到真實的原位。
你知道了童年周樹人的《社戲》比成年魯迅的沉思更鮮活,老舍就因為在真實的《茶館》裏生活,人們才忘了他叫舒慶春,冰心如果不那麼玉壺冰潔可能讓你感歎的不止《繁星》《春水》,張愛玲就是覺得叫張煐和愛玲沒有什麼兩樣,才有了直麵自己內心深藏的《小團圓》,胡蘭成沒有因為名字的清雅而在《今生今世》中為人清直,三毛以兜裏隻揣三毛錢自嘲她卻有《送你一匹馬》的豪情,與荷西一起唱絕了《撒哈拉的故事》,林清玄說一個人後半生的容貌由性情決定沒有說因為名字,所以才覺得與他一起《溫一壺月下的酒》體會一下慢生活,一定別有品味……諸此等等。
所以,在叫過怡悅、曉明、文凡等一係列的筆名以後,我決定把筆名和真名融為一體,就叫父親給起的原名:趙明。其實,應該這樣說,甭管叫什麼,你還是你就好,也許我還會用一下我的筆名,也許它的作用是可以給我帶來心靈的一些向往的怡悅。如此說來,我的這個筆名不知是太有意味了還是太直白了。
我女兒文文曾經專門為我寫過一篇文章,我把它當成了我的文集《時間深處》的後記之一,題目是《時間深處.做一個快樂的孩子》,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
那個給我快樂給我成長給我安慰給我勇氣的她。
她不是別人,她是茗之趙明,是我的溫暖與家。
她是我媽。
每每想到這幾句話,我無論在什麼地方做著什麼,也會如同隱身北山白雲裏一樣突然不忍微笑起來,心中是自是最深的怡悅。
(寫於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