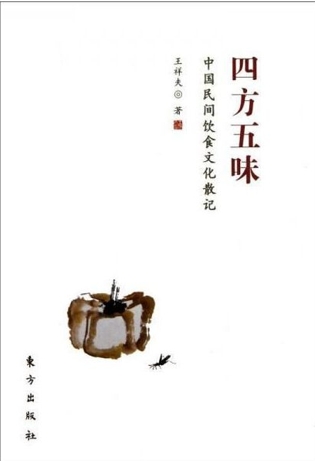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說 榆
我對榆樹是有點感情的。
現在仔細想想,我家早先那個院子好像隻有兩種樹,榆樹和楊樹。榆樹好像比楊樹還要多,除了老高老大的榆樹外,院子周圍還有不到一人高的榆樹牆。榆樹好像極能生蟲子,而且是那種個頭很大光不溜溜的紅色毛蟲,說它是毛蟲是有點高抬,它身上其實沒多少毛,隻有那麼幾撮兒,那幾撮兒毛又很長,所以它爬動起來就顯得格外張揚,它從樹上掉下來,先是會縮成一團兒,但馬上就會把身子舒展一下一下地爬動起來,這種蟲子有大人的食指那麼粗,如果它爬到街上去,恰巧給過往的車壓個正著,會給擠出一股白漿,不是一股,是一攤!我最怕的毛蟲就是這種,所以我總是不敢往榆樹上爬,但打榆錢兒的時候這種蟲子還沒生出來,到榆錢兒落了,榆樹葉子老了,這種蟲子才會出來。讓我害怕的是一位山東老鄉,居然說,這種蟲子很好吃,並且說,要用火烤了吃,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把這種蟲子扔在一堆樹葉子攏的火裏,過一會兒又把蟲子從火裏撥拉出來放在嘴裏。我問他什麼味兒,他說比螞蚱好,我說怎麼個好?他想了想,說:“肥!”
蟲子還能以肥瘦論之嗎?讓人不得要領。
我喜歡榆樹,榆錢兒下來的時候不少人都會去打榆錢兒,其實不是打,是把一大枝一大枝的榆樹樹枝折下來扛回去,榆錢兒要是能打下來必定是老了,老了的榆錢兒不好吃,吃榆錢兒要吃嫩的,是又嫩又甜。榆錢兒怎麼吃,用玉米麵和碧綠的榆錢兒合好,稍稍放一點水,合得鬆鬆散散,在山西北部叫“塊壘”,在山西南部叫“撥爛子”,總之是一小塊兒一小塊兒,絕不能粘連,然後放籠屜裏蒸,蒸好俟其稍冷再下鍋炒,要放大量的蔥花兒,還要放一點點鹽。這種飯,要配上小米子稀粥,最好,還要有一盤涼拌苦菜,這就是北方的春天了。因為打榆錢兒的關係,我們那裏的榆樹總是長得很高,細溜高細溜高,樹稍上的榆錢兒沒人打,夠不著,這樣的榆錢兒便會慢慢老了,黃了,白了,一陣風過來,像是下雪,飄飄飄飄地落下來,春天也就過去了。榆錢兒一落,夏天就來了。榆錢兒隻長在成了材的大樹上,小榆樹行子無榆錢兒可打,常見老頭老太太在榆樹牆那裏采榆樹葉兒,像采茶,挑挑揀揀,揀嫩的采,新嫩的榆樹葉子也很好吃,用水焯一下涼拌了,放嘴裏越嚼越黏乎。榆樹葉兒可以做菜團子,照例是用玉米麵,摻在一起合好,用兩手搏成團子上籠蒸,好吃不好吃且不說,顏色先就好看,黃綠相間格外醒目。
在北方,講究一點的人家不在家院裏種榆樹,“榆”和“愚”發音一樣,但河北一帶又愛在房子後邊種榆樹,這有個講頭,叫做“後邊有餘”,過日子有餘就好!
榆樹成材慢,能成大材者蓋不多見,晉北的家俱,講究一點都是用榆木做,“二月書坊”有一晉式炕琴,敦厚大氣,就是榆木所做,榆木結實耐用而且有好看的花紋,南方有一種木材學名叫“櫸”,而民間依然叫它榆,不過在榆字的前邊加一個字——“南榆”。
常見有人去剝給砍倒的榆樹的樹皮,砍了用車拉走,一整棵一整棵的樹都給剝得光光溜溜白得晃眼,榆樹皮給剝回去不是燒火,而是吃,把榆樹皮曬幹,上磨磨成麵,再一回一回地過籮,這種用榆樹皮磨成的麵叫“榆皮麵”,這種麵不能單獨用來吃,是要合在玉米麵裏,或者是和其它粗糧合在一起食用,無論再粗的粗糧,隻要一合上榆皮麵馬上就會變得筋道起來,可以壓成很細很細的麵條下鍋煮了吃。玉米麵做麵條,而且是細麵條,不用問,肯定是裏邊合了榆皮麵。這種麵不但筋道,而且滑溜。用白麵合榆皮麵擀麵條兒,那麵條兒就會筋道的過了頭,你挑起一筷子麵條兒,放嘴裏一吸溜,坐在對麵的人也許馬上就會有感覺,你說不定已經把麵湯彈在了人家的臉上!你看這麵條有多筋道!
我喜歡榆樹,試著種過幾次榆樹盆景,但都瘋長而不可收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