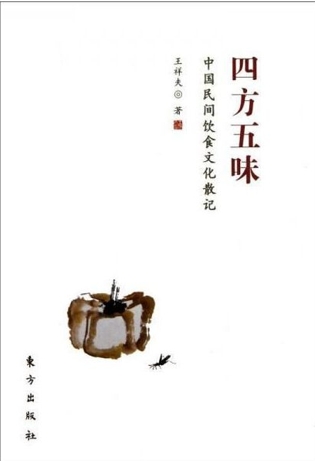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百菜不如白菜
各種的菜裏,白菜讓我最感親切。
我小的時候,每當家裏開始大批大批把大白菜買回來的時候,我就知道,冬天就要來了。那些年,幾乎是年年如此,父親請人用手推車把大白菜運回家裏,先是放在外邊晾一晾,然後才把它們放到小倉房裏去,我家的小倉房在正房南邊,快到冬天的時候裏邊就總是碼滿了白菜,當然大白菜最好是下到窖裏去,但我們隻有小倉房。大白菜放到小倉房裏,到了天氣最冷的時候上邊還要苫好幾層草袋子,這樣的白菜一般要吃到第二年春天。整個冬天,家裏人總是要到四壁皆是白霜的小倉房裏去翻大白菜,把下邊的倒到上邊,再把上邊的倒到下邊,讓它們的葉子既不能太幹,又不能爛掉。冬天的日子裏,幾乎是,飯桌上天天都是白菜,土豆白菜,蘿卜白菜,海帶白菜,有時候是豆腐白菜。母親有時候會用白如玉的大白菜幫子給我們來個“醋溜辣子白”。父親喜歡用白菜心和海蜇皮拌了吃,白菜和海蜇皮都切極細的絲,白菜絲用鹽抓過,海蜇絲用開水一焯,二者相拌,味道極清鮮,一盤這樣的菜,就二兩二鍋頭,簡直就是我父親的日課!春天來的時候,母親會把抽了花挺的白菜心放在水仙盆裏用水養,白菜花嬌黃好看,都說紅顏色喜慶,孰不知白菜花的黃顏色也喜慶!
白石老人喜歡畫白菜,且喜歡題“咬得菜根,百事做得。”而我最喜歡他在白菜旁邊題“清白家風!”白石老人畫的不是那種緊緊包住的“北京大白菜”,而是葉子散開的“青麻葉”,“北京大白菜”做醋溜白菜要比別的白菜好,吃涮羊肉也離不開它,吃菜包子就更離不開它,它的每片葉子恰好都像一隻小碗,正好讓人可以把餡兒放在裏邊,但這種白茶不好入畫,圓滾滾的。而青麻葉不但入畫還特別好吃,以青麻葉做菜泥,軟爛不可比方。醃東北酸菜也是用青麻葉,外邊的葉子打掉,整棵大白菜一劈為二,在開水鍋裏拉一下,然後就碼到缸裏去,不用放多少鹽,東北的氣溫可以讓它既慢慢變酸又可以讓它保持其脆勁。這樣的酸菜也隻好在東北才能吃到,要說做酸菜白肉,四川的泡菜不是那個味兒,韓國泡菜更不是那個味兒,東北酸菜好在本色,脆、嫩、白!吃酸菜白肉,最好是冬天,夏天不是吃東北酸菜的時候!說到吃,不單單水果是季節性的,酸菜也是季節性的。要吃四川泡菜,我以為最好是夏天,冬天吃四川泡菜,也不大對路!
冬天快要到來的時候,也是曬幹菜的時候,把小棵的白菜一劈四瓣掛在那裏曬幹,說是曬,其實是陰幹,要是曬,一過頭就黃了。幹白菜燉豆腐別是一個味兒,幹白菜和鮮白菜一道煮,又是一個味兒,味道都很厚,味道可以分厚薄嗎?真還不好說!冬天的日子裏,玻璃窗上滿是山水花草般的霜花,你坐在暖烘烘的屋裏,餐桌上是小米幹飯和幹白菜熬蝦米,這頓飯真是樸素簡單而好吃。直讓人想到周作人說喝茶的那幾句話:“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吃飯和喝茶雖不一樣,但小米幹飯加幹白菜熬蝦米會讓你覺出清淡中的滋味綿長。我現在是想的要比做的多,一年四季總是忙,幾乎是,年年都想曬那麼一點幹白菜,但每年照例都會忘掉,而現在的市場上又沒得幹白菜賣,起碼是,我經常去的沃爾瑪就沒有,那裏有幹豆角、幹茄子和幹葫蘆條兒,但就是沒有幹白菜,他們說幹白菜太麻煩,沒等賣多少就都碎了,碎糟糟像煙葉兒,所以現在不再進貨。
其實要想吃幹白菜還是自己動手去曬為好,今年秋天,也許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