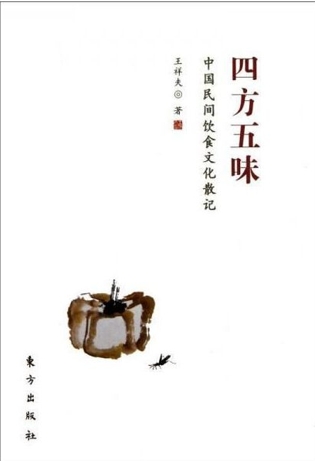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代序
無一例外的是,人生下來就得張嘴吃飯,一天不吃也不行,而且一直要吃到死。傳說中的道士辟穀不知誰見過,一天隻吃三枚癟棗而能鶴發童顏我總是有些不敢相信。古人偏會說話,字字句句原都經過錘煉,比如“食色”二字,誰前誰後大有講究,食在前,色在後,吃飽了肚子色膽才會像魚網樣鋪張開。餓著肚子色也不是色了,再好的色也不如一碗薄粥來得讓人恨不得叫爹叫娘。“人是鐵飯是鋼”的意思是什麼?鐵若是打成一把刀,如果沒有鋼來鑲刃子,又有什麼用?所以說,臥室內可以“金猊香冷,被翻紅浪”萬種風情,可以“水精簾裏珊瑚枕,暖香惹夢鴛鴦錦”,綺麗得緊,但就是不能與烏煙瘴氣的廚房相比。那原因是:廚房乃是人類一切活動的發動機部位。
那年我去湖南,看到那樣大的月牙型的灶,當下就渾身開了眼。那灶唯我獨尊蹲在廚房當中,四邊不靠,有獨霸天下的意味,讓主婦在那裏上演精彩的節目,把雞鴨魚肉和各種鮮嫩的蔬菜做成一盤盤一碗碗一碟碟的菜肴讓人垂涎三尺。灶上邊是通氣窗,那些臘著的雞鴨肉便從天窗上方吊下來,在暗處看,上邊有一點點閃爍的燈光,是油,欲滴未滴的樣子,讓人想到波羅的海的琥珀。
我是東北人,東北人做菜氣勢簡直是粗放,東北有大片的森林,不怕沒柴燒。肉大塊大塊地下鍋豪煮,土豆也隻一切兩三塊。我喜歡我母親做的春餅,包春餅的菜裏有綠豆芽、韭黃、雞蛋攤得薄薄的再切成細絲,還有肉絲,味道很好。吃春餅的時候必定是春天,我們弟兄都比賽著要把春餅包得最大最好,一個個像煞小枕頭,兩隻手捧著,餅烙得隻有紙那麼薄,看得見裏邊的內容。我母親現在已經垂垂老矣,不烙春餅已多年。飯菜店裏的春餅差遠了。還有就是春卷,春卷和春餅是不能相比的,意思雖然仿佛,但太小,又經過油炸,沒有自己動手的那種樂趣。再比如吃手抓飯,原是一種原始,也最直接,什麼也不用,野蠻人一樣直接下手。新疆手抓飯要用大量的油、羊肉和胡蘿卜。大量的油,少量的水,先把肉和胡蘿卜下進去,接著是大米,然後是慢慢把它燜熟。手抓飯油汪汪的,讓人無端端地覺著日子怎麼可以這樣富足而光輝,一大盤一大盤油汪汪地端上來,有喜慶的味道。吃手抓飯講究是大家席地而坐,然後是用手,這時候左手和右手是有嚴格分工的,右手在這時候就是調羹,抿抿捏捏,一球一球地往嘴裏送。世界上許多民族吃飯都隻用手。印度人和非洲黑人也是這樣。說到非洲,非洲的女人不去打獵,卻要到林子裏去采集花花綠綠的蟲子,非洲的那些蟲子都好像過節日樣盛裝著,花花綠綠,風騷的樣子,被非洲女人放在一大片葉子上帶回家,便是道好菜。還有蟻卵,一顆一顆晶瑩剔透,非洲人就在蟻穴邊品嘗他們的美味,就像我們在葡萄園裏摘葡萄吃,那蟻卵也大,像剝了皮的小荔枝。非洲人是喜歡吃昆蟲的,不知是什麼蛹,小拇指大小,像我們的蠶蛹,珍藏著,客人來了才八蠻獻寶樣拿出來,在鍋上“唰啦,唰啦”的炒炒,然後放在麵糊樣的湯裏煮,然後亦是用手把那蛹一隻一隻從麵糊裏拖出來吃。非洲人捕大蛇,簡直是奇特,一個人用布一層一層地把腳包了,包得很厚,然後,真是勇敢,把腳直伸到大蛇的穴裏去,當然有人在後邊死命拖他,拔河運動樣的。那大蛇,在穴裏居然憤怒了,一下子死死咬住那隻腳再不肯放開,人們就這樣把那條大蛇從洞穴裏拉出來,那大蛇怎麼會願意,百般扭動著,但它扭動的最終歸宿是進到了人的肚子裏。非洲人和我們畢竟不一樣,看過那麼多的片子,就是看不到非洲人在那裏讀書,非洲的家庭裏好像也不會有書,但一定有鼓,他們的生活是離不開鼓的,總是“嘭嘭嘭嘭”熱烈地敲著,女人的臀部會搖成那樣,好像不準備要那臀部了,要擺脫掉它,但又擺脫不掉。男人的舞蹈簡直就是在那裏做性交的演示。這就是原始,並不以性為醜。我不知道黑人的盛宴都會有些什麼菜,蟲子嗎?一盤一盤美麗的蟲子?中國人是不吃蟲子的。我的父親,用蠶蛹下酒,我看著就不舒服,用毛蛋下酒,我看著就更不舒服。看來看去,不明白父親怎麼會這樣野蠻。
中國人的不可思議在外國人看來是吃飯的時候使用筷子,兩根細棍,魔術般夾得起小鴿子蛋。最細的發菜也會挾一絲起來,簡直是絕技。有用筷子在空中夾正在飛著的蒼蠅的,這幾乎近於魔道。我們家吃雞,內臟全部會扔掉,看人家在那裏細細地用一根細筷子一捅一捅地洗雞腸子我就很難過。內蒙那邊吃羊,洗腸子不用水,割一塊羊肺子,硬塞到羊腸子裏邊去,就那麼一捋一捋,腸子就幹淨了,真是好辦法。四川人整治豬頭,會把豬頭擺弄成一隻大蝴蝶,人們就叫它蝴蝶豬頭,半風幹的,紅光光的,燈光可以從那邊照過來,可以做壁上裝飾,眼神不好的人還會以為是一隻風箏。這豬頭並不怎麼好吃,切了上籠蒸,是臘肉的一路。肥的部位呢,像琥珀。西藏的牛肉幹,一條一條的,咬起來卻十分的酥香,簡直讓人意想不到,是越嚼越香,怎麼會?西藏康巴漢子好像都有一口白厲厲的牙齒,好像是為了強調他們的牙齒,他們把黃金派上用場,鑲一兩顆金牙給人們看。笑起來,就分外的光輝燦爛。想一想他們圍在一起喝酒吃肉的光景,應該是金碧交錯。再加上綠鬆石幽幽的藍,珊瑚溫潤的紅,琥珀喜滋滋的黃。價值千萬的財寶都累累垂垂披掛在身上,這就是遊牧民族。雪山是白的,草原是綠的,這兩種大顏色中,多虧了金牙和珠寶讓人眼睛不單調。
川菜是應該一提的。酸甜苦辣之中,好像是,數辣沒有多少道理,但又讓人沒頭沒腦地喜歡它,讓人有自虐的傾向而且舒服。舒服的事有時就難免讓人出醜,鼻涕和眼淚是辣的副產品,一邊吃一邊擤鼻涕是吃川菜一大景觀。還有麻,小粒的川椒的顏色和形狀就像是荔枝縮小了幾十倍,把人會麻得“索索索索”直吐舌頭而四顧茫然。川菜好就好在要和人的腸胃起劇烈的衝突,就像燒刀子的汾酒,一入口,衝突便驟然而起。衝突有時亦是一種快感。而古越龍山的花雕則好在讓人渾然不覺,是一種陰謀,悄然進行著,神不知鬼不覺的樣子。和人是如魚得水的,妥妥貼貼的,一旦醉倒則是身心俱垮。喝酒其實就是為了那刺激,為了那衝突,酒像暴徒樣一下子入侵了,而腸胃呢,簡直就是開門揖盜,好像是在說:你進來,你進來,請你進來。量好的酒徒,就像是古時的好捕快,再多的強盜,一入他的窟竅便被一一招安。而酒量小的人,讓酒一窩蜂地進去,但很快就會馬上又出來,不但出來,金銀財寶也給擄掠了出來,那金銀財寶便是剛剛下肚的各色菜肴。川菜的品性實際上是野蠻的,風風火火的,是戲劇裏的武場,是鑼鼓的急急風,是一場有聲有色的戰爭。一盆油汪汪的水煮魚端上桌,你需要用筷子深入其中去拯救那魚,那盆裏全是紅光四射的辣椒,若不及時把那魚拯救出來,那魚便好像不會再是魚了。好了,麵對那紅汪汪的刺激,你有了洗桑拿的感覺了,那熱辣辣的感覺在你的全身曼延開了。也就是,你簡直就是被激怒了。這時候的酒倒像是變得溫和了,簡直是有幾分謙虛了。吃川菜,隻有滬州大曲才壓得住那陣腳。日本清酒,不行,紹興花雕,不行。汾酒照樣的不行,汾酒到了這時候是隻有刺激而聲勢不行,掛釉陶瓶的那種濃鬱的滬州大曲一上來,川菜的氣焰才會稍稍收斂,調和了,好像經過了談判。茅台當然更好,打開一瓶好茅台,那酒香便會一下子把川菜的氣焰打下去。川菜好在哪裏?好在和腸胃起衝突,川菜培養出一代一代的四川好漢子不是沒有道理的。麻婆豆腐好在哪裏?好就好在一點點硬性都沒有,豆腐其實就品性而言隻能是十五六歲尚未長成的小女兒,不可以再嫩。但麻婆豆腐的好處就在於軟性中掩藏著刻骨的鋒利,簡直就是刻骨,這道菜在那裏好像說:讓你再說我軟,你看看我軟不軟。這是以辣味做主帥的一道菜。川菜的氣勢原是鋪天蓋地,如和杭州菜相比,那簡直是白臉秀目的秀才遇到黑撿的胡子兵,有理說不清。怎麼說呢,杭州菜隻好在那裏和淡黃酒談情說愛卿卿我我,到後來,再滑溜溜地讓蓴菜湯把感情滑到不知何處。
中國人造字,真是妙得可以,“品”字是三個口,一道菜要吃出味道還真是非要吃到三口不行。或者那意思又是在申明一個人吃了還不算,要三個人一起吃吃才算。我們的一般吃飯,原是不能用品字的,隻是吃。民間的說法之一是喂腦袋。這是素描式孩子的說法,僅停留在觀感上。看一個人在那裏埋頭吃飯,那飯果真是給喂到腦袋裏去了。
有一種梨,軟得不能再軟,還有一種蘋果,怎麼也可以那樣沒有筋骨,綿軟得毫無道理。我都不愛吃,我愛吃有嚼頭的。從我家往西,華嚴寺門口有一家烙燒餅的,現在卻不見了,這一家的燒餅烙得真好,黃黃的,皮殼是脆脆的。我常去那裏吃,現買現吃,如果放在塑料袋子裏拿回去吃,那燒餅給熱氣一捂就不好吃了。我常在烙餅的爐子邊吃燒餅,熟人見了輒以為怪。說,燒餅有什麼好吃的?我就告訴他,品味吃,有時候不能單單品味味道,比如酥和脆,是給牙齒的安慰。比如筋道,也是讓牙齒來享受的,亦是快事。海蜇皮,有什麼味道?可以說沒什麼味道,隻是給牙齒帶來些快感,脆脆的,好像是在施虐,海蜇絲拌白菜絲是一道下酒好菜,但海蜇絲一定要用開水燙一下才好,眼下飯店為了給眼睛好看,卻在那裏欺騙人們的牙齒。滿滿的一盤,用水發過了頭,比粉條都軟弱無力。還比如臭,世界上,嗜臭的民族並不僅僅隻有中國,榴蓮臭不臭,但遠遠比不過臭豆腐,臭豆腐之妙全在於簡直就可以與某種東西做嫡親的兄弟。但好吃,吃臭豆腐的時候,心理上微妙的變化亦是一種享受,比如,有那麼一點鬼鬼祟祟,有那麼一點對不起別人的感覺,如果全家人一齊上陣大幹,便會在心裏產生一種集體墮落的快感。
總結吃,總是這四個字:甜酸苦辣。隻不過是一種粗疏的概括。
說到品味,我相信是可以寫一篇世間最大的文章,我們往往隻談怎麼吃,怎麼品味,很少有人談吃不到飯挨餓的滋味。倒很想讀到這樣一篇文章,題目不妨就叫做《品味挨餓》。現在許多的少女甘願挨餓是為了減肥,生活好起來,肥胖的人漸漸增多好像並不是一件好事,人畢竟不是雞鴨,要那麼肥做什麼?沈從文先生說看到一個很胖的女人從路那邊走過來讓人心裏很難過,如果看到很多呢?一個一個肥胖地過來過去,而且是絡繹不絕,那非但是讓愛美的眼睛難受,我想男性公民的情緒也會因此而大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