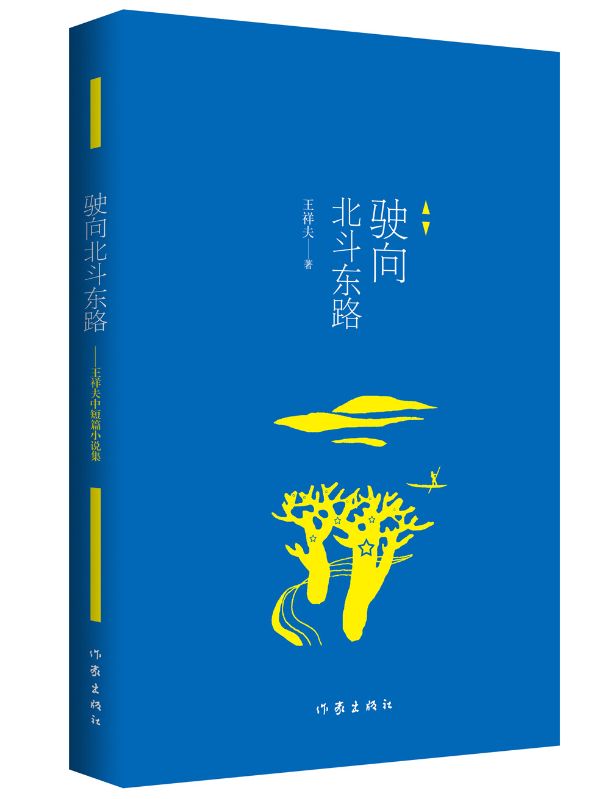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十一章
澡堂就不是遊泳的地方
其實這件事就該怨老趙,但現在無論是誰,都無法再埋怨老趙了,人們往那輛白色救護車上抬老趙的時候老趙已經不行了,人們都知道那輛救護車完全是為了例行公事。出了那樣的事,是沒法不讓人們知道的。從那以後,小萊就總是問胡兵他們那天在澡堂裏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三個多月過去了,這一直是胡兵和小萊之間爭吵的話題,雖然他們的爭吵沒那麼厲害,雖然胡兵對小萊解釋過不知道有多少遍,這連他自己都煩了,怎麼說呢,他們當時確確實實是在洗澡,大家先是在一個熱水池子裏泡了一會兒,然後就到了旁邊的溫水池,當時老趙拍拍身子說他想在池子裏遊一下,一邊說一邊就馬上大張著嘴仰遊了起來,從這邊遊到那邊,也隻不過是揮幾下胳膊,人們接著就看見他往水底下沉,都還以為他是在玩兒什麼新鮮花樣,過了一會兒,大家才知道是出事了。
“就這麼回事!”胡兵對小萊說,“我們根本就沒做別的什麼事!”
那天洗澡馬東也在,胡兵說馬東可以為自己做證,馬東既是小萊的同學,又是胡兵和小萊的婚姻介紹人。其實小萊從一開始就比較相信胡兵的話,但他們之間的問題並不出在這裏。小萊對胡兵說也許是自己腦子裏有什麼事了,總是在想入非非,但她又不能不讓自己想,小萊說這不是她的錯,說來說去澡堂根本就不是可以讓人們遊泳的地方,全世界可能沒多少人會相信澡堂可以遊泳,誰在澡堂遊泳?
那一陣子,胡兵和小萊很想要孩子,為此胡兵還戒了酒,即使和朋友出去,也隻喝一點點,然後就坐在一邊看別人喝。出事後的那天下午,胡兵抱了好大一紙袋子綠皮荔枝興衝衝從外邊回來,倒好像他真做了什麼不好的事。他和小萊上了南邊的陽台,從陽台上可以看到對麵樓頂上落了一隻布穀,孤孤零零的就那麼一隻,在那裏叫叫停停,布穀不叫的時候簡直就像是隻鴿子,隻有在它啼叫的時候人們才會明白它原來是隻布穀。
胡兵給小萊剝了荔枝,剝好的荔枝一顆一顆很像水晶球,胡兵把它們都放在一個白瓷盤子裏,但很快他發現小萊隻吃她自己剝的。到後來,胡兵隻好自己把自己剝好的荔枝全部吃掉,他邊吃邊把荔枝核兒吐到陽台下邊去,“啪、啪、”的聲音從下邊傳上來,下邊是樓下那家人家的遮陽篷。到了這天晚上,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從結婚以來胡兵和他小萊幾乎是夜夜都要來那麼一下,但胡兵那天晚上沒辦法進入,小萊不但不配合而且還把自己夾得緊緊的,到後來他隻好從小萊身上下來。
“我跟你說我什麼也沒做。”胡兵憤憤地說。
胡兵去衛生間待了一會兒,上床的時候又對小萊說,“我什麼也沒做!”
從結婚以來胡兵和小萊一直都是相擁而睡,但從那天開始他小萊不再跟他抱在一起睡,而且很怕胡兵進入,包括胡兵的手。那天,小萊突然問胡兵,“澡堂裏怎麼就會把一個人淹死?”胡兵的兩隻眼馬上離開了電視,看著小萊,說,這事不是已經很清楚了,怎麼還要問?是老趙自己的心臟病要了他自己的命,小萊看著胡兵,說洗澡不會給一個人的心臟增加太多的負擔吧?胡兵說問題是老趙要在水裏瞎撲騰,其實那種瞎撲騰挺費勁。小萊看著另一邊,那邊有什麼東西亮晶晶的,是那把咖啡壺,胡兵那幾天特別勤快,把家裏的東西都擦拭得很亮,幾乎把所有的東西都擦拭了一遍。
胡兵把手又朝小萊伸了過去,小萊把身子往旁邊扭了一下。
“告訴你我們什麼都沒做!”胡兵跳起來大聲說,又說,要是做,自己也會戴個套兒。胡兵馬上就覺得自己這話說錯了。
胡兵明白自己的生活進入了一個說不清的階段,他察覺小萊厭惡自己的身體,晚上睡覺的時候,隻要翻身靠近小萊一點,小萊就會把身子馬上躲開。
胡兵對小萊不止一次大聲說:“跟你說我沒做就是沒做!”
小萊說自己也不想這樣,但一想那件事自己就不行了,澡堂根本就不是遊泳的地方!
胡兵有晚上吸煙的習慣,他問小萊:“是什麼樣的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小萊說。
胡兵把一條腿蹺了起來,“試一下?”
小萊都已經把身體慢慢打開了,但馬上又蜷做一團,說自己真是不行,一想到澡堂根本就不是遊泳的地方就不行了。
“你怎麼總往那邊想?”胡兵說你這是不是潔癖!
小萊說這不是潔癖不潔癖的事!自己也很想讓自己相信他什麼也沒做。
胡兵無話可說,他把手裏的煙拿遠了,煙在暗處一閃一閃,他想自己是不是應該強行來那麼一次,說什麼也不能再這麼下去了,都三個多月了,也許強行來那麼一次一切就都過去了,他實在是太想進入,從他還沒結婚的時候他就那麼進入慣了,那已經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吃飯。但他現在隻能是想想,抽完了那根煙,他又躺下,他的右胳膊讓床微微有點顫。
胡兵知道小萊還沒睡,就對小萊說:“最討厭的就是人們都以為一到了澡堂就要做那種事!”胡兵停停又說:“最討厭的就是人們都喜歡對這種事添油加醋!”
“澡堂總不是遊泳的地方吧?”小萊說。
胡兵希望這件事很快有個結束,但他好像看不到結束的跡象。
但事情終於好像有轉機了,馬東這天給胡兵出了個主意,馬東說,“這種事暫時換一下環境最好,這種事隻要兩口子做一下就順過來了,不少人都碰到過這種事。”
馬東說話的時候胡兵的兩眼正看著另一邊,那邊一個很漂亮的小姐正在做頭發,給她做頭發的是個挺瘦的小夥子,他正用夾板一樣的東西一下一下往直了拉那位小姐的頭發,嘴裏還咬了兩隻綠塑料發卡,小姐的頭發很長,給染成了淺棕色。胡兵和馬東都知道這是個小姐,他們一眼就看出她是個小姐,因為胡兵和馬東剛剛洗完澡,他們這時正坐在大廳的玻璃茶幾旁邊喝茶。這時候忽然從外邊進來了五六個高中生模樣的年輕人,長得是一個比一個帥。這幾天天氣是忽然一下子就熱了起來,這五六個高中生都穿著漂亮的體恤,他們去換鞋的時候又有兩個小姐從裏邊走了出來,是快到吃中午飯的時候了,她們大概是要去吃午飯,那五六個學生馬上都盯著這兩個小姐看,有一個學生還跟著往外走,出了門,看了一下,又回來,手很快抓了一下褲子那地方。那幾個學生馬上都嘻嘻哈哈起來。
胡兵和馬東不知道他們在嘻嘻哈哈什麼。
“帳篷!”胡兵和馬東都聽見那幾個學生說。
馬東對胡兵說,“別看他們的歲數,也許連一個處男都不會有。”
胡兵說,“我沒結婚的時候也已經不是了。”
馬東看了一下胡兵,“那不太一樣,你那會兒都工作了。”
胡兵說自己現在和處男差不多少。
“所以明天你一定去。”馬東說自己馬上就可以聯係好,那邊的朋友說了好幾次了想讓自己去,“咱們可以先去看一下教堂,那個小教堂據說在地圖上都查得到,除此,一路還能看看桃花,桃花這種花總是開在杏花的後邊,或者就是李花,明天就在那地方住一晚上,後天再回來。”
馬東對胡兵說到時候就看你的了,“女人隻要環境不同心情馬上就會好起來。”
茶水有股子怪味兒,他們又喝了一會兒。一直到那個小姐做完了頭發。
馬東理發的時候胡兵就坐在那裏翻一本印得很漂亮的發型雜誌,上邊的女人都不像是真的,因為她們都實在是太漂亮了。
胡兵翻雜誌的時候聽馬東問了那個理發的小夥子一句:
“是不是剛才那小姐用過的梳子?”
理發的小夥子停了一下,沒說什麼。
“馬上給我換一把!”馬東大聲說。
這天早晨,胡兵和小萊都起得很早,也許是太早了,他們都不太想吃早飯,最近他們連一點點食欲都沒有。小萊在廚房裏“嘩嘩嘩嘩”洗什麼?胡兵過去看了一下,是一大堆小萊準備帶出去給大家吃的西紅柿,胡兵用手捏了其中的一個,說西紅柿對男人的前列腺好。小萊沒跟上說什麼前列腺。洗完西紅柿,她對著一進門的那麵鏡子去試衣服,一進門那兩把椅子上馬上是一大堆衣服。
小萊發現要穿的絲襪上破了一個很小的洞,胡兵正好點了一支煙在那裏抽。
胡兵說小心點兒,別反而燙一個大窟窿。胡兵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上陽台看看那隻布穀還在不在,那隻布穀幾乎是叫了一夜。
“那隻布穀在求偶。”胡兵對小萊說。
“什麼?”小萊用三個手指撐著襪子,另一隻手拿著胡兵的煙頭兒。
“布穀鳥根本就和種地沒關係,它那麼叫是因為它在發情。”胡兵又說。
小萊把襪子弄好了,她總是那麼弄,用煙頭。
“不過它也許是白發情,如果這一帶沒有第二隻布穀。”胡兵又說。
小萊挑好了衣服,她把一大堆衣服又抱了回去。有什麼掉了下來,“啪”的一聲,聽聲音像是扣子,滾了一下。
八點的時候,車來了,是兩輛小車,胡兵和小萊比較喜歡那輛紅的,馬東和胡兵悄悄開了一個玩笑,說你和小萊坐在後邊做什麼都行,我裝著看不見。胡兵沒說什麼,因為這時候他小萊已經走了過來。胡兵沒在車上做過,他打量後邊的車座兒。
小萊說你看什麼,挺幹淨的。
胡兵說沒看什麼,是挺幹淨。
“有些車就臟得不行。”小萊說。
胡兵說,“對,臟得都讓人沒法坐。”
因為修路,胡兵他們先開著車子繞了一下,先朝南上了四環然後再朝北,那個小鎮子在城市的北邊。兩輛車開去開來到了那個小鎮已經過了中午了,中間他們還停下車吃了西紅柿,西紅柿好像一下子變得很好吃,人人都搶著吃。這八個人裏邊包括胡兵和他小萊,還有馬東和他的媳婦,還有小喬,老高和李建,李建帶了一個姑娘,人們都知道李建已經結了婚,李建和那個姑娘一說話,大家馬上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但這種事現在不算什麼。
“他們是同事。”胡兵對小萊說。
小萊說,“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胡兵說。
小萊看著胡兵。
兩輛車開到地方已經過了吃中午飯的時候,中午這頓飯真是很豐盛,菜上了很多,吃都吃不了,酒有兩種,低度白酒和葡萄酒。小萊發現胡兵也喝了一些白的。胡兵很長時間已經不喝酒了,胡兵喝酒的時候看了小萊一眼。小萊沒說話。
吃飯中間,人們還站起來出去看了一回飯店後院的火雞,因為它們的叫聲實在是太與眾不同了,讓人耳朵發麻,人們都沒見過火雞,火雞根本就不是這地方的雞,所以他們都出去看了一下。胡兵和小萊都想不到火雞會有那麼大,雞冠的顏色居然會變,一會兒發紫,一會兒發藍,一會兒拉長,一會縮短,滑稽得很。那隻總是讓翅膀發出“沙沙沙沙、沙沙沙沙”聲響的雄性火雞一直火氣十足,不停地追逐另一隻母火雞,當它終於跳到另一隻母火雞的身上時,胡兵忍不住握了一下自己小萊的手,那隻雄火雞在母火雞身上使勁的時候,翅膀再次“沙沙沙沙、沙沙沙沙”,胡兵又用力握了一下自己小萊的手。
“火雞挺有意思。”吃完飯上車,胡兵對馬東說。
“吐綬雞。”馬東說。
胡兵說火雞居然把翅膀搞得那麼響。
“翅膀?”馬東說。
“不那麼‘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動翅膀它根本就使不上勁。”胡兵說。
馬東聽懂了,笑了一下。
“沙沙沙沙!”胡兵說。
“那是它們的語言!”馬東說。
“要是人這樣就好了。”胡兵說到時候每個男人背後都長兩隻翅膀。
“到什麼時候?“馬東笑著說。
“還能到什麼時候?反正不是飛翔的時候!”胡兵說。
胡兵這麼一說小萊也笑了,她好長時間都沒笑過了,她在一個電影裏看到過這種畫麵,好像是一部美國電影,那裏邊的男主人公就長了一對翅膀,並且能把翅膀收得緊緊的,外邊還要穿衣服,但那部電影不怎麼好看,隻不過是好玩兒而已。
這時候胡兵想起了胡子,早晨他忘了這事,他知道馬東車上有。
胡兵一邊用手摸一邊刮,馬東點了一支煙,他從倒車鏡裏看胡兵,胡兵一邊的腮幫子鼓著,臉像是有些變形。馬東忽然對小萊說起聚會的事,說下個月也許同學們要來一個聚會,說話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從車裏看到了那個教堂,教堂在很高的地方,遠遠就能讓人看到,胡兵把車窗玻璃搖了下來,車窗玻璃一搖下來,草的味道就全進來了。
上坡的時候,胡兵一直拉著他小萊。那小教堂是磚砌的,現在隻剩下一個高高的鐘樓,上邊有許多鴿子拉的糞,太多了,白花花的都有些晃眼。
胡兵問小萊,要不要去那邊方便一下?胡兵把手裏的那罐啤酒打開了。
“砰——!”
到了農場的時候,天都快黑了。讓胡兵和小萊想不到的是那個農場居然在山裏。他們的車在山上迷了一會兒路,隻迷了一會兒,然後就有人開著車過來給他們帶路,這樣一來,是三輛車在山間的路上飛跑。坐在車裏的胡兵和小萊很快就又看到了水,是山間的一條白亮亮的小溪,很窄的那麼一道,然後又看到了攔在下邊兩山之間的那個壩,嚴格說那隻能說是一堵很高的水泥牆。這時候,小萊又看到了牛,四五頭奶牛,那種黑白花的奶牛,正在那裏不知道吃著什麼。馬上,房子也出現了,小溪這邊兩排,小溪對麵又有兩排,都是紅磚砌的,所以顯得很鮮亮。這時候,天已經暗了下去。接下來的那頓飯吃得並不怎麼好,因為農場這邊根本就沒做什麼準備,他們也許想根本就不會有人說來就來,誰肯來這種地方?來這種地方做什麼?也沒什麼好吃的東西,也沒什麼好看的東西,而且到處都充滿了牛糞的騷臭,遍地是牛屎,一般人說要來這地方也都是裝裝樣子,根本就不會來。而一旦真有人來了,農場這邊就會慌了手腳,不知道該給客人吃什麼?
胡兵和小萊看到了那條狗,那條沒見過這麼多的人的狗此刻正被嚇得渾身發抖。
“你看它抖得有多麼厲害。”胡兵對小萊說。
“你說它敢不敢咬人?”小萊說。
胡兵一靠近那條狗,那條狗就齜出牙來,狗鼻子皺成一團。
這時候小萊身後的那個很高大的女人正在彎腰熱一鍋很稠的牛奶,熱牛奶的鍋放在一個四四方方的灶上,小萊小聲對胡兵說:“我可不喝這種奶。”胡兵回頭也看了一下那鍋冒著熱氣的牛奶,覺得自己也不可能喝,胡兵覺得那鍋牛奶真不怎麼樣,奶上邊厚厚的一層不知道是什麼?顏色有些不對頭。
胡兵和小萊看那鍋牛奶的時候,馬東從那間屋裏出來朝胡兵和小萊招手,要他倆進去吃西瓜。“瓜已經切好了。”
進那間屋的時候,胡兵被地上那一盆血乎乎的東西給嚇了一跳,而且那一盆東西也太難聞了,又腥又臭。小萊也聞到了,但她沒看到,胡兵有意用身子擋住她的視線。胡兵馬上就斷定了那是一盆牛的內臟,他又看了一眼,盆裏是一大堆肺子,還有氣管兒,氣管的顏色要淡一些,盆子裏相信可能還會有牛肝和牛心。
馬東的朋友叫李新,是個漂亮小夥子,戴著眼鏡,襯衫很白,是他開著車把馬東他們接到農場的。後來胡兵和小萊才知道李新在區上工作,他是特意從區上跑回來接待馬東他們。他告訴小萊那鍋牛奶的事,說那鍋牛奶是用來喂小牛的,這個農場的主要項目就是讓奶牛生小牛,不停地生,不停地賣,因為離市裏太遠,這裏的牛奶從來都不往外邊賣。這時候有人抱了許多枯樹枝堆在了院子裏,並且馬上就點著了,火一下衝起很高。
胡兵不知道點火幹什麼?小萊也不知道。人們都跑過去看火。
點火的那個人這時又端了一大盆子土豆過來,那是滿滿一大盆子土豆,胡兵忽然明白可能是要吃烤土豆,便對小萊說了一句:“烤土豆挺好吃。”後來和胡兵一道來的那些人就圍著火看烤土豆,直到小萊驚叫起來。
其實小萊驚叫的時候馬東他們都已經看到了房子正前方坡下邊的牛骨骸,整隻牛的骨骸真是有些怕人,還有牛頭骨,牛角還在上邊,都堆在坡下邊,而且不止一隻,牛的骨骸上邊還殘留著一些幹了的皮肉。胡兵跟著小萊過去,馬上也都看到了,胡兵奇怪農場這邊的人怎麼不吃牛肉?怎麼會把整隻整隻的死牛扔在這裏讓它慢慢爛掉?這可能是冬天的事,要是在夏天,可能誰也受不了牛肉腐爛的臭氣。小萊再次驚叫的時候胡兵把小萊摟了起來。胡兵和小萊互相看了一下,胡兵說他也從來都沒見過整隻死牛就扔在那裏讓它慢慢腐爛。
“這時候回去不行了吧?”小萊小聲說。
胡兵說可能不行了,都是山路,天眼看就要黑了。
“住一晚再回,說好了的。”馬東在一邊說。
小萊看著胡兵,想讓他說句話。
“別,要不就白來了。”胡兵小聲說。
在天快要黑下來的時候胡兵跟著馬東去看了另一頭死牛,那頭死牛放在坡的另一邊,像是剛剛死了沒多長時間,牛皮已經被剝掉了,牛肚子裏的內臟也已經被掏空了,但牛身上的肉卻一點點都沒動,這頭被剝了皮的死牛就四腳朝天硬邦邦地躺在那裏,看樣子真是挺硬。讓胡兵吃驚的是那條狗,太讓人想象不到了,那條狗居然被拴在死牛的身上,一根鏈子決定了它和牛之間的關係,它被拴在牛的脖子上,它想走也走不開,看樣子它很無奈,一動不動趴在那裏,就趴在死牛跟前。看樣子狗的主人是想讓這條狗把這頭牛給吃了,到時候吃不吃它都得吃,死牛就是它的一日三餐。胡兵忽然覺得那條狗真是可憐,被拴在比它大十多倍的死牛身上,被剝掉皮的死牛真是怕人。
“別對小萊說。”胡兵對馬東說。
馬東說你最好帶小萊來看看,她一害怕就會鑽到你懷裏,到時候你推她都推不開。
胡兵說自己快要窒息了,想吐都吐不出來了,“雖然還沒有吃什麼東西。”
開始吃飯的時候,那一盆牛雜碎給端上來的時候胡兵終於忍不住吐了起來,桌上的人目瞪口呆地都看著胡兵。李新說不吃東西空肚子喝酒就是容易吐,吃點牛雜碎就好了,“這牛雜碎挺香。”
李新這麼一說胡兵就吐得更厲害。
“胡兵。”小萊說。
“我沒事。”胡兵說。
牛奶最後給端上來的時候胡兵又吐了一回,把剛剛吃下去的那點兒東西全都給吐了出來。
“胡兵。”小萊一邊給胡兵捶背一邊又叫了一聲胡兵,聲音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我得馬上回去。”胡兵說。
小萊看著胡兵,她覺得胡兵是把自己想說的話說了出來。
胡兵說,“可能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了,也許該去一下醫院。”
胡兵這麼一說,不想回的人也不好再反對,再說,他們也都不太想在這種地方待下去。
“我得馬上回。”胡兵又說,說自己實在是太難受了。
“太難受了!”胡兵說。
胡兵和小萊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小萊先去廚房想給胡兵做點吃的,小萊對胡兵說吃點東西壓壓可能會好一點兒。胡兵說還有沒有西紅柿?有西紅柿就行。小萊看著胡兵,說你從來都沒這樣吐過,“我從來都沒看你吐過。”
胡兵說反正現在也不在那個鬼地方了,告訴你也無妨。
小萊坐下來,把盤子端給胡兵,要他一邊吃西紅柿一邊說。
“那麼大的一頭牛。”胡兵說。
小萊說奶牛都那麼大。
“那是頭死牛。”胡兵說想不到農場的人不吃牛肉,他們隻要牛皮。
小萊說你是不是說那些死牛的骨骸。
胡兵說他說的是另一頭剛剛死的牛,被放在坡的另一邊,像是剛剛給剝了皮,紅彤彤的。
“我怎麼沒看到。”小萊說。
“因為在坡的另一邊。”胡兵說你要是看了也許比我還要吐得厲害。胡兵說馬東也看到了,可憐的不是那條被剝了皮的牛,最讓人可憐的是那條狗。小萊說是不是咱們看到的那條?胡兵說不是那條,是另外一條,那地方的狗我想不止一兩條。
胡兵說你想也想不到那條狗給拴在什麼地方?
小萊想知道胡兵說的那條狗給拴在什麼地方。
胡兵說那條剛剛給剝了皮的牛就四腳朝天躺在坡那邊,那條狗就給拴在死牛的身上!問題不在於它什麼時候想吃就可以吃一口,問題在於是它不想吃也得待在那裏,和那條又腥又臭的死牛待在一起,一直到那頭牛腐爛,也許那頭牛腐爛了它都離不開,它都要給拴在那裏。胡兵比劃了一下:“牛那麼大,狗這麼大,讓一條活狗和一頭死牛待在一起,讓一條活狗吃一頭死牛!”
“狗給拴在剝了皮的死牛身上?”小萊有些不相信。
“用一根鏈子,就拴在死牛脖子這地方。”胡兵說。
“它跑不開?”小萊說。
“它下輩子也跑不開。”胡兵說。
小萊站了起來,她覺得真是有點惡心。
“你聞見沒?”胡兵忽然說。
“什麼?”小萊看著胡兵。
“臭味兒。”胡兵說。
胡兵這麼一說小萊也像是聞到了一股難聞的味道,好像是那種他們已經熟悉了的臭味,是農場的臭味兒。接下來,是胡兵和小萊在屋子裏用鼻子尋找臭味是從什麼地方散發出來的,但他們找不到,接下來的事情是他們開始洗澡。胡兵說可能臭味就在咱們身上,胡兵這麼一說,胡兵就和小萊互相聞了聞,但他們還是弄不清臭味兒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咱們得好好兒洗一洗。”胡兵說。
胡兵和小萊的衛生間裏隻有一個噴頭,他們的熱水器已經用了近十年,胡兵總是擔心它會跑電,所以洗澡的時候總是先要把電斷掉。他們很少在一起洗澡,主要是沒機會,說得準確一點是沒時間。站在水龍頭下邊,胡兵說你聞聞我的頭發是不是很臭?小萊說要是頭發會染上臭味兒,那我要比你臭十倍。兩隻手洗頭發的時候,胡兵發現自己下邊有動靜了,他把身子側了一下,這麼一來他就站在了小萊的身後。
小萊馬上感覺到了,她有點兒緊張。
“你要是再吐了怎麼辦?”小萊說。
胡兵說不會,這時他已經把頭上的泡沫兒都衝幹淨了,他覺得小萊這一次也許可以了。胡兵要小萊把身子朝前彎下去,胡兵能看見水花在小萊的背上變成一道道水流。胡兵用一隻手幫著自己尋找的時候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了,他想好好兒享受一下這次進入,而就在這時小萊忽然掙了一下,把身子一下子蹲了下去。
“你到底想什麼!”胡兵說,一下子就暴怒起來。
“你們到底在澡堂做什麼?”小萊緊緊抱著自己。
“你比那頭牛還要臭!”胡兵說。
胡兵從衛生間一下子跳出去,胡兵光著身子去廚房給自己倒了杯茶,他讓燈開著,他根本就不會再想有沒有人在對麵看,然後又光著身子坐在廳子裏的沙發上,時間已經很晚了,胡兵要自己別開電視,胡兵要自己就那麼坐著,那杯茶水涼了之後他又給自己重新倒了一杯,這時候他的耳朵開始傾聽屋裏小萊的動靜。
小萊那邊終於有動靜了,她輕輕地走了過來,站在胡兵後邊了,試探著把一隻手放在了胡兵的肩上。
“我跟你說我們什麼也沒做!”胡兵說。
這一次,小萊沒再說“澡堂不是遊泳的地方。”
“真沒做。”胡兵又說。
胡兵和小萊在床上躺了下來,這時候已經很晚了。胡兵抓緊了小萊的手腕,他想這一次進入之後就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他想這一次自己應該做得特別好,但他想不到這一次自己居然還是沒能進入,他找到地方了,那地方很潤滑,很好。但小萊忽然又猛地把身子蜷了起來。
小萊大哭著說:
“澡堂就不是遊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