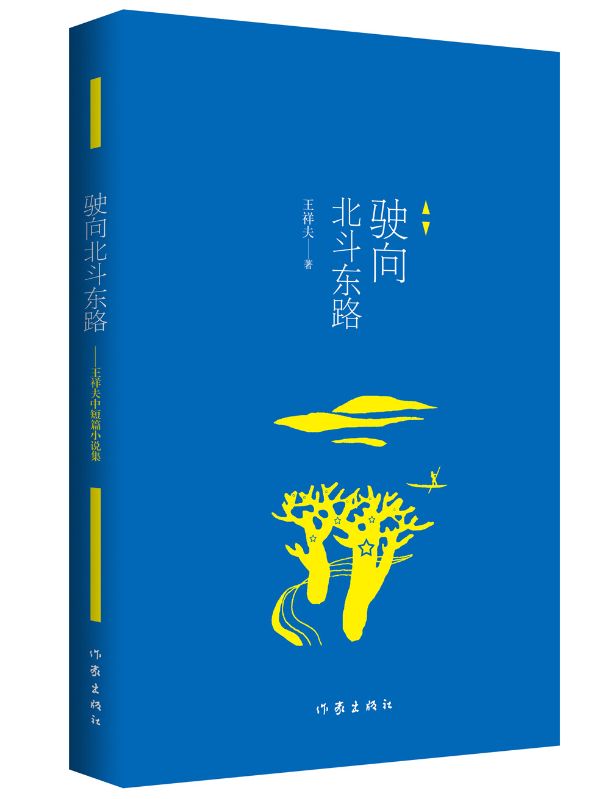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四章
真是心亂如麻
九年前年她就找到了這份兒不錯的工作,當時也真是湊巧,這家的主人急著要找一個像她這樣的保姆,因為他們馬上就要出國,全家都出去,去新西蘭定居。而他們的母親卻一時怕沒人照顧。她和這套房子的主人隻見了兩麵,就拖著她的全部家當來了,從那時候起,已經過去九年了,在這整整九年中,這套房子的主人一共才回來過三次。現在,她就像是這套房子的主人了,而這套屋子的主人也已經把一切都交給了她,包括幾乎是所有的鑰匙。他們給她的工資不能說低,每年會定期往過來寄兩次,還有老太太的工資,她每個月會替老太太去銀行取一次。這套房子的主人給她的工資是一個月兩千六,而且這套房子的主人還對她說過,說隻要是把他們的母親服侍好了,她的工資每年還會遞增一百,如果他們的母親還能再活一百歲的話,她的工資到時候就要增加一萬!好家夥!當然她知道誰也不可能活那麼大,即使是拚命讓自己活也不可能。她明白即使是自己,如果現在才十七八,也活不到那麼大,她現在不敢想這件事,她唯願這套房子主人的母親就這樣一直活下去,她甚至想最好是自己有一天忽然不行了而這套房子主人的母親還好好兒活著,她想過死,其實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想到過死。她覺著最好的死法就應該像樓下的那個老頭兒,上午還在院子裏大聲說話,用除草器修理草坪,到了晚上據說就不行了,正吃著飯,喝了一杯白酒,就一下子趴在了餐桌上。但她在心裏希望這套房子主人的母親一直活著,她活著她就有事做有地方住。她很早就是獨身一人了,丈夫早就去世,廠裏的鍋爐發生了大爆炸,她丈夫當時正站在鍋爐前邊,人一下子就沒了,隻有一條腿在牆上貼著。而她也沒有子女,所以,丈夫去世後她就一直住廠裏的公共宿舍。也正因為如此,這套房子的主人才一下子就選中了她。直到現在,她一直都很感謝這套房子的主人,那時候,她都發愁她那些有限的東西都放在什麼地方?東西雖然不多,但都是必需的,從工廠宿舍把那些東西一搬出來,她就慌了,好像是世界末日來了。也正是那時候,她被介紹到這家來做保姆。這家的房子挺大,是這座住宅樓最高端的一層,是複式二層,上邊那一層南北還各有一個挺大的漏台,隻不過南邊的比北邊的大一點。她來這家做事,也就是每天一起來就打掃衛生,先擦地板,然後再擦拭家具,然後是做飯,剛來的時候這家人還沒全走,讓她就住在樓上的一間靠近衛生間的小屋子裏,那間屋子的屋頂是傾斜的,動不動就碰頭,不過她現在早已習慣了。衛生間旁邊還有一間屋頂傾斜的小房間,裏邊掛著不少女主人的衣物,現在那些衣物都還掛在那裏,裙子大衣什麼的,用一幅白色的大窗簾苫著,還有許多鞋盒子。已經九年了,從沒人去動過這些東西,她進去過幾次,去看暖氣是不是夠熱,有一次她還拉打開一個鞋盒子,把裏邊的鞋取出來試了試,她這麼做的時候心裏“砰砰”亂跳,好像自己已經做了什麼壞事。這家的主人讓她住到樓上有他們的想法,樓上兩個漏台,他們怕那些修補房頂的工人晚上會偷偷從漏台溜進來,或者是別的什麼人,小偷也常常會爬到最高這一層來。這家主人考慮到這一點,就讓她住在了樓上。但現在她又住在了樓下,這套房子的主人一走,她就下來了,主人的母親非要讓她下來,她現在就住在這家主人母親旁邊的那間屋。但她自己帶過來的東西都還放在樓上。樓上那間屋裏有一張床,床上鋪著本來是用來鋪在地板上的那種很厚的紅色麻毯,麻毯被貓抓得亂糟糟的,那隻貓現在不在了,已經送了人。靠牆是一個書架,架上放著些沒用的課本,都是這家女兒上高中時候的課本,還有個小瓷爐,那種黑黑的,像個小亭子,打開蓋可以插香,還有兩盒盤香,那些盤香她想肯定連一點點味兒都不會有了,有一次她居然還點了一下,香冉冉升起來的時候,她的心裏又“砰砰”亂跳起來,好像自己已經又做了什麼壞事。她的一個舊皮箱,還是當年買的處理貨,但挺結實,還有一個塑料箱,粉色的,上邊的兩個小輪子早就不能動了,原來還可以拉上走,現在就放在書架旁邊的地上,還有一些別的什麼,都打了包放在書架上邊,苫著發了黃的報紙,那好幾大包東西她好久都沒打開過了,因為她從來都沒想到過再去別的什麼地方。九年的時間讓她覺得這裏就是她的家。春天的時候,她還在南邊的陽台上種了不少東西,用那種塑料盆,那種綠色的很大的塑料盆,當年不知道這家主人用這種盆子種什麼,她把盆裏幹枯的根子挖出來看了老半天,還是不能知道是什麼植物。她在這種盆子裏種西紅柿和青椒,她自己留的種子,把選好的西紅柿和青椒一直曬幹,再把種子取出來,到了春天直接種到盆裏,還有薄荷和紫蘇,老太太也經常跟著她在漏台上看她澆水,或者跟她一起曬曬太陽。北邊的陽台上還有七八盆花,都是紅色天竺葵,她經常一邁腳就過到那邊去澆花。冬天的時候她還會做臘肉,把帶皮五花肉買回來,用醬油和糖當然還有白酒醃那麼幾天,然後把它們拿到南邊的漏台掛在晾衣服的繩子上。老太太挺愛吃她醃的臘肉,隻是老太太的牙不好了,一小塊臘肉要嚼上老半天。誰知道老太太那口假牙都鑲了有多少年了,動不動就往下掉。吃飯或說話,老太太隻要把手往嘴邊一抬,她就知道老太太嘴裏的假牙又要掉下來了。
那天她對老太太說現在鑲牙很方便,不費事。
老太太正把勺子往嘴邊送,勺子裏有一點點米飯。“我還能活幾年?”
老太太的這句話讓她的心裏一時很煩亂,她站起身就去了廚房,心裏“怦怦”亂跳,她忘了自己到廚房要做什麼?水也沒有開。她在廚房裏站了好一會兒,她問自己,要是眼前這個老太太突然不在了,自己應該去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可以讓自己去?她被這個問題嚇了一跳。
可老太太現在確實是一下子就沒了,今天早上一起來她就覺著有什麼不對頭,屋子裏靜得有點不對勁,既沒有咳嗽聲,也沒有別的什麼聲音。她在廚房裏做好了牛奶麥片,心裏不知道怎麼就“砰砰”亂跳起來,她覺著是不是出什麼事了,她拿著一個玻璃杯去了老太太那間屋。床上的老太太頭歪向一邊,嘴微微張著,人一動不動,已經死很久了。
現在老太太就靜靜躺在她屋子裏的床上,就跟睡著了一樣。老太太的樣子並不讓她害怕,讓她想不明白的是老太太得了什麼病?怎麼會一下子就死了?從上午到現在她就一直呆坐在老太太屋子旁邊自己的屋子裏,就坐在窗邊的床沿上,從窗裏看出去,對麵樓頂的雪化得差不多了,春天快要來了,有人在對麵擦玻璃,人蹲在窗戶裏邊,一條胳膊伸在外邊。這說明外邊的天氣很好,但她的腦子卻是要多亂有多亂。窗台上的那兩盆天竺葵有點缺水,葉子蔫了。
這時又有人打來了電話,電話響了好一陣子,她希望這個電話不是從國外打過來的,一旦是國外打過來的,她不知道自己到時候該怎麼說,但打電話的又是那個女的,那女的在電話裏總是說什麼東西做好了,讓過去試試。她沒說什麼就又把電話放下了。她已經想好了,要是老太太的兒子或其他人打來電話,她就說老太太睡著了,一般來說,她一說老太太睡著了他們就不會再讓她把老太太叫醒,很長時間了,他們都不往過打電話了,他們都很放心,因為他們給老太太找了她這樣一個保姆,她想他們也應該放心,她想他們已經吃透了她,知道她希望老太太一直活下去,老太太隻要活著,她就有住的地方和吃的地方,還有工資,他們也知道她希望老太太活的歲數越大越好,到時候她每年還能長一百塊錢,所以他們一定都很放心。所以他們打過來的電話越來越少,更別說回來看看。
她坐在那裏,兩隻手的手指交叉著,兩眼一直看著窗外,對麵樓靠樓頂的地方雪化得差不多了,下邊靠屋簷的地方雪要多一些,那天對麵那家人樓頂的太陽能熱水器可能是壞了,水一直往下流,亮花花的,就那麼一直從樓頂流到了下邊的院子裏,再從院子裏流到院子外的路上去。這會兒,她看到了熱水器上落了一隻很大的鳥,黑色的,但她從來都叫不出鳥的名字,她其實很愛看有關動物的電視頻道,但老太太不愛看她也就算了,雖然樓上還有一台電視,就在一上樓的地方,電視前還放了一把很寬大的椅子,椅子旁是一排小書架,上邊塞滿了過時的課本和過時的雜誌,這台電視已經很久沒人看了,有兩次,她悄悄上樓打開了電視,找到了動物頻道,她這麼做的時候心裏又“砰砰”亂跳,又像是自己已經做了什麼壞事。
她坐在那裏,她不知道自己現在應該做些什麼?該不該往那邊打個電話?把老太太的死訊告訴他們。老太太此刻靜靜地躺在旁邊的屋子裏,如果沒人動她,她想必會就這樣一直躺下去。她聽見,有什麼又在“嗡嗡”地響,她一直不明白是什麼在響,她覺著是不是樓上衛生間的電淋浴器在響,她剛才上去了一趟,發現聲音不在那地方。這會兒她明白是自己的腦子裏在響,那響聲是她早上發現老太太死在床上時“嗡”的一聲響開的。她現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要不要往那邊打個電話?”她問自己。
這時候電話忽然又響了,把她嚇了一跳。
她用一隻手壓住自己的胸口。
“抽時間過來一趟。”電話裏的聲音像是特別遙遠,又是那個女的。
她沒說什麼就又把電話放下了,她實在是想不起這個打電話的女人會是誰?在這九年中,有時候會有電話打過來找老太太,都是當年和老太太一起教過書的老教員,她們也都老了,七老八十了,都上不了樓了,有的還在染頭發,但都染得馬馬虎虎,把白白的頭發根都露在外邊,老太太的同事們也都老了,能上樓也不想上,有時候老太太還會出去和那些七老八十的老頭兒老太太聚一下,也僅限於喝杯茶,在街心公園的那個小湖邊,茶座就在賣茶的那個小房子旁邊。老頭老太太一般都喜歡去那種地方。每逢聚會,老太太都會讓她攙著上樓下樓,每上一層都要歇上老半天,下樓的時候會好那麼一點,但也氣喘籲籲。
這時候電話又響了,她站起來,看著電話,好像一下子看到了電話那頭,很遠的地方,那個叫新西蘭的地方,感覺中是一大片綠的地方。她對自己說,如果是那邊的電話就說是老太太還在睡覺。
電話又是那個女人打過來的,她弄不明白這個女人會是誰?
是不是又要來一次聚會?她把電話放下來了。
電話放下來的時候她聽見那個女人在電話裏又說:“過來試一下就行。”
她動手收拾起自己的那些東西已經是下午的事,她把兩隻箱裏的東西都取了出來,離上次打開箱子取東西已經很長很長時間了。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收拾自己的東西。要是這家的老太太還活著一定會過來問她想做什麼。她把箱裏的東西取出來再放進去,東西忽然放不下了,好像是一下子多出了什麼。她從來都是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得有條有理,但現在一切都亂了。她沒有一點點主意,放在箱裏的舊衣服忽然怎麼也疊不好了,剛才她突然覺得自己是不是產生了錯覺,老太太是不是沒事?是不是還活著,就又輕手輕腳過去了一下,老太太還是那樣子,臉朝一邊歪著,嘴微微張著。要是沒人動她,她會一直這樣待下去。她站在那裏,彎著點腰,看著老太太,老太太的枕頭上繡著一朵很大的向日葵,黃黃的,她知道那枕頭不是老太太的,是老太太孫女上大學時用過的,她喜歡,就一直枕著它。她看著老太太那張臉,還有那被壓住一半的向日葵,她回過身,把五屜櫃上蒙在電風扇上的那塊白紗巾慢慢取了下來,白紗巾上沒一點點灰塵,挺幹淨,她就用這塊白紗巾把老太太的臉給蒙了起來。
接下來,她吃了一點點東西,就是早上給老太太做的麥片,她吃了一點,然後就上了樓。她忽然不想再待在樓下,過了一會兒她又下了一次樓,把老太太的那間屋門給關了起來。她希望這時候有電話打過來,最好是從那邊打過來,她想好了,隻要那邊這時候把電話打過來,她就會把老太太的死訊馬上告訴他們,他們也許會很快就從新西蘭那邊趕回來。但她也想好了,要是那邊不打電話過來,她也不會把電話打過去,雖然她知道那邊的電話號碼,但她不知道自己打過電話之後將會發生什麼事?但她可以肯定自己不會再繼續住在這裏,自己到時候要搬到什麼地方去住?或去什麼地方再重新找事做?她過去,扒在窗口朝外看了看,對麵樓頂白花花的。
她回頭又看了看自己這間屋的門,她走過去,輕輕把門關上。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三天過去了。到第四天的時候她不得不找了些膠帶紙把老太太那間屋的門縫封了起來,那種味道實在是太難聞了,但味道是封不住的,她隻好重新打開門把老太太屋子的那扇窗戶打開。老太太還那樣躺著,當然她隻能那樣躺著,如果沒人動她的話,她隻能一動不動臉上蒙著那塊白紗那樣躺著。她繞過床,踮著腳把窗子打開,又馬上踮著腳從這間屋子出去,然後又把老太太的門縫用膠帶紙封了一下,這樣一來味道小了一些,再說她也像是習慣了。在這四天裏,她又接到那個女的打來的電話,現在是,她隻要一聽到是那個女的就會把電話放下。這四天,她一次門都沒出過,也不見有人來敲門,整整九年了,上門的人除了收電費水費和煤氣費的她幾乎就沒見過別人。整整四天,她一直待在樓上,有時候會下來找點吃的,廚房裏有方便麵,還有點心,點心都放硬了,她看了看冰箱,裏邊有元宵,那種袋裝的,還有溫州人醃的那種雪白雪白的小蘿卜,這種小蘿卜原來是粉紅色的,一旦醃成白的,味道就酸酸的很好吃。老太太很喜歡吃這蘿卜,用一點點瘦肉切成丁兒,再把這種蘿卜也切成丁兒放在一起炒,是一道吃米飯的好菜。她總是把要拿的東西從冰箱裏一取出來就馬上急慌慌離開廚房,上樓的時候心裏又總是“砰砰”亂跳,好像做了什麼壞事。其實她現在沒什麼食欲,一點點都沒有。有時候她會下樓去廚房燒一壺水,水壺坐在煤氣灶上她往往會把這檔子事忘掉,當水壺猛地叫起來的時候她又會被嚇一大跳。
電話是第五天打過來的,從遙遠的新西蘭,打電話的是老太太的兒子。
接電話的時候,她的心“砰砰”亂跳,她用手按著那地方,到了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
“睡著了。”她說。
“那就讓她睡吧。”老太太的兒子在電話裏說咱們那邊下雪沒?
她朝外望了一下,對麵屋頂上的雪已經不見了。
“身體怎麼樣?”
她聽見自己在說:“很好。”
電話裏又說了話:“牙鑲得合適不合適?”
她的腦子忽然亮了一下,忽然想起那個女人無數次打過來的電話。
“怎麼樣?”
她忍不住“啊”了一聲。
電話裏老太太的兒子說老太太是該再鑲口牙了。
“謝謝你帶她出去鑲牙。”老太太的兒子又說。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又說,“身體挺好。”
“那台電視,樓上那台電視。”電話裏老太太的兒子說你可能和老太太看不到一塊兒去,你看樓上那台電視吧,各看各的。
老太太的兒子最後又說打電話就是想問問鑲牙的事,牙鑲得合適就好。又說,這邊看牙醫要花很多的錢。這時候她聽見電話裏有什麼叫了一聲,聲音很尖。是狗。她知道他們在那邊養了一條狗。她還看過那張狗的照片,黑的。
她對電話那邊老太太的兒子說:“身體挺好,放心吧。”
這麼說話的時候她的另一隻手用力按著自己胸口那地方,好像馬上就要透不過氣來了。
“它一點兒也不臟。”
她不知道電話裏這句話是對她說還是對站在那邊電話旁的人說,是在說狗還是說人。電話裏又有人說了句什麼,聲音很含糊。
這天她下樓去了一次,她徑直去了那家小鑲牙館,她想起來了,她把老太太那口亮晶晶的假牙取了回來。她對鑲牙館的那個女牙醫說老太太這幾天下不了樓,她會把假牙先拿回去讓她試試,有什麼不合適再拿回來。女牙醫說她們可以出診,“有時候給躺在床上不能動的老人鑲牙我們都出診。”從鑲牙館出來,她路過那家賣麵包的小鋪子,她喜歡吃那種最便宜的麵包,那種麵包總是十個連成一片地賣,有那麼點酸味兒。她買麵包的時候,賣麵包的年輕人正把一個麵包掰開讓另一個顧客聞,並且很生氣地說裏邊的果醬都是鮮貨!誰可能用過期的果醬做麵包!她看不清玻璃後麵賣麵包的那張憤怒的臉,玻璃的反光很厲害,她隻能在玻璃上看到自己,她就那麼看了一會兒自己。她算了一下,要是老太太和她一起吃這十個麵包,她們可能要連續吃五天,但現在隻有她自己。
從外邊回來,她踮著腳去了老太太那間屋,但她沒有進去,老太太的屋門還被膠帶紙封著,所以她現在聞不到任何味兒。她把那副假牙用一塊兒黃綢子包了包,那塊兒黃綢子是從禮品盒子裏取下來的,這會兒終於派上了用場。她把那副假牙仔細包好,然後把它輕輕放在了老太太那間屋的門口,遠遠看過去,是那麼黃黃的一小塊兒。很長時間,它就一直被放在那間屋的門口。從樓上下來去廚房的時候,她總會朝那邊看一眼,然後急急走開。她現在是吃在上邊住也在上邊,平時很少下來,下邊這一層除了廚房,地板上都已經蒙上了很厚的一層灰塵。
再有一次,已經快到秋天了,那邊又打來了電話。
“身體挺好,老太太和老同事們聚會去了。”
她的手抖個不停,胸口那地方又好像要透不過氣來了,她正想再說句什麼,那邊已經掛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