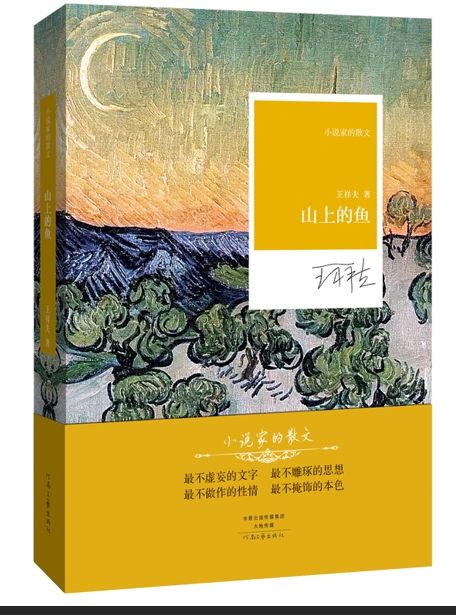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蓴菜之思
蓴菜真是沒什麼味,要是硬努了鼻子去聞,像是有那麼點清鮮之氣,你就是不聞它,而是在水塘邊站站,滿鼻子也就是那麼個味兒。蓴菜名氣之大,與西晉時期一位名叫張翰的人分不開,他寧肯不做官也要回去吃他的蓴菜和鱸魚,無形中給蓴菜做了最好的宣傳,這一宣傳就長達近兩千年。蓴菜是水生植物,隻要是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可能有蓴菜,沒有,你也可以種。但要論品質之好壞,據說太湖的蓴菜要比西湖的好。我隻吃過西湖的蓴菜,沒有比較,說不上好壞。蓴菜之好,我以為,不是給味覺準備的,而是給感覺準備的,這感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口感。蓴菜的特點是滑溜,滑滑溜溜,讓嘴巴覺得舒服,再配以好湯,難怪人們對蓴菜的印象頗不惡。滑溜的東西一般都像是比較嫩,沒等你怎麼咀嚼,它已經滑到了你的嗓子眼裏頭。蓴菜湯,首先是要有好湯,你若用一鍋寡白水煮蓴菜,你看看它還會不會好吃?蓴菜根本就不能跟竹筍這樣的東西相比。蓴菜要上席麵必須依賴好湯,它的嬌貴又有幾分像燕窩,沒好湯就會丟人現眼。蓴菜是時令性極強的東西,一過那個節令,葉子一旦老大,便不能再入饌,隻好去喂豬。常見蓴菜湯裏的蓴菜一片一片要比太平猴魁的葉子還大,這還有什麼吃頭!葉子上再掛了太多的澱粉,讓人更加不舒服,這樣的蓴菜湯我是看也不看,很怕壞了對蓴菜最初的印象。好的蓴菜根本就不需要抓澱粉,它本身就有,蓴菜的那點點妙趣就在那點點自身的黏滑之上。去飯店,要點就點蓴菜羹,湯跟羹是不一樣的。說到以蓴菜入饌,那還要數杭州菜為第一。
以蓴菜入饌,我以為也隻能做湯菜,如果非要和別的東西搭配,與魚肉搭配也可以,與雞片搭配也似乎能交代,但與豬肉羊肉甚至牛肉相配就沒聽說過。蓴菜好像是不能做炒菜,但也有,杭州菜裏就有一道“蓴菜炒豆腐”,但必要勾薄芡。一盤這樣的炒菜端上來,要緊著吃,一旦那點點薄芡澥開了,稀湯寡水連看相都沒了。這道菜實際上離湯也遠不到哪裏去,而這道菜裏的豆腐我以為最好用日本豆腐,日本豆腐比老豆腐老不到哪裏去,正好用來配蓴菜。
老北京醬菜中有一品是“醬銀苗”,現在可能已經沒有了,我去了幾次六必居,他們是聽都沒聽說過。汪曾祺先生對飲食一向比較留意,他曾經在談吃的文章中發過一問,問醬銀苗為何物。汪先生也沒吃過醬銀苗。我後來偶然翻到有關銀苗菜的資料,明人呂毖所著《明宮史》載:“六月初六日,皇史宬古今通集庫、鑾駕庫曬晾。吃過水麵。外象赴宣武門外洗。初伏、中伏、末伏日,亦吃過水麵,吃銀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我給汪先生寫了一信。
在北京的民間,現在還有沒有人吃“藕之新嫩秧”?我很想做一番調查,也很想再深入一下,調查一下,還有沒有用銀苗菜做醬菜的地方。想來醬銀苗也不難吃,首先是嫩,其次呢,我想還應該是一個字——嫩!醬菜一旦七七八八地醬到一起,都那個味兒。什麼味兒?醬菜味兒。我蠻喜歡北京的醬菜,都說保定的醬菜好,學生特意從保定帶一小簍送我,齁鹹!比我小時候吃過的鹹魚都鹹。說來好笑,我小時候總是吃鹹魚,那種很鹹很鹹的鹹魚,一段鹹魚下一頓飯!以至於我都錯以為凡海魚都是鹹的!——好笑不好笑?
保定的醬菜沒北京的醬菜好,北京的醬菜要以六必居為翹楚。我有一道拿手好菜,在各種的餐館裏都吃不到,就是“炒醬菜”,小肉丁兒,再加大量的嫩薑絲,主料就是六必居的八寶菜。這個菜實在是簡單,實在是不能算什麼菜式,但就是好吃,就米飯、佐酒都好。過年的時候我要給自己炒一個,好朋友來了我要給好朋友炒一個。但要是沒了六必居的醬菜,我就沒轍。
蓴菜可不可以像銀苗菜那樣做醬菜?俟日後到杭州細細一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