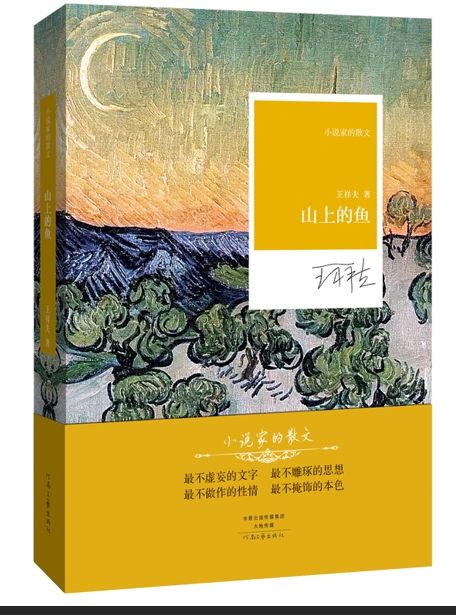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午時記
午睡前照例要找一本書隨便翻翻,順手便拿到了一本講琥珀的小冊子,沒有多少圖片,文字也清淺。說到琥珀,我父親大人年輕時喜歡用琥珀雕刻各種小動物。那是近半個世紀前的事情,而現在的撫順是既沒有多少煤可挖,也沒有多少琥珀可以拿出來示人。而我喜歡琥珀倒不是因為我是撫順元龍山的人,其緣由說來可笑,是因為從小吃那種魚肝油丸,一粒一粒黃且透明而又頗不難看。我之對於琥珀,是獨喜那種原始的,裏邊多多少少要有裂紋,古董家術語叫作“蒼蠅翅”的便是。前不久,把一大塊經常放在手裏的琥珀不小心一下子摔作兩半,一時悵惘了許久,忽然覺得那摔作兩半的琥珀用來做章料正好,這便想起“植蒲仙館”的主人誰堂來。誰堂不獨篆刻精彩,菖蒲也養得極好。說到菖蒲,起碼在北方是十分的難養。而文人的案頭照例是應該有些綠意才好,陳從周先生主張到處可以種一種的“書帶草”,聽名字就好,卻隻宜養在園林的階前砌下,案頭養一盆卻太顯蓬勃。那種叫文竹的草,日本人喜歡,川端康成的一張老照片就顯示他養了一小盆在書案上,遠遠看去確有幾分雲煙的意思,但一旦長起來其勢一發不可收,可以發展成藤蔓植物一樣在屋裏到處攀爬。而唯有那種金錢菖蒲和虎須菖蒲頂頂合適養在案頭,你想讓它蓬蓬勃勃起來,比如你想讓它長到大如車輪,那幾乎是沒有可能,它似乎永遠隻那碧綠的一窩。南國的畫家陳彥舟養的菖蒲卻分明太高大,放在茶桌邊,猛看像是種了水稻在那裏,卻也與那茶案相當,坐在其側喝茶,讓人起“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之思。是另一番意境。
讀書人的書案,我以為一是要有一點綠意來養眼,二是還要有一塊小小的供石,我以為這供石以靈璧為好,黑而亮或不黑而亮都好。我的嗜好是見了靈璧石就要買它一買,陸陸續續買了幾十品,而入眼養心的卻僅僅幾塊。其中一品小且玲瓏,恰像一炷香點燃後嫋嫋而起的那股煙,便名之為“一炷煙”。本可以取雅一點的名字,如“輕雲起”或“或如煙”,但我寧可要它有踏實的品性。還有一品山子,猛看一如宋人玩過大名鼎鼎的那個研山,我的這個山子上居然也有兩個小小的天池,儲水在裏邊可經旬不涸。我們這地方把天池叫作“那”,原是極為古老的一種叫法,比如寧武山上的天池,當地人便叫它“那”,而我給我這上邊有兩個小小天池的供石取名卻叫了“十二郎”,因為高高低低一共是十二峰。這名字讓人覺得它與我的關係是石兄石弟,而且有古意。就鄙人的興趣而言總覺得古意要比今意好一些。因為這十二郎的山子,我便給誰堂去信要了菖蒲,誰堂讓人用竹筒寄來,打開來不免讓人驚喜,郵路迢迢,居然還是一窩的綠。誰堂的養菖蒲在國內是出了名的,楣其館曰“植蒲仙館”,他的各種養盆裏,最好的是那方古磚琢成的盆。若有人問,喜歡菖蒲與供石,其趣味在哪裏?這不太好解答,就像你問熱愛法國紅酒的朋友紅酒的趣味在哪裏,相信他一定答不好。
六月是插荷花的時候,街市上沒有荷花賣,卻有蓮蓬,而一律又被掐掉了那長長的梗子,無法做瓶插。太嫩的蓮蓬其實也沒有什麼吃頭,一剝一股水。今年有個計劃,就是要去誰堂那裏看看他的菖蒲,再讀讀他的印譜。印譜原是讀的嗎?以我的經驗是大有讀頭,若讀得進去,小說又算什麼?
甲午夏至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