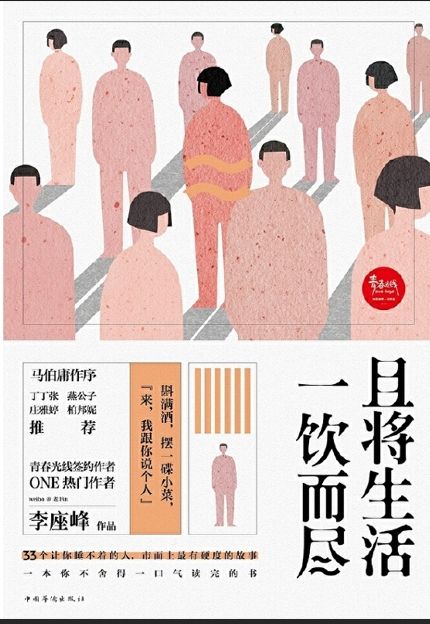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05 剃刀耿
小區附近的超市新開張的第二天,老耿在道邊兒擺了個剃頭攤子。
老耿滿腦袋鐵刷子毛兒一般的硬楂兒花白頭發,身高能有個一米七五六,黑褲子黑布鞋,上身穿著件零八年奧運會的文化衫,五個古靈精怪有些掉色的福娃兒在胸前一字排開。
支好二八大永久後,老耿把一麵臉盆大小的蛋圓鏡子掛到路邊兒的小樹上,然後拽下肩上的白毛巾在小折椅上撣了撣重新搭好,又打兜兒裏摸出盒點兒八的中南海,看了看往來的人群,敲出一根點上,抱著膀子有一口沒一口地抽了起來。
煙燒到三分之二處,一白得晃眼的平頭胖子挪過來。
“剃頭嗎?”
“剃!”老耿忙把煙掐滅,小心地塞回煙盒。
胖子低頭看著小折椅瞄了瞄準兒,轉身坐下,椅子被兩瓣兒大屁股裹得隻剩四條腿兒。
“剃光。”
“好嘞。”
老耿看了一眼胖子那沙皮狗一般滿是褶子的頭皮,從大永久車把上的布兜兒裏拿出一把折疊的剃刀打開,伸出左手按住胖子的腦袋,食指拇指兩邊兒一分繃起塊頭皮,右手捏著剃刀就要削。
“哎哎哎!”
胖子打鏡子裏瞧見老耿手裏的剃刀,一縮脖兒叫了起來,“師傅您沒推子啊?”
老耿搖搖頭:“使不慣那個。”
“手動的也沒有?”胖子使勁兒扭頭兒看著老耿,脖子上的皮肉都快擰成麻花兒了。
“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倒是用過一陣子,後來使不慣,就換剃刀了。”
胖子想了一下,倆胳膊支著膝蓋一較勁站了起來。
“得,您這家夥什兒我看著不踏實,我這腦袋皮鬆,回頭兒您再給我削一塊下去。”
胖子說著抬腿就要走,老耿急了,抓住胖子肩膀硬生生又給他摁回到椅子上。
“今兒我還非得讓你試試我這手藝不可!”
老耿這倔脾氣也上來了,摁住胖子不撒手。胖子掙巴了幾下,發現這瘦老頭兒還真有點兒幹巴勁兒,自己這麼大的塊頭兒,愣是起不了身。
“剃個頭多少錢啊,您這麼賣力氣?”胖子抹了一下鼻尖兒上的白毛兒汗。
“五塊。”
胖子又瞅了一眼鏡子裏腦後那把閃著寒光的剃刀:“那您可慢著點兒。”
“放心吧您就。”
老耿抻開一塊白布往胖子脖子上一圍,拿夾子夾住,一扳他腦袋,使勁兒舉了下右胳膊,把拘在肩膀上的文化衫扯開,三個指頭捏著剃刀輕描淡寫地在左手繃起來的頭皮上一掃而過。胖子脖頸一僵,再也不敢動彈,老老實實地任憑老耿在他腦袋上刷刷地剃。
“行了!”
老耿拿毛巾左右撣了撣胖子的脖子,隨後解下白布。
胖子舒展著筋骨站起來,對著鏡子一摸腦袋,樂了。
“喲,您這手藝可以啊!以前國營理發店的吧?”
老耿笑:“不是。別廢話,給錢。”
“脾氣不小啊老爺子!”胖子一手掏錢一手繼續摸著光頭。
“嗬嗬,不是我脾氣大,隻是我以前拾掇的那些位都是不愛說話的。”
老耿說著接過胖子遞過來的五塊錢往褲兜兒裏隨便一塞,又從另一邊兒的兜兒裏掏出那盒點兒八來,拽出那根沒抽完的煙點上。
很快,周圍幾個小區的老頭兒們都知道這超市附近有個隻使剃刀的理發師傅,甭管怎麼理,哪怕捎上刮臉也是五塊錢,紛紛跑來理發。
後來老頭兒們索性在老耿的理發攤子旁邊兒擺起了棋盤支起了牌桌,見天兒地聚在這裏玩兒,有人覺得下巴毛糙了就往老耿的小折椅上一坐,舒舒服服地讓他給刮上一圈兒。相對於剃頭,刮臉的頻率自然要高出不少,因此老耿也不是每回都收錢,隔三岔五地收個兩三塊錢就拉倒了。老頭兒們心裏覺得過意不去,就總給他捎吃的,今兒送一蘋果明兒給個茶葉蛋,時間一長大家都混熟了。
“您看您這鼻毛,再不收拾過兩天喝粥的時候它得比您嘴先夠著碗。”老耿扶著一老頭兒的腦袋望著他的鼻孔直搖頭,胳膊一伸,手裏就多了把小剪子,嚓嚓兩下,“出氣兒。”
仰著脖兒那老頭兒閉上嘴一噴氣兒,幾根鼻毛楂子被吹了出去。
“老耿!”另一老頭兒抱著個大冬瓜呼哧帶喘地走過來往老耿那小折椅上一擱,“老耿!你來來這個!老聽相聲裏說牛×的剃頭師傅刮冬瓜上的白霜兒都不帶傷皮兒的,今兒你也讓咱哥兒幾個開開眼!”
老耿看著那冬瓜直樂。
“咳,說書唱戲您也信,哪有那麼神,我這一刀下去準得見白瓤子。”
老頭兒急了:“別謙虛啊,玩玩兒嘛,怕什麼!”
“我不是謙虛,是真來不了這個,您還是趕緊抱家去吧,待會兒您家那口子等急了又得當著我們麵兒整治您,我們可都看膩了。”
老耿說著朝旁邊兒幾個老頭兒壞笑,大家一起哄,那位抱起冬瓜走了。
“玩兒呢孫師傅?”
老耿一回頭,見是那白胖子。
“咳,閑聊天兒,嗎去啊?”
“去超市買點兒東西。”胖子說著打老耿身邊兒經過奔不遠處的超市走去。
老耿無意間瞥見胖子腦後有個結著血痂的大包。
“喲,怎麼了這是?”
胖子知道老耿說的是什麼,站住腳摸了摸後腦勺,又看了看其他幾個老頭兒。
“咳,別提了,我不是在那邊兒路口弄了個燒烤攤子嘛,昨晚一點多我收了攤子往回走,經過工地那一段兒的時候沒路燈,被人從後麵給了一磚頭,暈倒是沒暈,就是倒地上起不來了,那孫子搶我裝錢的腰包時我還跟丫支巴了幾下,不過最後還是讓丫給搶走了。”
旁邊兒幾個老頭兒聽了胖子這話都湊了過來。
“報警沒?”老耿問。
“報了,不過我沒看清那孫子長相,估計是逮不著了。”胖子朝老耿笑笑,“沒事兒,隻當是請街坊鄰居吃串兒了。”
老耿繞到胖子背後看了看那處傷:“人沒事兒就成,以後當心點兒。”
“得嘞老爺子,您忙著。”
胖子說完轉身走了。
剛被剪過鼻毛的老頭兒望著胖子那兩人寬的背影嘖嘖有聲:“這小夥子人不錯。”
老耿沒說話,點上根點兒八,看著往來的行人發呆。
轉過天,老耿剛支好大永久,就有人在他身後粗著嗓子說話。
“理發!”
老耿回頭,見是一個黝黑壯實的漢子,三十來歲,頭發有點兒長,後腦勺的發梢兒都杵著脖頸子了。
“坐。”
漢子叉開腿坐到小折椅上,老耿給他把白布圍好夾住。
“平頭?”老耿問。
“四周圍剃光,就留頭頂那一片。”
“哦,郭德綱那頭型唄?”
“對對對!”
“好嘞。”
老耿拿出剃刀開工,剃了沒幾下,左手一不留神碰著了漢子後肩,漢子嘴裏“嘶”的一聲。
“喲,不是剃著您頭皮了吧?”老耿趕緊問。
“沒有沒有,”漢子直搖頭,“你別碰我肩膀那塊兒,疼。”
老耿輕輕拽起漢子T恤的領子看了看,後肩上果然有三道抓痕。
“喲,您這是怎麼弄的?”
漢子猶豫了一下:“跟老婆吵架讓她撓的。”
“哦。”
老耿又看了看那三道抓痕,放下T恤的領子繼續剃頭。
“多錢?”
“五塊。”
漢子給了老耿十塊錢。
老耿在兜兒裏掏了半天,掏出四張皺巴巴的一塊錢紙幣遞給漢子:“您等會兒哈,我記著還有個一塊錢的鋼鏰兒。”
“哎呀,一塊錢就算了。”
漢子揣起四塊錢轉身就走。
老耿看著漢子走出幾步後,喊了一嗓子:“哎,您等一下!”
漢子一回頭,老耿一抬手把一個一塊錢的鋼鏰兒拋過去。
“找著了!”
漢子下意識地伸手一接,朝老耿點點頭,走了。
老耿從兜兒裏掏出漢子給他的那張十塊錢鈔票放到鼻子下麵聞了聞,隨後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旁邊兒那堆老頭兒,往旁邊走了幾步,開始打電話。
“趙兒啊,我老耿……好著呢生意,是這麼個事兒,昨兒有個胖子去你們那兒報案了是吧?……怎麼樣,有線索沒?……小案子就不破了嗎?!……少來這一套!我給你們提供個線索,男的,剛在我這兒剃了一郭德綱的發型,身高在一米七八七九這塊兒,方臉,長得又黑又結實,左撇子,右胳膊上文了個潘長江,應該就住在永華超市附近這個小區裏,去吧。”
“耿爺!耿爺!”
傍晚,老耿正坐在小折椅上困盹兒呢,白胖子滿頭大汗地跑過來。
“錢找回來了吧?”
老耿睜開眼,笑眯眯地問雙手撐著膝蓋直捯氣兒的胖子。
“是!是啊!哎?您,您怎麼知,知道?”
老耿站起來把胖子摁到小折椅上。
“您都知道我姓什麼了,估計是剛從趙所長那邊兒過來吧?”
胖子皺著眉頭捂著胸口使勁兒大喘了幾口氣:“是啊,是啊,耿爺您太牛×了,真的。您怎麼知道是那人呢?”
老耿看了一眼旁邊兒下棋打牌的老頭兒們,胖子心領神會,馬上把大腦袋湊過去。
“趙所長沒跟您說我以前是幹嗎的?”
胖子把腦袋搖得臉上的肉亂飛:“他讓我來問您。”
“這小子,”老耿笑,“那人來剃頭,我瞧見他後肩膀頭子那兒有抓傷,就問他這是怎麼弄的,他說是被老婆撓的,我看了下那傷,絕對是老爺們兒抓的,一般女的沒那麼大手,除非他老婆是女籃的。那會兒我就已經開始懷疑他了,再加上之前我看您這傷口的位置和角度是左手拿著磚頭砸的,所以剃完頭我故意等他走出去幾步再把找的一塊錢鋼鏰兒扔過去,他想都沒想就拿左手接了,還接得特順溜兒。哦,還有,他給我那十塊錢,一股子孜然味兒。”
胖子一臉敬仰地看著老耿。
“耿爺,您以前是刑警吧?”
老耿笑了笑,沒說話。
“您這當刑警的怎麼還有一手這麼好的剃頭手藝啊?”
“嘿嘿,天底下可不光隻有理發師傅會剃頭啊。”
胖子又一臉茫然。
“那您是?”
“法醫。”
胖子打小折椅上“噌”一下站起來。
“怪不得您說您以前拾掇的那些位都不說話呢!”
老耿嘿嘿地笑。
“以後還找我剃頭不?”
胖子想了想:“剃!等我頭上傷好了!”
晚上,老耿和胖子坐在燒烤攤子旁邊兒的小桌旁嗑毛豆。
“對了,耿爺,差點兒忘了,趙所長讓我告訴您,那孫子胳膊上文的不是潘長江。”
“嗯?那是誰?”
“奧巴馬。”
彩蛋:
趙所長坐在桌子後頭,看著銬在對麵兒的黝黑漢子。
“再沒別的了?”
耷拉著腦袋的漢子搖搖頭:“沒了。”
“嗯,”趙所長翻了翻那幾頁筆錄,“哎,你胳膊上文個奧巴馬是什麼意思?因為他也黑嗎?”
“啊?哦,這不是奧巴馬,這是泰森。”
趙所長起身繞過桌子來到漢子身邊,抓起他的胳膊仔細端量,撲哧一聲樂了。
“文這麼一個多少錢啊?”
“六十五。”
“難怪像潘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