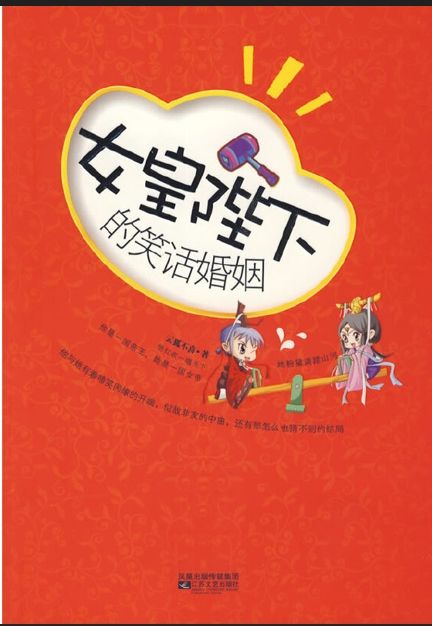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七章 我要去妓院!
說起來,在帶葉蘭心離開大越的前一天晚上,德熙帝曾經把他召去長談過了一次,兩人除了商量一路如果發生意外要怎麼應對之外,也仔細分析商量了葉蘭心榮陽此行的目的。
毫無疑問,她來榮陽,一定是為成王葉晏初,這點他和德熙帝都沒有異議,但是,她到底要幹些什麼,德熙帝也推測不出,隻吩咐他一路小心觀察。
這一路行來,蕭逐不止一次揣測過葉蘭心的意圖,卻很沮喪的發現,她的意圖即明確又模糊。
但是,他毫無疑問是為了晏初來的,但是到了之後她打算做什麼和怎麼做,他卻一點兒都沒看出來。
他生性正直溫和,但生在皇家,注定很多東西他不想看也要看,不想知道也要知道。
他不說不做,並不代表他不懂。
他那個比他還大了三歲的侄兒蕭羌,是這東陸之上眾口一辭的英主,行動往複之間,他都能猜著幾分,但是身邊這個葉蘭心……呃,她下一步敢做什麼和下一步做了什麼都讓人猜不到啊猜不到……
好吧,他承認,是她要幹什麼他想都不敢想。
正如現在。
看完成王入城,她拉著自己興致勃勃的繞著成王暫住的驛館轉了三圈,也不進去也不靠近,就純繞了三圈,便滾回客棧,休息到了晚上。晚飯時刻,她精神再度抖擻了起來,從行李裏扒拉出一兩件衣料極好但樣式樸素的衣服,朝兩人身上一套,又摸出幾錠他劫來的銀子銅子金葉子,興高采烈地抓著他就要出門。
越看越覺得不對,蕭逐在她要溜出門前一把抓住,問她要去哪裏,葉蘭心非常水汪汪地一回眸,用十分之期待的語氣回了他兩個字——妓院。
一瞬間,蕭逐覺得自己爆了,然後他知道,原來自己真的生氣到一定境界,是說不出來話的。
看他僵硬的一句話都沒有,葉蘭心振振有詞,說她從來沒有去過妓院這種地方,她平常偶爾聽到侍衛說妓院裏美女成把成把,她就一直想去看。在塑月被看得太牢,這一路過都是荒郊,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大城市她一定要去看看。
她非常堅定的說,我一定要看美女呀呀呀!
蕭逐就在她的堅定下很常規的蕭瑟了……
葉蘭心死活都要去,他也不能把她綁在床上不讓她去,而且聽了她的描述,他很懷疑她對於妓院的理解到底正確與否……
沒有辦法之下,隻好被她拖著出去,蕭逐不情不願地跟著她朝外走,還試圖做最後的掙紮:“我大越律法有令,官員不得狎妓……”
“沒事兒,這是榮陽,反正沒狎你大越的妓。”
他曾說過的話被當麵丟回了他臉上。
蕭逐絕望地閉上了眼睛,等待再過片刻即將降臨在他身上的脂粉美女們……
“露觀”是晉源城內最大的妓館,從來富貴氣象,歌舞升平。
彩袖殷勤之間巧笑晏晏,舞的是霓裳羽衣,歌的是玉樹蒹葭,怎不叫浪子駐馬,寒夜未央聽長歌?
露觀的舞榭建於水中,周圍高低不一涼亭觀樓,竹蔭環繞,夜晚時分滿池碧波映襯華燈初上萬點金燦,絲絲水氣低低彌漫,有若雲霓,更是襯得水榭之中長袖欲飛,配著淩波輕舞,仿佛隨時會飛仙而去一般。
然後葉蘭心就跟個剛進城的鄉巴佬一樣,看著什麼都好奇地要伸出爪子撓兩把,蕭逐覺得自己太陽穴突突的疼,二話不說,扔下大把銀子,就抓著她朝最高級的觀樓走——露觀最好的觀樓獨幢獨間,設計巧妙,舞榭上一切可盡收眼底,但本身卻掩映竹林之中,不上得樓來,樓上談話和發生了什麼,外界一概不知,這邊即便葉蘭心再搞出什麼來也不至於太驚動。
蕭逐的主意打得蠻好,但是他忘記了,天從不遂人願這條定律……
結果就是,他們到了觀樓前麵,管事非常抱歉地告訴他們,這個觀樓剛才被人包下了。
他們進來的時候,確實是還有一幢觀樓是空的,但是他們到了,卻立刻說沒有了,隻能說明有人中間插了一杠,且這個人來頭頗大,露觀不敢開罪。蕭逐也不願惹事,在管事打躬作揖隻差下跪的賠罪下,選了觀樓旁邊,離舞榭較近,但是離人群較遠的一座半封閉亭子坐下,觀賞歌舞。
他們是掌燈時分過來的,在亭子裏吃過了晚飯,看了歌舞,不知不覺就到了午夜時分,外麵早已宵禁,這園子裏卻正是高潮時分,鶯聲燕語已開始變成淫聲浪語。
蕭逐持身極正,修習武功又是清心一脈,定力極好,這等場麵他看了全當沒看,該吃吃,該喝喝,決不放過每一樣菜——每樣都花了大把銀子,不吃完怎麼對得起又癟下去的荷包!
葉蘭心卻也是一幅純觀賞的樣子,左顧右盼,朝嘴裏送東西的動作也一等一的快。
這東西也就剛開始看的時候新鮮,看多了也就很無趣了。
葉蘭心左右看看,把筷子一扔,就要去散心,蕭逐也隻好跟著出去,兩人穿過竹林,慢慢行來。
這一帶人比較少,風吹竹動,遠處笑語歡聲,管弦之聲輕得像是一陣風,在這紅塵溫軟之地,竟有了幾分清幽。
葉蘭心沒說話,隻是很放鬆地走著,蕭逐也沒說話,兩人就這麼慢慢走去,忽然就有一種歲月靜好,閑庭信步的味道。
這一路走來全無目的,忽然前方有了一線燈光,蕭逐定睛一看,卻發現他們已走到觀樓附近了。
他輕輕咳嗽一聲,正在想什麼的葉蘭心哦了一聲,又往前走了兩步,忽然才明白過來蕭逐意思一樣,看了看眼前觀樓,她剛要轉頭往回走,忽然嘿嘿兩聲,拽了拽蕭逐袖子,“阿逐,走,咱看看去,到底誰搶了咱們的位置。”
“……我不在意位置問題,阿葉。”
“我在意,我生平最恨別人插我的隊!”惡狠狠地說了這一句,挽挽袖子,葉蘭心就氣勢萬鈞地朝觀樓走了過去,蕭逐飛身上去,一把拉住她往回拖。
葉蘭心死命掙紮,蕭逐又不敢真的用力,就在兩人糾纏的時候,觀樓忽然猛地被撞開,一個女子從裏麵奔了出來,緊接著身後一道銀紫身影一閃,已抓住了那奔逃女子。
驚鴻一瞥之下,那個女子素白衣衫,雲髻精巧,身姿修長纖細,臉上覆著一層白紗,容貌雖看不清,單憑那身姿嫋娜,已是上上之選,卻衣衫散亂,顯是被人所迫奪路而逃。
這個女人蕭逐兩人剛才見過,正是露觀的看家花魁琴娘。
他們進來的時候就有人介紹,說琴娘等閑不出來,心情不好大半年不出來都是有的,今天他們運氣好,剛來就碰到。
這琴娘確實神秘得很,在舞榭裏奏琴的時候,一乘小轎直接抬進舞榭,四周垂了紗簾,若隱若現,水風熏熏卷起一角,內中琴娘一身素白,麵覆輕紗,明明什麼都看不清,但僅僅就是坐著撫琴的姿態,一身素白,已然氣質凜然,壓倒群芳。
現下從這觀樓裏奔出來……嘖嘖嘖,葉蘭心都不用不厚道,立刻就想起了逼x未遂這樣字眼。
一看這姑娘撲出來,葉蘭心也不往前衝了,反而一把拽住蕭逐朝林子裏藏,這會倒是蕭逐朝前湊,路見不平就要拔刀。
我說,這地方不是你地頭,亂出頭會被人抽飛的!反正現在也沒出事你老實一會成不成啊?!葉蘭心一把按住蕭逐,就在兩個人也在掙紮的時候,琴娘的方向忽然傳來一聲悶哼,蕭逐就下意識踏前一步,正巧踏上一根枯枝。
四周寂靜,這一聲雖輕卻響亮,在同時聽到這一聲的一刹那,四個人都怔了一下——
葉蘭心第一反應是糟了,被發現了!
蕭逐則一把把她拽到身後,以防萬一。對麵僵持廝打中的男女也楞了,但是等對方醒過神來,反應卻大出所料。
按理來說,這種情況下發覺有人,女方都應該求救,哪知一聽到聲音,琴娘立刻停止掙紮,整個人朝銀紫青年懷裏一撲,被青年一把攬住,將她整個人抱在懷中,臉孔全埋在他胸膛間。要不是蕭逐兩人親眼看到她剛才的掙紮反抗,這樣親昵,幾乎以為是一對情人幽會。
不對,這樣看來,卻是那女子寧願向逼迫自己的人求救也不願意被人看到了——其中有問題!
在這世上,保全之道就是不該知道的就不要知道——
電光石火之間想到這裏,蕭逐抓了葉蘭心就要退走,卻已來不及,一刹那,那青年身形一轉,把懷裏女子掩在身後,眼眸一轉,已看到了二人。
銀紫華衣,碧綠眼眸,芙蓉麵,凶煞眼,在看清青年容顏的一瞬間,蕭逐隻覺得渾身一僵,腦海裏就一個念頭——不好!
他認得這個人,當然,對方也一定認得他。但是葉蘭心不能被認出來。
蕭逐腦子裏極快一轉,主意已定,輕輕一推,不動聲色地徹底把身後女子護住,也不說話,隻等對麵青年先說。
銀紫青年靜靜凝視他們片刻,倏忽唇角毫無預兆地一彎,不緊不慢轉過身去,小心把身後琴娘麵紗拉好,理好衣服,完完全全遮在身後,才回眸,又是一笑,清淺優雅。
他開口,聲音動聽,清澈如銀:“平王殿下,一別經年,別來無恙?”
歎氣,既然對方立意揭穿自己身份,蕭逐心下立刻有了計較,才慢慢展動笑顏,向對麵銀紫青年微一點頭,“托您的福,符大人。”
聽到符大人三個字,對麵青年笑意更深,一雙眼微微眯起,煞氣更重,卻偏偏又扯出無限風情,直如染血長刀上盛開的詭豔花朵,攝人而不祥。
他正是榮陽重臣,當今太子要迎娶嫡妻的嫡親兄長,奉命前來迎接成王晏初的雍侯符桓。
蕭逐知道這個人,正如這個人也知道蕭逐一樣。
南平北雍,蕭逐麵前這個銀紫青年,本就和他齊名於天下。
蕭逐十六歲初陣,三十萬大軍中取敵將首級那一役,對抗的就是榮陽,那次大戰,蕭逐麾下風神軍在榮陽主將戰死,陣腳大亂的情況下,本可以全殲敵軍,但當時還不過是個參將的符桓力挽狂瀾,整頓軍陣,親率五千精兵斷後,保了大軍主力撤回國內,此一戰,符桓也揚名天下。
然後第二年,兩國締結和約,來的使者正是符桓,兩人相見,差不多年紀,都還尚未弱冠,卻也都成名天下,又恰是同一戰成的名,一起出現在大殿上,一邊是紅衣玉冠,絕代美貌的少年親王,一邊是一色銀紫,優雅雍容若狐的榮陽世家貴胄,立刻多少人側目。
他們兩個自然彼此寒暄,一場宴席下來,蕭羌問蕭逐對符桓有什麼看法,蕭逐隻答了此人睚眥必報六個字。
而事實證明,蕭逐並沒有說錯。在此後十年之間,與符桓自身才能一樣馳名東陸的,就是他的睚眥必報和絕大殺性。
而現在,大越平王蕭逐,榮陽雍侯符桓,這兩個絕不應該出現在此地的人,卻偏偏相遇。
兩邊都不是笨蛋,現下情勢是兩邊都不約而同把同伴掩在身後,便都知道對方和自己的情況相差不多,符桓輕輕掃了一眼幾乎被蕭逐掩得滴水不漏的葉蘭心,唇角又是一彎,笑道:“這種地方相遇,就不用敘舊了,我這邊還有一隻野貓要馴,請殿下自便吧。”
他這幾句話說得雲淡風清,蕭逐心下略一掂量,立刻有了計較,也不廢話,輕輕和他頷首為禮,護著葉蘭心就要離開。
就在蕭逐將走未走的一瞬,符桓懷裏的女子忽然發難,蕭逐眼角一斜,赫然看到女子手腕一動,一抹極細的銀光忽然乍起,閃電般掠向符桓的脖頸——
幾乎就在同時,符桓手裏早扣著的一枚信焰一聲輕響已升了空,陡然在半空炸出一個血紅的詭圖案,立刻消散!
距離不近,加上竹林搖曳,蕭逐看不清對麵到底發生了什麼,隻聽得信焰輕響,一股輕輕的血腥味道也隨之漫了過來!
符桓殺心已動!
立刻知道大事不好,蕭逐什麼都顧不得,一把攬住葉蘭心,足尖一點,也不見怎樣動作,人已飛掠而出,兩三個起落,已消失不見。
“哪,垂翼遮天逐雲鳳,劍起鳳鳴天地動。不愧是蕭逐,別的不說,逃得是一等一的快。”望著兩道人影消失的方向,榮陽雍侯輕輕笑了一聲,語音含混,卻別樣撩起一種風情。
他唇齒間銜著一枚小小銀匕,匕首一端是女子一雙玉手,明明隻差一點就可致人於死命,卻因為被符桓握住一雙皓腕,絲毫動彈不得。
符桓銜著匕首說話,毫不在乎,一線鮮血順著刀刃汨汨而下,流過符桓唇角,滑下他形狀優雅的下頜。他唇色本就淡薄,這一映襯,居然就有了豔鬼飲血般妖麗。
笑語問了一句,他輕輕轉眸,眼睫微斂,一雙碧綠眼眸看向麵前女子,倏忽一笑,吐出匕首,指尖一抹唇角,看著白皙指頭上鮮紅熱血,符桓歎氣,滿足又遺憾,“你告訴我,為什麼我這樣喜歡你?你看,我為了你可要跟蕭逐為敵。”符桓聲音本就動聽,這時又加倍溫柔,越發有種曖昧味道,他癡癡迷迷看著麵前女子,語氣越發甜蜜,手裏的力道卻漸漸收緊,女子手腕骨節被他捏得作響,符桓聽在耳裏,唇角笑容越發滿足,“你說,我要拿你怎麼辦?我砍掉你四肢,挖掉你眼睛,讓你再也不能離開我,好不好?”
這句讓人毛骨悚然的話,他說來仿佛情人蜜語,無限溫柔,同時,染血左手輕輕按上女子的頸子,一點點,一點點收緊——
女子一聲不響,仿佛一切全沒聽見,麵紗下那雙美麗鳳眼輕蔑地掃了他一眼,隨即輕輕閉上,竟把他當作無物。
“……怎麼辦呢……你這冰冰冷冷一點兒都不把我看在眼裏的樣子,我也覺得好喜歡……”符桓低低說著,手指收緊,著迷地看著女子呼吸漸漸急促。
“真想就這麼殺了你,你才肯安安靜靜乖乖在我身邊……”
以異常溫柔的眼神注視著漸漸呼吸不上來的女子,符桓茫茫然歎氣,然後同時鬆手——
嗆啷一聲,匕首墜地,女子因為呼吸不順也站立不穩,撲入他懷中,被他雙臂一伸,完全抱住,然後一點點摟緊。
他異常心滿意足地歎氣,然後忽然想起了什麼好笑的事情一樣輕輕一笑,在女子耳邊低語:“放心,他們我會殺掉的,任何看到你的人,我都會殺掉的,不然,我會嫉妒。”
符桓那樣悠悠地說著,碧綠色的眼睛漫漫眯細,內裏一痕嗜血的陰毒一點點泛濫起來:“……陪我下地獄去吧……我的愛人……”
女子倏忽睜大雙眼,然後仿佛用盡了全部力量一般,疲憊不堪地慢慢閉上眼。
輕輕一聲歎息,卻不知,是誰的聲音。
符桓那樣憐愛地看著懷裏女子,愛若珍寶一般輕輕又在她鬢邊一吻,擁著不再掙紮的女子進了觀樓,忽然有風,身後竹林內夜鳥振翅,一隻漆黑鸚鵡撲簌簌遠飛而去。
任何人小的時候,大概都做過生了雙翅,在空中自由飛翔的美夢,葉蘭心自然也不例外,但是,當她被蕭逐一把抱起,飛簷越脊,真的“飛”了起來的時候,她驚恐的發現,自己懼高——
在屋頂上奔波實在不是人幹的事兒啊啊啊啊!雖然在“奔”的是蕭逐,她隻是被“波”而已。
結果就是雙腳剛一落地,葉蘭心二話不說,抓著蕭逐吐了個昏天暗地翻江倒海。
很多人都是這樣,蕭逐並不意外,但是如果這姑娘吐的時候還堅持抓著他吐,還美其名曰美人兒讓我看看你的臉,我覺得多看一會兒一定能少吐一點的話,那麼即便是聖人也會抓狂的。
不過蕭逐明顯在這方麵的意誌力已經超越了聖人這個境界,即便葉蘭心吐了他一身,他也毫不在意,一手抓了她腕子,小心不讓她摔倒,一手運了真氣,抵住她後心慢慢撫摸,一點點送入真氣,平複她體內紊亂的氣息,另外還要分神去觀察四周情況。
天色已是接近破曉,他這一奔,最起碼已奔出百裏,就算符桓的人再怎樣厲害,在搜索的情況下,想要找到他們兩個現在所在的地方,最起碼也要一個時辰,現在可以好好修整一下。
總算把隔夜飯都吐了個幹幹淨淨,葉蘭心搭著蕭逐的手腕晃晃暈乎乎的頭,咂咂嘴裏一股又苦又澀的味道,慢慢回過神來,向四周看去,才發現一路狂奔,兩人已出了晉源,身在荒郊野外,四周月黑風高,真乃放火殺人最佳時間。
葉蘭心看的很仔細,看完之後,拍拍蕭逐的手,開口問了一句:“符桓就這麼殺性大嗎?”
她問這句的時候,蕭逐正搭著她腕子,診脈看她內息,一聽之下,慢慢抬頭,一雙細長鳳眼微微眯起,看了她片刻,“……為什麼殿下會這麼認為呢?”
葉蘭心坦坦然回看,“連客棧都來不及回,什麼都沒拿就這樣直接逃到這樣荒郊野外,我覺得,除了說你覺得符桓已動殺心,而且他動了殺心之後必然很難纏之外,沒有別的理由。他扔出去的那隻信焰,應該也是集結人手的吧?”說完這句,她忽然自己沉思起來,然後比了個手勢,修正自己的用詞,“不,不對,準確說來,我問的應該是,符桓真的那麼難纏麼?”
蕭逐定定看了她片刻,問道:“那你覺得呢?”
她看了一眼蕭逐,又沉思片刻,然後很緩慢地點頭,“憑剛才那一麵,從理性上我完全沒有任何資料判斷,但是我直覺的覺得,他確實動了殺心,也確實很難纏。”
她這麼說的時候,正正抬眼看向蕭逐,那個絕代風華的男子看著她,忽然一笑,“對不起、”
這個話題轉換太快,葉蘭心好奇起來:“為什麼說道歉?”好奇怪喲,是她吐到他身上,又不是他吐了她一身,要道歉也該是她才對。
她完全摸不著頭腦,蕭逐卻很慎重地向她低頭,低聲說道:“我抱歉的是,我一直小看了你、”
是的,他一直在小看她。
不是不知道她無賴之下聰明睿智,也不是不知道她身為一國皇儲必然有她過人之處,但是,從一開始,他就把她放在了需要他保護的,年輕女孩這樣的位置。
他尊重她,卻並不曾真正把她放到和自己對等的位置上。
但是,他錯了。
這是一個足以和他站在一樣的高度,共看天下的女子。
所以他道歉。
葉蘭心聽了他的理由,非常不可思議地看了他片刻。
然後笑了起來。
她笑得很孩子氣,猶如一隻乖巧的貓咪,隻差沒甩甩尾巴,乖巧地叫兩聲來蹭蹭了。
這是多麼有趣的一個男人啊。
東陸本就還是傳統的男尊女卑,即便是塑月這樣女帝立國的國家,都還重男輕女得厲害,但是這個男人卻把一件所有人都覺得理所應當的事情,當作他的錯誤來道歉。
他確確實實把她當作一個女子來對待,卻又尊重她,把她放在一個平等的位置看待,這其實是葉蘭心生命裏,第一次這樣被對待。
她在塑月也是被尊重著的。有人尊重她的地位,有人尊重她的血統,有人尊重她的能力,但是,所有尊重她的人,從根本上說來,都沒有把他當作一個女人來看待——他們都忽略了她的性別,隻看到了他們所尊重並重視的部分。
看她一幅開心的樣子,蕭逐也輕輕笑了起來,眼中卻毫無笑意,他緊盯著葉蘭心,輕聲道:“那麼,殿下應該可以告訴我,今夜到這露觀來,到底是為了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