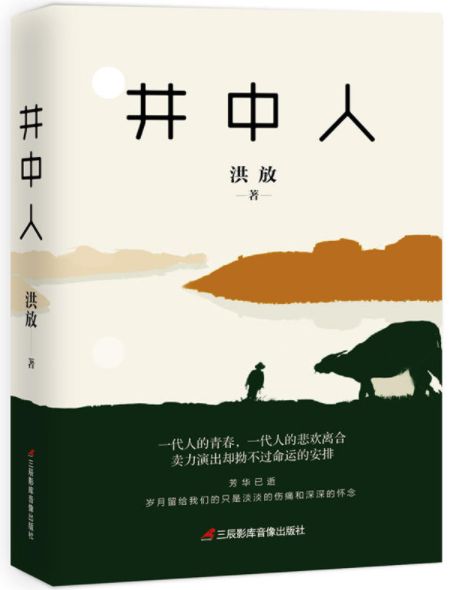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曲折一生
丁成龍清楚地記得,他這一生到現在為止,總共有三次真真切切地想到了死亡。
丁成龍八十歲了。1928年農曆戊辰年,龍年,這年也是民國十七年。閏二月的最後一天,他倒著頭從母親的肚子裏出來。彼時,魯北那個小山村裏,還飄著雪花。他的第一聲啼哭,吸引了雪天裏停在枯樹枝頭的老鴰。
老鴰一共叫了三聲。
父親捏著他的紫紅的小臉蛋兒,說:“這孩子一生曲折!”
父親用的是“曲折”。教私塾的父親年前剛剛從淮河邊上趕回來。本來,他應該在半個月前就去新東家那裏,但為了等他的第三個孩子,他留在了響堂莊上。他托著剛剛洗淨的第三兒子,歎了口氣。
祖父拄著拐杖,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祖父搖了搖頭。
站在祖父邊上的是三姨太。祖母逝去經年,大姨太、二姨太也已歸山。如今家裏隻有這個比父親年齡還小的三姨太。有三房姨太,至少能讓人想起丁家從前的光鮮。但時光與榮耀已不複存在。當下的丁家,在響堂莊上,已破落到靠父親的教私塾的碎銀子來維持。
然而終究是大家庭。祖父搖搖頭後,吩咐三姨太:“擺幾桌席,請莊子裏人都來喝酒!”
父親將嫩如小鼠的三兒子放到母親懷裏。他告訴祖父:“必須得去東家那裏了”。人家的孩子正在等著他念四書五經。家裏的事,就得靠祖父來操辦了。
祖父咳嗽著應答。三姨太拿眼瞟著父親,她的目光糾纏混亂。父親卻不理會,徑自收拾行李,出發到遠離響堂二百裏的臨淮。
當然,誰都不會想到:父親自此一去,再沒回過響堂。
酒席照擺,大醉如常。祖父怪罪父親臨走時居然沒有給孩子取個名字,他思忖再三,決定讓這個三孫子大名叫“丁成龍”。至於這名字有何意義,三姨太問了兩遍,俱無解釋。母親覺得這名字讀著有些拗口,但既是祖父之意,她也不便違拗,隻好聽從。母親心裏明鏡一般知曉:父親對這個三兒子並無多大興趣。年前歸家,父親望著捧著大肚子的母親,說:“倘若是個女娃才好!”父親希望有個女娃,母親也是如此希望。可是,偏偏還是男娃。民國十七年,兵荒馬亂。連續幾年地裏莊稼欠收,不遠的運河裏,魚蝦也越來越少。大概是被不斷樹立的那些漆黑的帆船和拖駁所嚇跑。雖然家道中落,但有父親教私塾的碎銀子,加上祖父每年從院中樹下掏出的一小袋銀元,日子倒也對付得過去。日子能過,希望便多。想生個女娃,給這丁家添一星弄瓦之喜,也是人之常情。
就在酒席過後三天。臨淮那邊傳來消息:父親被亂兵給抓走了。
丁成龍當然不可能看見這些。丁成龍即使活到了八十歲,他也不可能看見他的父親。不過,如此說又有些不太準確。他是看見過他的父親的。他出生時,父親手托著他,還捏了捏他的小雞雞。然而一切不無印象。丁家因為丁成龍父親的突然消失,碎銀子也成了夢想。祖父歎息著從院中樹下挖出最後一袋銀元,但第二天早晨卻不翼而飛。連同銀元一道飛走的還有三姨太。人世蒼涼,人心不古,祖父大哭三聲,嘔血而死。母親領著三個孩子,大的八歲,二的五歲,小的還未滿月,站在雪花之中,看新墳漸起,黃土越來越厚,不由得泣不成聲。大兒子丁成江拉了拉母親的衣角。而此時,丁成龍正熟睡著。他沒聽見鞭炮聲,他也沒看見黃土,他隻聞見了母親的氣息,雪花的氣息,黃土的氣息,迷蒙一片的天空的氣息。
但世事總是迷幻。在後來丁成龍八十多年的歲月中,雪花總是一次一次猝不及防地到來。母親從他三歲開始,不斷地敘說丁家的過往。母親細眉,圓臉,皮膚卻粗糙。魯北風沙大,她日日在風沙中討生活,自然難以滋潤。直到如今,差不多七十多年後,丁成龍依然記得母親的粗糙的皮膚。他用手摸著,鱗殼一般。可是,這種撫摸也隻維持了十年。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冬天,更大的雪天。母親到河邊沙地裏背地瓜。當地瓜背上肩時,她卻一頭栽倒。她一句話也沒留給孩子們,如同父親十年前突然消失一樣。父親和母親,用幾乎相同的決絕的方式,離斷了他們同三個兒子的關聯。
那年,大哥丁成江十八歲。二哥丁成海十五歲。
丁成龍十歲。
丁成龍如今坐在廬州城裏淝河邊上的小花園裏。
“曲折”。這個由兩個字組成的詞,此刻便幻現在丁成龍的腦子裏。他順著這“曲折”二字,清清楚楚地回想著這一生所想到的三次關於死亡的細節。
人到如此歲數。風花雪月已是塵埃。所有的回想,核心已不在此,而是更加觸及內在。比如死亡。二十七年前,丁成龍重回廬州。那時,死亡對他來說,隻是一個曾在腦海裏短暫停留的概念。當然,那也是經過了淬火的概念。因為淬過火,便有了鋼鐵般的冷靜。他更有理由束之高閣,不再理會。可是,自從今年入秋以來,死亡這個詞,連同“曲折”,頑固而執著地鑿擊他。或許這是在提醒他:是該回頭望望自己這一生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總得有次回望。總結也好,歎息也罷,既是自己走過來的路,何妨再慢慢地重溯一回?
丁成龍聽著小花園裏的落葉聲。淝水比早些年更加渾濁了,也更加緩慢。這是他這兩年來的發現。同樣是一條河流,水有流得快也有流得慢的時候。河流亦如人心,隻是子非魚,安知魚之意?
這樣,丁成龍在這個下午,又進入了他所想到的第一次死亡。
那不是母親的突然栽倒。母親栽倒在沙地上後,大雪很快覆蓋了沙地。母親成了一個倒臥在雪地裏的雪人。安靜,寧靜,甚至是死寂。黃昏時,在小鎮子上逛了一天的大哥丁成江回到家,問到母親。丁成海和丁成龍一下子愣了。母親呢?他們如何也不會想到:母親正在黃泉路上跋涉。丁成江領著丁成海和丁成龍,從莊子東頭尋到莊子西頭,再到莊子北頭,南頭,最後,他們在沙地裏一無所獲。白雪覆蓋了一切,母親同所有的沙丘一樣,安然不動。丁成江開始哭泣,丁成海跟著哭泣。丁成龍瞪著眼睛,他沒哭。他這極少哭泣的天性,從出生開始一直保持到了如今。他站在沙地上,不哭,心裏頭卻一陣陣地收緊。他來回奔跑,左衝右突,如同被人鞭打著。最後,他被一團沙丘絆倒。而在他倒下之後,他感到了沙丘的綿軟,甚至還有一絲絲的溫暖。他將手伸進沙丘,他準確無誤地摸到了母親的粗糙的皮膚。他沒有喊,他喊不出來。喉嚨裏有腥鹹味。有血絲味。有細小的繩子勒緊的感覺。
他伏在沙丘上。
丁成江走過來,哭著問:“咋啦?”
他不說。
丁成海也走過來,問:“咋啦嘛?”
他依然不說。
丁成江走到他身邊,想拉他起來。他死活不動,丁成江彎下腰,他卻用了勁,將丁成江拉倒了沙丘上。丁成江一下子明白了,丁成江的哭聲更大了。
母親就葬在沙地裏。
母親真正地成了一塊沙丘。
第二年春天,丁成江帶著丁成海、丁成龍離開了響堂莊。
臨淮鎮是淮河邊上的一個大鎮。早晨,臨淮鎮上熱氣蒸騰。大鐵鍋煮著辣糊湯,胡椒的氣味,直入天空。牛羊雜碎,大饃發糕,一應世上百般好吃,全在這家家戶戶的店麵前陳列著。丁成江領著兩個小的,就在這臨淮鎮上混生活。按丁成江的說法是:既要混口飯吃,也還得捎帶著尋尋父親。父親當年就是在來臨淮鎮的路上被抓走的。這些年,母親從未停止過對父親消息的打探。雖然零星,也理不出眉目。但總是使人感覺到三星兩點的期待。丁成江也便是沿著這期待,他在臨淮鎮的碼頭上做搬運工。他有力氣,年輕,能睡。而且,還有兩個小的跟在後麵。他有動力。他日以繼夜,除了在碼頭上勞作,就是三個人一道在鎮子上閑逛。
臨淮鎮上新鮮的東西太多。丁成龍喜歡看那些貼在站門上的門聯。
大紅的紙,好看的毛筆字。丁成龍雖然不認識那些字,但他喜歡。他一看見這些字,就像被施了魔法,挪不動腿。大哥也拉過幾次,後來便不拉了。有一晚,三個人睡在碼頭邊上的工棚裏,漆黑之中,大哥突然說:“士元,明天送你到鎮上去讀書!”
“讀書?”丁成龍似乎被人一下子推向了遙遠。
“是的,讀書!”大哥用粗糙的手摸著丁成龍的頭,說:“看得出來,你喜歡讀書,也是讀書的料。那就讀書吧!記得母親曾說,你出世時,父親說這孩子一生曲折。我也不懂這曲折的意思,那就是讀書吧!隻有讀書人才算得上曲折!”
丁成龍說:“我不讀。我得跟著你們幹活去。”
二哥一直沉默著。這天上午,大哥才帶著他到大頭上第一次扛包。他的背現在酸疼難忍。
大哥將手從丁成龍頭上拿下,說:“就這麼定了。明天上午我送你去學校。睡了!”
淝河貫穿廬州城。
河水即使再廣闊浩大,但倘若深入進去,其實還是“曲折”二字。這是丁成龍從前想也不敢想的念頭。沒有多少人曾看見過淝河水的曲折,人們看見的都是滿河的流水,攜帶著落葉、垃圾、樹木的碎片、花花綠綠的廣告紙……
現在,丁成龍理解了當年父親所說的“曲折”。
臨淮鎮上的學校一共有兩所,一所是臨淮一中。那是相對來說有錢人才能上的學校。另一所,就是丁成龍所上的臨淮小學。小學建在文廟之後。高大的文廟大殿,將小學校收納於陰影之中。小學其實僅有平房五間。其中教室三間,老師辦公室兩間,食堂一間。或許真的有命數,也甚至人世間其實有冥冥注定,丁成龍看見那些端正的漢字,就感到親切、興奮、快活。先生念: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他跟著念: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
然後,他又加了一句:“樂哉!”
先生笑了。旁邊的三五個同學也笑了。
這笑聲,雖然這麼些年過去,丁成龍還是覺得這笑聲清澈。後來的歲月中,他聽過無數的笑聲。但像如此清澈的笑聲,他很少再能聽到。他記得的也就兩次。一次是當年在新疆,他送女兒丁昌吉去連隊小學上學。才七歲的小昌吉抱著他的腿,不讓他離開。他隻好哄著,直到上課鈴響。他抱著昌吉坐到教室裏的課桌前,那一刻那個漂亮的小蔣老師和全班的小朋友都笑了。笑聲像無邊無際的向日葵被風吹動,還潛藏著小小的波浪。還有一次,是李光雪第一次到百花井時。那應該是1984年,丁成龍重回廬州的第三年。李光雪跟在哥哥李光升的後麵,到孟浩長家裏做客。李光雪十七歲,正上高二。她額頭光潔,笑容燦爛。孟浩長給丁成龍介紹說:“這是東大圩的光升和光雪兄妹倆,他們的母親就是書田。”
“啊!記得。難怪!”丁成龍一下子想起了當年在百花井孟家老屋裏的那個年輕女人。
他又望了哥哥李光升一眼,再看李光雪。就在這個時候,李光雪清澈的笑了聲。丁成龍也就在那聲清澈的笑聲之後,認定了這個孩子。當然,那個時候。丁成龍也絕對不會想到:這個有著清澈笑聲的孩子,將來會跟丁家發生許許多多剪不斷理還亂的故事。比起這些故事,他更願意聽到李光雪的笑聲。那麼清澈,明媚,珠玉一般,渾然天成。
四年後,丁成龍離開臨淮小學時,正是他第一次直麵死亡的那一天。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
很多人一輩子會不止一次的遇到死亡,甚至與死亡擦肩而過。但是,直麵死亡且去思想死亡,卻並不是所有人都曾有過的。死亡如同一個怪物,時時刻刻都存在於人世間之中。它唯一的任務就是選擇。它選擇那些應該死亡的,或者說必須死亡的,也許是不應該死亡但是被人世的罪惡殺戮了的,它選擇好後,便守在人世的上空,注視著這個即將死亡的人。它是端正而莊嚴的,它把每一次死亡都當成儀式。雖然死亡在事實上,往往出乎意料。丁成龍有生以來第一次直麵的死亡,並不是他的母親,而是哥哥丁成江。
丁成江是被刺刀挑的。
丁成江被綁在小學院子裏的那棵大柳樹上。柳樹一段一段地結著老疤子,剛剛下過的秋雨,還汪在這些疤子裏。丁成江的前後,就是一塊碗大的疤子,雨水正慢慢地往外滲出,他的被扯破了的黑夾襖,漸漸地現出了潮濕的痕跡。丁成江不言不語,眉頭緊皺。他左眼已經沒了,血糊在眼眶上。而他的右眼,正努力地睜大。
小學校的孩子們被集中著趕出了教室。一大批日本人圍在院子周圍。校長似乎和日本人爭論了幾句,結果引來了一陣咆哮。然後是靜寂。
丁成龍一出教室門,就看見了綁在樹上的哥哥。
但他並沒有衝出去。但他並沒有衝出去。六十多年後,他回想起這一幕,他也不明白當時自己為什麼沒有衝出去。而他更加清楚地記得的是:他剛出教室門,就被兩個老師有意無意地夾在中間。他跟著老師,站在了柳樹前。他與哥哥僅兩丈遠。他聞見了哥哥身上的血腥味。而哥哥丁成江,隻看了丁成龍一眼,便迅速地掉轉了頭。
瘦長的翻譯在日本人說過後,作了古怪地轉述——丁成江是臨淮抗日遊擊隊的情報員,被捕獲後,拒不交待。皇軍決定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丁成江聳了聳肩膀。左眼的血水順著臉往下滴落。瘦長的翻譯問了日本兵幾句,接著,他閃向一邊。校長對著站成兩排的學生們說:“別怕!閉上眼。”
丁成龍並沒閉眼,他站在第二排,兩邊是老師。他盯著哥哥。就在他看見哥哥轉頭的一刹那,兩條三尺來高的大狗從校門口衝了過來。兩條狗直衝向老柳樹上的丁成江。接著是慘烈地叫聲,狗的撕扯聲,骨頭的折裂聲,以及孩子們往下癱倒的微弱的呼吸聲……
死亡如此迅疾如此不堪地撞擊著丁成龍。
而他更不曾想到的是,在大哥丁成江慘烈地死去的同時,二哥丁成海也在碼頭上被殺害。二哥僅僅因為是丁成江的弟弟,所以理所當然地也必須一同去死。然而,日本人還是忽略了丁成龍。丁成龍在一夕之間,孤身一人。小學校的校長拿出兩塊銀元,讓他火速離開臨淮。他甚至沒有回到工棚收取日常衣物,便出了臨淮鎮。淮河千裏,茫茫無涯。他一直走到天黑,然後沿著河壩,下到一處草丘。他的到來,驚起了一隻正欲眠在草叢中的野鳥。野鳥撲楞著飛向河麵。河水巨大而平靜,但丁成龍知道:在這巨大的平靜下麵,是急速的漩渦。他望著野鳥飛遠,自己便臥進草叢。他剛一接觸到柔軟的秋草,喉嚨裏一股濃烈的腥鹹直衝上來。他猛地嘔吐起來,他吐得沒有停歇,他直吐到滿嘴苦味,一地黃汁。
星光照耀著廣大的淮河。
丁成龍躺在草丘上。往事曆曆,從母親栽倒在老家沙丘上開始,到大哥帶著他們弟兄來到臨淮。如今三個人隻剩下他一個了。多年來,他們不斷地尋找父親。父親杳無音信,大哥二哥又已成黃鶴。他心頭發疼,頭腦發疼,身子顫抖,他在迷迷糊糊中,進入了另一重世界。
那是一重怎樣的世界呢?
六十多年後,坐在淝河邊的小花園裏,丁成龍還在苦苦地思想著。當死亡將黑色的大手,按向它所選擇的頭顱時,那重世界也許就以另外一種方式在打開。丁成龍看見父親、母親,兩個哥哥,依次走進了那一重世界。那裏,水是彎曲、透明的,山是溫和、敦厚的,而花草是清新、可愛的。人,是自由而愉悅的。他想起小學校的老師教他的《論語》。還想起老子的《道德經》。明禮,大同,就是那一重世界的本質麼?誰也不曾真正地說明過,誰也不曾真正地從那一重世界回來過。因此,那一重世界,隻能是一重思想中的揣度。
那是父親的世界嗎?
那是母親的世界嗎?
那是大哥丁成江的世界嗎?
或許都是,或許都不是。那隻是丁成龍的世界。丁成龍在日後六十多年的生涯中,往往被那一重世界所困擾。他曾無數次感到自己走了進去,卻隻是在其門外痛苦地徘徊。對於那一重世界,他是永遠的流浪者。
淮河不語。大河的覺悟正在於它的沉默。丁成龍臥在草叢裏,秋夜已然寒冷,他有一瞬間想到了追隨大哥二哥而去。河水正好接納一切。但是,他又迅速而果斷地切斷了這種念頭。他看著啟明星升起,河水嘩嘩流動,東方一脈張絳紫。他啟程,沿著淮河,往上遊走。三天後,他在一處河灣裏被人截住。來人說是奉了組織之命來找他,且護送他到根據地。他半是疑惑,半是相信,隨了來人進入了桐柏山區。
倘若沒有一九四四年的中秋,沒有大哥丁成江和二哥丁成海的被殺,丁成龍也許就不會坐在今天的淝河邊的小花園裏。城市正在身邊擴張,硬化,長高,長扁,長得冰冷而森嚴。算起來,他看著這個城市,已經五十七年了。一九五一年,他跟隨部隊第一次進入這座城市。那時這座城市僅僅五萬人口,三條大街,圍繞著一座城隍廟。金鬥河從淝河引入,橫穿城區。街人行人稀少,除了城隍廟一帶,幾乎沒有商業網點。部隊是晚上入城的,在他們之前,先頭部隊已經完成了解放這座城市和初步管理。他們的到來,完全是因為這座城市由一座普通的城市,即將變成省會城市。省會從長江邊遷至此地。一大批軍政幹部被從各個地方調來。丁成龍跟在進城的隊伍中,當時萬萬不會想到:從此會與這座城市血肉相連。
他更不曾想到的是:五年後,他會以一個逃犯的身份,逃離這座城市。而三十年後,他又頂著另一重身份,在秋風蕭瑟中,再次回到了這座城市。
小花園裏人來人往。沒有人注意到丁成龍,丁成龍坐著,時光如流水。他成了一枚被時光打磨的石子。他今年八十了,他想起了十七歲那年在淮河邊上的草叢中所想到的那一重世界。
也快了吧!
他掏出小女兒丁昌吉前幾天剛從新疆寄過來的手機。這是一款巨大的手機,大屏幕,大字,大按鍵。女兒說:這手機好用。而且,女兒已經將一些常用的號碼設置成了一到十的阿拉伯數字。女兒在去新疆前還專門為他請了個保姆。本來,她是要帶他一道回新疆的。女兒一直用“回”,而他一直說“去”。他拒絕了。他也同時拒絕了去養老院。他說我還能動,而且,我還想在這百花井邊上多呆幾天。
這一生,沒人能改變他。女兒自然也不會。
他按了個三。他耐心地聽著撥號音。他自語道:“孟浩長,你一輩子就這麼磨蹭!”
終於接了。他大聲說:“浩長,晚上過來喝一杯!”
“好。我也正想呢。回頭見!”孟浩長還是小生嗓子,蜻蜓點水。
丁成龍起身,他得去三孝口切一盤吳山貢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