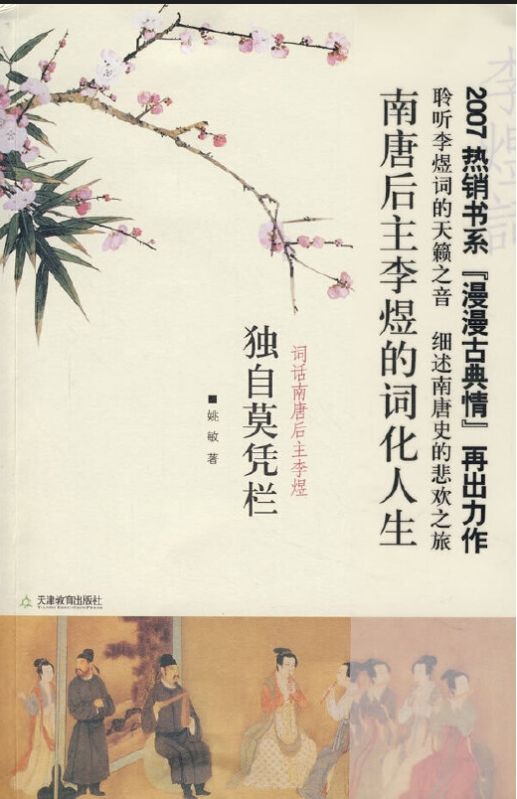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天教心願與身違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跡悵人非,。
待月池台空逝水,蔭花樓閣謾斜暉,登臨不惜更沾衣。
——李煜《浣溪紗》
李煜隻活了四十二歲,生於七夕,死於七夕。民間傳說生於乞巧節的人一生注定多劫難,何況身處那樣一個亂世,末世。他短暫跌宕的一生,總容易讓我想起《歸去來兮辭》裏的那句“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陶淵明在彭澤令任上不忿小人嘴臉,不肯為五鬥米折腰,心裏一不樂意,盡可以紗帽一掛,皂靴一脫,一曲“歸去來,田園將蕪胡不歸”,仰天大笑,直奔南山而去,自此采菊東籬,對飲南山,荷鋤月下,自管自自在去也,誰奈我何。 “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人生忽忽如白駒過隙,怎能為了世人眼裏一點蝸角虛名蠅頭微利,委屈了這一顆傲岸頭顱?可是李煜能嗎?身在萬丈紅塵最深處,即使有出世之心,也無出世之力。縱然“始知鎖向金籠裏,不及林間自在啼”,千般念頭轉過,也隻得長太息一聲:奈何生在帝王家。——草民的樂趣,原來也不是任何人都有福消受的。
這曲《浣溪紗》,寫登臨意。從來詩詞多登高懷人之作。現代交通發達,通訊迅捷,人與人之間相見不難別亦易,早上還在南半球的枕邊人,夜裏可能就在北半球發來短信說在和人喝茶。但是在我們生命中,一定還是有一些人,是“一別音容兩渺茫”,是從今以往,天上人間難相見的。不是音訊壅塞,無法找到,而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縱然近在咫尺,也要任它如隔天涯了。
所以“每登高臨遠,惹起平生心事,一場消黯,永日無言,卻下層樓”,這樣的情緒,千古之下,卻也是相通的。總有一些內心,是現代高科技的便利無法完全滲透和鏽蝕的。讓我們仍然可以僅僅憑借這樣簡簡單單的漢字,就能迅速地穿越漫長的時光隧道,與寫下這些詞句的古人一見如故,心心相印。
李煜,此刻你的登臨,懷想的,又是什麼呢?
是回想起那珠圍翠繞的幼童時,依依在祖父膝前,搖頭晃腦背誦典籍?是憶起昔年與兄弟姐妹們在這樓台水榭對月投壺行射,擊節而歌?還是那白衣勝雪的少年時,與意中人驚鴻一瞥的一見傾心?而今園中亭台依舊,花木扶疏,往事曆曆如在眼前,那些愛過的人,經過的事,早已風流雲散,而早年那個一心沉醉詩詞無意功名的少年,卻終究還是被命運翻雲覆雨的手一把推到了前台,從父親手中接過了這沉重的擔子,糊裏糊塗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身為一國之君,卻連帝號也不敢稱,上朝穿朝服都要看別國的臉色,何其窩囊,想起來,怎叫人不淚濕衣衫!
李煜另有一首《蝶戀花》:
遙夜亭皋閑信步,乍過清明,早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澹月雲來去。 桃李依依春黯度,誰在秋千笑裏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
這首詞也有說是李冠所作的。大多認為這是李煜早期傷春感懷之作:那是春天,清明的一場雨後,桃花正在緩慢凋零。微雲澹月,風裏分明還有微微寒意,春天卻已迅忽離去。好時光總是短暫的,誰能伸手挽留。是誰在秋千架上輕顰淺笑,更襯得這形單影隻的人不勝涼意。
我每讀到“一片芳心千萬緒”的句子,總免不了問:這苦惱的人兒,一顆心究竟為誰如此彷徨,無處安排呢?他是這樣心思澄澈的男子,繼承發揚了父兄才華,卻自動過濾掉了父兄血脈中的霸氣和陰鬱。誰能明白他的身不由己,誰相信他隻是“不幸生在帝王家”呢。既生帝王之家,誰又相信這多愁善感的男子,此刻填滿心裏的悵然,卻是為了手足之情,兄弟之義呢。正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啊。
可憐這一片芳心,說有誰知。
即使一千年時光河流的此岸,你我相信。長兄弘毅卻是不會相信的。
南唐的天空下,皇子弘毅是一個異數。
弘冀是中主李璟長子。唐末之亂中,民間有讖語:東海鯉魚飛上天。而李昪果然發跡,似乎正應了這句傳言。自此李氏就很相信符讖之說。弘毅出生時,民間又正流傳一句話:有一真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向左邊。李璟因此為長子取名弘毅,希望以此名應了這句讖語,算是討個好兆頭。
《南唐書》說弘毅為人沉厚寡言。沉著陰鷙,不苟言笑,這樣的形象與南唐宗室溫柔敦厚之風相去甚遠,格格不入。江南民風淳樸,是經年煙雨浸潤的酥香溫軟,即使民間也自有一種柔和靡麗,三代皇室諸子,大多性情謙和,澹泊,斯文,收斂,是儒家禮義熏陶下教養良好的書香世家子弟。弘毅卻是迥異的,為人行事,竟處處見出一個“狠”字。尤其表現在繼承權的問題上。
李璟嗣位後,封弟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並在烈祖李昪靈位前發誓,約定將皇位兄弟相傳。弘冀此時雖尚年少,但自小便是這樣心思重的孩子,又已先後冷眼看過祖父和父親在皇位問題上的曲折經曆,未必因父親這番姿態就此放棄了心裏對皇權的渴望。
弘毅與李煜不同,雖一母同胞,但出生於亂世,想來當時祖父父親的精力都還無法顧及子女養育的問題,孤獨總是容易催生補償的欲望的。在此得不到的,就要在彼加倍地奪回來,有一天我要讓任何人也不能忽視我。——可以想象這個孤獨的孩子,內心是如何萌生出第一粒野心的幼芽的。長在宮中,身為長子,最有可能也最能有效實現自己對自己諾言的方式是什麼?皇位!一定要坐上這個位子,千百年來皇位父子相傳,立長立嫡,這個位子本來就應該是我的!誰若擋了我的路,對不起,就別怪我不顧念血脈親情了。
於是又一出宮廷爭鬥戲上演了。在江南的草長鶯飛時節,在南唐綺麗灩斂的天空下,皇子弘毅,要奪回在他看來本就屬於自己的權利。所以,凡在他看來對此構成威脅的,都是他的敵人。
也所以,那有著廣額顙隆帝王之相的李煜,首先成為了他要拔掉的肉中刺。
史書上說弘毅“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覃思經籍”。就因為李煜生就了“胼齒重瞳”的異相,讓對皇位誌在必得的皇長子弘毅嫉恨上了,而且看起來這個嫉恨還並不是暗中,而是很明顯的,以至於他要小心“避禍”了。
按說,弘毅是長子,而且從史書記載來看,在中宗的諸子之中,他“為人剛嚴,人多畏懼”,性格剛毅,冷酷,行事利落。既長且嫡,又有能力有手段,作為王位繼承人是順理成章的事。李煜排行第六,本來對他應該是構不成什麼威脅的。但是中宗李景的幾個孩子都早夭,李煜雖是第六子,但實際上他出生的時候,前麵就隻有這個大哥弘毅和二哥弘茂,而弘茂也僅僅隻活了十九歲。這時候的李煜,實際上就是李家的第二個男孩子,何況這個自小就得到爺爺和家人寵愛的弟弟還偏偏長了副帝王之相呢,這自然成為了弘毅很嚴重的一塊心病。可以想見,在深宮內苑的曲曲回廊,幽僻小徑,性格“仁懦”而溫和的李煜,偶與““為人猜忌嚴刻”的長兄弘毅總顯得有些陰鷙狠毒的目光相遇時,心頭都難免心驚肉跳吧。
老天爺有時候也真愛開玩笑。他這樣一個對任何的鬥強爭勝都毫無興趣,隻希望能獨善其身的人,為何偏偏要給他這樣一幅相貌,稀裏糊塗裏就成了人家的眼中釘肉中刺。大哥,讓你這樣不快活不是我的本意啊。
性情仁弱善良的皇子從嘉,敏感到了長兄目光中的敵意甚至殺氣,遠遠地躲開了。
躲起來吧,這樣大家也都清淨。於是,他躲到了鐘山上,每日,伴著靈穀寺的晨鐘暮鼓,沉浸於經卷典籍,作畫,吟詩,填詞。
第一塊擋路石算是搬開了。弘毅卻並沒有放下心來。
因為他更明白,此時自己繼位路上的真正的絆腳石並不是這個天生異相的弟弟,更大的威脅來自叔父景隧。甚至也不真得來自景隧,因為決定權掌握在父親的手裏。父親那裏才是關鍵。
所以,關鍵還是要得到父親的青眼。
而知子莫若父,以李璟的心智,弘毅的這點心思怎麼瞞得過他。
不知道李璟到底是怎麼看待這個有別於其他孩子的長子的。其實在我看來,真正繼承了中主李璟骨子裏的霸氣的,正是弘毅。然而弘毅太不懂得藏拙了,鋒芒畢露,卻完全沒有學會乃父表現在外的謙謙君子風範。
所以,在確立景隧為皇太弟後,李璟就將弘毅遠遠地打發到潤州去了。
機會總是垂青那些有準備的人的。戰爭,給了弘毅嶄露才華的機會。
這一年,周師攻陷廣陵,此時吳越也趁機攻打常州。中主李璟擔心弘冀安危,於是派人召他回金陵。然而滄海橫流之際,正是男兒建功立業好時節。弘毅骨血中自有亂世豪傑的驍勇之氣,原非貪生怕死之輩,但父親此番專程派人下詔,卻足見父親仍是顧念和愛惜他的,常年遠離帝京的弘毅,對此一定還是感動的,不回去豈非有負聖眷。所以頗為猶豫。部將趙鐸卻勸說他道:元帥之重,眾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
趙鐸說得有理,主帥怎能臨陣退縮,置這麼多將士於不顧。何況弘冀本也覺得這正是嶄露才華的機會。於是聽從趙鐸之言,打發了中主使臣回去複命,轉告自己堅守的意思。然後就調兵遣將,加緊備戰,軍心民心於是大振。中主李璟隻好派遣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和右衛將軍陸孟俊帶兵增援常州。兵至潤州時,樞密使副使李徵古建議弘毅用神衛統軍朱匡業代替柴克宏,但弘冀認為不可,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是兵家所忌,拒絕了這一建議。而且很信任柴克洪的膽識和才略,認為他一定可以破敵立功,並願以自家性命作保。
士為知己者死,柴克宏非常感激,這一仗果然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並俘獲了敵方將佐數十人,押解回潤州。這次戰爭弘毅鋒芒嶄露,更讓景隧覺得危險,於是又一次請求去太弟稱號,回到自己的藩地。而景達在這次戰爭中作為元帥,卻大敗南歸,唯獨弘冀有功,於是終於得稱所願,立為太子,參決政事。
然而弘毅畢竟年輕,得意未免忘形,以為這天下就是自己的了,於是開始放開手腳整頓起朝綱來。《南唐書》說“中主仁厚,群下多縱馳,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綿軟的南唐有了陽剛之氣,本來應該是一件可喜的事,然而如果認為那坐在高高皇帝位子上的父親真是庸碌之輩,弘毅就錯了。江南世代詩禮傳家,治理國家靠的多是文治而不是武功,弘毅太張揚了,即使有才,終究不是人君之度。其實早在那場嶄露頭角的勝仗中,李璟就已經對他有了不滿。當時南方諸國交戰,多不殺俘虜,而是戰後互相交換,這樣一來,戰場上將士往往並不拚死出力,反正被俘了以後也能回去。各國雖然也知道其中弊端,但出於人道,都約定俗成遵從這一點。而弘冀打了勝仗後,居然將押解回潤州的俘虜盡數斬首,這樣一來,敵方俘虜被殺,無以交換,己方被俘將士也就或被斬或為奴,總之再也回不來,戰場上還有誰敢不拚命?所以軍容一時大振。但這樣的做法畢竟血腥狠毒了一些,嗜殺畢竟不是人主之風,所以中主李璟“不悅者久之”,而弘毅竟不自知,在參決政事中愈來愈放肆,終於把他老子惹毛了。史載有一天李璟大怒,用打毬杖痛打弘毅,並一邊打一邊恨恨罵道:“你再這樣我馬上把景遂召回來!”
弘冀聽了這話大懼,眼看煮熟的鴨子要飛,那以前的種種努力豈不是白費了。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幹脆來個斬草除根永絕後患一了百了。於是竟然找人下毒謀害了景隧。
景隧暴亡,自然有人替弘毅掩飾,隻說是死於急病。中主李璟歎息了一聲,並不認真追查。其實他心裏真不明白嗎?然而事已至此,家醜不可外揚,而且父子和兄弟,到底還是親疏有別的。弘毅是自己的兒子,難道已經斷了手足筋,還要剜卻心頭肉?隻是可憐景隧,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終於還是成了第一個犧牲品。
溫軟的南唐出了這樣一個狠角色,也是天命使然吧,李璟想來也是無可奈何了。此時南唐已經江河日下,半壁江山已盡數割讓給後周,李璟恥於向後周稱臣,於是多次遣使向周世宗請求傳位於弘冀,並正式承認為周的附庸國。周世宗卻怎麼也不答應他退位,並且還正式寫信力勸阻止說:你還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而且國家正有難,怎麼可以輕易卸責脫逃呢,你飽讀詩書,更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吧。這番話軟中有硬,李璟隻好作罷。於是周世宗又派人慰問,並對弘冀也有賞賜安撫。
這件事頗有意思,人家的國家,老子要讓位給兒子,還要請示別人,而這個別人居然不允許。我想,周世宗和李璟都是聰明人,或者,李璟終於覺得,此時的南唐,也許還真的需要一個弘毅這樣狠角來推一把了吧。而周世宗,既然已經與弘毅交過手,怎會不考慮到,以弘毅的性子、膽略,肯乖乖對周俯首稱臣嗎?所以怎麼會自己給自己安放一個定時炸彈呢。
其實他們都高估了弘毅。說到底,弘毅也並不真是心狠手辣之輩,他不過是個想要得到關注的孩子,即使下手去搶的,也隻不過在他看來,本來就是屬於自己的氣球和糖果。而一時糊塗,用了不光明的手段去搶,即使搶到手了,還是無法心安理得。弘毅終究也沒有成為勝利者,景隧死後,弘冀心中愧疚,常常夢見景遂鬼魂索命,幾經驚嚇就一病歸西了。這個被爭來搶去的帝位,就這樣戲劇性性地落到了對此毫無興趣的李煜,當時尚是皇子的從嘉頭上。
時時刻刻覬覦惦記著這位子的,卻一一退場,而這處處要避讓的,卻避無可避。命運的手翻雲覆雨,誰能料定,真個是天教心願與身違。
誰會相信在這場漩渦中心的他,心中更加顧念的仍是兄弟手足的情分呢。
也許連與李煜最親厚的弟弟從善,也未必會全然相信這一切吧。
從善的心裏,恐怕一直是有陰影的。
從善為中主第七子。弘毅死後,儲君之位空虛,也許元宗李璟是因為剛剛看完弘毅與景遂的兩敗俱傷,憂心未息,對於立儲一時猶豫不決。此時群臣在觀望中各自在剩下的皇子身上押賭注,或明或暗,也有人在不動聲色觀察。自認善於揣摩上意的權臣鐘謨這次自有打算,竟將籌碼押在了皇子從善身上,這看似冒險島孤注一擲,其實正是鐘謨的精明,因為將寶押在從善身上的人顯然不多,但隻要押對了,日後就是元老功臣了。於是屢次在李璟麵前誇讚從善才幹,貶損李煜,說他“器輕誌放,無人君度”。但李璟何等樣人,怎會看不清他的這點把戲。或許反倒促使他拿定了立李煜的主意。鐘謨因此失勢,並被貶官。
從善失去依靠,但被鼓蕩起來的一點野心卻不易死去,竟然還心存幻念。李璟在南都駕崩,此時後主李煜留在金陵監國。從善竟向掌管遺詔的徐遊索討遺詔,為徐遊斷然拒絕。回到金陵後,徐遊將此事告知後主,後主隻是寬厚地笑笑,並不以為意,反而更加多方撫慰從善,封賞有加。
這天性仁厚的男子,即使做了天子,還是改不了他的書生氣。也許在他看來,自己並不想坐卻坐上了這個皇帝位子,心心念念想這著位子的弟弟卻偏偏坐不了,倒似乎是自己虧欠了從善。所以從善這在大臣看來如此忤逆的舉止,後主竟然並不放在心上。也許他從來都不覺得這個皇帝的位子應該是自己的。那是因為,他從來也沒有垂涎過這個位子吧。
在他眼裏,帝位的分量,怎能及得兄弟的分量呢。
別來春半,觸目柔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據說,這首《清平樂》就是李煜為思念從善而作的。
開寶四年,李煜遣從善入周朝拜,宋太祖趙匡胤封了他一個泰寧軍節度使的虛職,賜第汴陽坊,就此將其羈留汴梁,不準南歸。分明就是將其扣作了人質。後主手足情深,屢次作書陳情,試圖以兄弟深情感動對方。但趙匡胤不為所動,始終不肯放還從善。李煜牽掛胞弟安危,自此抑鬱不樂,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每每臨窗北望,泣下沾襟,並自此連四時歌舞遊燕都無心了。
又是一年早春了。落梅如雪,草色初青。長空雁回,人在何處?
北地苦寒,從善,這江南煙雨薰風裏長大的男子,不知道是怎樣捱過這又一個冬天的。
李煜本手足情重,對其他弟兄亦如此。即使對弘毅,那處處嫉恨他,欲加害他的弘毅,在他的心裏,也首先是長兄,是一母同胞的骨肉,所以他也隻是處處避嫌,生怕惹他不高興,甚至為此不惜躲進山中,與晨鐘暮鼓相伴。從鎰開寶初年出鎮宣州時,他也率近臣在綺雲閣為之置酒賦詩餞行。徐鉉有詩句相贈:“滿座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李煜親自為作序,並吟詩句“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勸勉從鎰莫畏前路,寬舒懷抱,放遊天地。對從鎰尚且如此周到體貼,何況是這個最為親厚的弟弟從善,何況從善實際上是為自己做了替身呢。因此,當從善被扣留,或許他竟然更覺虧欠這個弟弟的多了吧。
某年重陽,有大臣上書奏請後主輟朝一日秋遊。重陽登高,煮蟹下酒,把酒賞菊,自古便是文人才子的賞心樂事。但一想到此情此景,便不由得又勾起對羈留敵國的弟弟,想起唐人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榮萸少一人”之句,胸中萬般牽念無以排解,於是揮筆寫下《卻登高賦》,寄托相思,也謝絕群臣。中有這樣的句子:“愴家艱之如毀,縈離絮之鬱陶。陟彼崗兮企予足,望複關兮睇予目。原有翎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洱!無一歡之可樂,有萬緒以纏悲。”淒惻酸楚,不忍卒讀,確是如斷手足,悲懷切切。
從善經年不得返,從善妃子常常在後主麵前哀哀哭泣,後主無顏以對,此後聽說她來就隻好躲起來,從善妃最後竟至於憂鬱而卒。
心情不好時,拿“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勸慰自己。人生天地間,如蜉蝣,如螻蟻,沉浮起落,離合聚散,也許冥冥中自有天意。連萬人之上的帝王,也未必做得了自己的主,世事豈能盡如人意。所以古人說,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終須暫時放開了懷抱,得一時歡樂也是好的。
通透的人,總是活得自在些。遍地塵埃裏也能開出花來。
這倒勾我想起一個人來,那個琢磨 “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這個集活佛、浪子、詩人甚至流浪者於一身的傳奇人物。他在人世間僅逗留過短短的25年,卻為西藏這片土地留下了大量的民歌,人們交相傳誦他的情詩,甚至忘記了他的達賴身份。這個在情竇已開的十五歲才以轉世靈童身份進入布達故宮的俊美多情少年,厭倦深宮單調刻板的黃教領袖生活,眷戀多姿多彩的世俗人生,更思戀年少美麗的情人,經常在夜色掩護下溜出布達拉宮與情人幽會,或化名宕桑汪波混跡歌樓酒肆宴飲狂歡。八廓街上有座黃房子,有說就是微服出行的倉央嘉措以少年宕桑汪波的名義與情人幽會之處。
這種隱秘的浪子生涯一直持續了好幾年,直到某夜破曉之前天降大雪,清早鐵棒喇嘛發現雪地上腳印,順著腳印追索到了六世寢宮,行跡終於敗露,受到嚴厲懲戒,他的情人也被處死。自此他開始創作大量的情歌,歌頌愛情,歡樂,自由,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悲憤、無奈和抗爭。
我讀過好幾個漢譯版本的倉央嘉措情歌,總覺得都不盡人意。也許隻是因為任何的翻譯,都難以窮盡原作的風貌。倉央嘉措的情詩在藏民中如此受歡迎,其原來的語境一定遠高於翻譯後呈現的這些終究顯得生硬的漢字。遺憾的隻是我們不懂得藏語的音節韻律,無法深入領會這個倜儻多情的少年借助這些自由浪漫的歌節所要傳達的內心。我想,也許最懂得他的,應當是匍匐在西藏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生靈,那些有著天空一樣清澈的眼睛,泥土一般淳樸的麵容的藏民。不過,即使在這些被漢語肢解得斑駁破碎的音節中,還是可以看到自由、歡愉、幻滅,看到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種種人世共通的情愫,那是身份、地位、戒律都無法捆綁的人性。
在某個譯本裏,看到這一句:
留人間多少愛,迎浮世千重變
和有情人,做快樂事
莫問是劫是緣
初見到這句歌詞,是在很早以前,在電影〈青蛇〉裏聽到陳淑樺唱,一點嫵媚,一點清冷,一點不羈,一點無奈。說不出的沉溺。卻並不知,原來這句,也是來自倉央嘉措情歌,一旦知曉,卻也覺得,的確再也沒有別人,能將這句說得這般的貼切和到位。佛法的本義,分明不是束縛,而是放下。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沒有人比這個浪子更能深刻領悟佛的寬憫和慈悲。
而他的放浪形骸終於使他成為西藏政教鬥爭的犧牲品,25歲時被清廷廢黜,在解送北上的途中死於青海湖畔。但我寧願相信另一個版本的說法,他是在青海湖中夜遁去,化名為阿旺曲紮嘉措,開始了自由的流浪生涯,先後遊曆印度、西藏、四川等地十餘年,曆盡艱辛。這似乎更符合人們寄托於西藏這塊有神靈的土地,寄托於這個集神性與人性一體的傳奇故事的理想。也更符合我對於這個來自天地也將回歸自由的靈魂的祝福和祈願。能掙脫桎梏,重新回到寬廣的藍天下,呼吸到自由新鮮空氣,是多麼幸福的事情,肉體的艱苦算得了什麼,生命如彗星般短暫又有什麼遺憾?怕隻怕,如李煜這樣,長恨此身不由人,貴為君王又如何,何曾有過真正的歡顏?
25歲,正是李煜在風雨飄搖中正式坐上南唐帝位的年紀。事實上這時候他早就已經不能稱“帝”,隻能叫做不倫不類的“江南國主”了。在他父親元宗李璟的手裏,江北土地已盡數割讓給後周,成為北方政權的附庸。國號不存,帝王的一應權利隨之減免,包括儀仗、裝飾都不得使用帝王之禮,連袍服也不可以用皇家的明黃色,隻能用臣子的紫色。甚至在處理中宗的葬禮儀製上,他這可憐的南唐國主都做不了主,還要專門上表呈情,言辭謙卑地請求上國恩準,得到點頭才敢使用皇家儀製。
不過,又有誰能斷定得了,李煜的懦弱,是貽誤了南唐,還是保全了南唐呢。在那樣的亂世,隻剩下半壁江山的南唐,在他手裏還能休養生息十多年,也算是江南百姓的幸運吧。試想一下,即使換了個狠角色如弘毅,是不是就能改變南唐覆亡的命運呢?也許,那一天來得更早些也說不定。
曆史沒有假設。世間的禍福,誰能說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