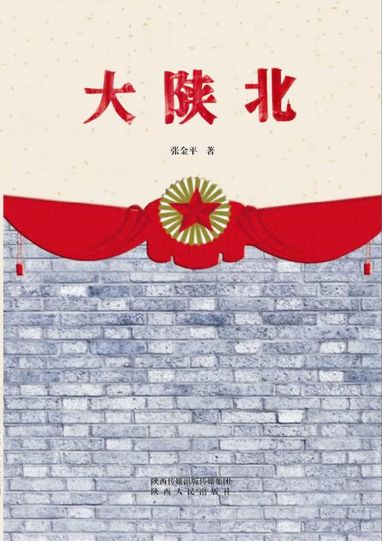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二章
過了夏天,時間的軌跡就從很多地方凸顯了出來,比如夜長晝 短,比如落葉繽紛,一抬眼就能看到風的臉色。從陝北到北京,這 一路很長,長得足以讓高良長大。高良能感覺到,這個家看上去高 靖遠是一家之主,其實真正拿事的是吳夢湘,也就是說,至少在他 來之前這個家是吳夢湘說了算。吳夢湘年齡比高靖遠小,還為他生 了一對兒女,高靖遠心裏感謝她,平時對她嗬護倍至,許多事情上 自然多多少少都讓著她,久而久之,吳夢湘便坐實了自己的家庭地 位。下班之後,高靖遠買了一條魚,喜滋滋地去紅燒。像高靖遠這 樣曾經血戰沙場、馬革裹屍的漢子, 居然能夠心甘情願地去做家務, 這一切經曆了漫長的蛻變過程……他想借這條魚一來慶祝兒子的回 歸,二來緩和緊張的家庭關係。吳夢湘倒沒有拒絕,高坡一看到高 良上桌就立刻叫道,爸,他沒洗手。高媛剛舉起的筷子被吳夢湘一 把奪過去,高良自然受不了這種壓抑的氣憤,幹脆用手抓起半條魚, 邊啃邊吧嘰嘴說,好吃!吳夢湘剛要發作,高良被魚刺卡著喉嚨了, 梗著脖子,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來,憋得臉發紫,急得伸著 手指摳喉嚨,摳了半天沒摳出來,反而把自己摳惡心了。高坡和高 媛看得緊張不已,吳夢湘氣得摔下筷子回了屋。高靖遠一番美意,
化成了泡影。
高良好不容易吐出了魚刺,整個人虛脫了一半,剛躺下,吳夢 湘和高靖遠的吵鬧聲傳過來了。吳夢湘說,你孩子已經接回來了, 我希望你尊重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不要影響和破壞我兩個孩子 的生活。高靖遠說,你什麼意思?高良剛從陝北來,很多生活習慣 和方式都跟我們不一樣,你總得讓他慢慢適應吧。高靖遠想息事寧人, 可吳夢湘偏偏要把這件事情掰扯清楚。吳夢湘拿著一張紙說,我不 管,我有自己的原則,你看著辦,能接受就讓他繼續住,不能接受 你自己想辦法。吳夢湘說著把紙拍在桌上,紙上是她寫好的十多條 互不侵犯的規章製度。高靖遠看了一眼,剛要爭辯,高良的三弦就 在這時響起來了。他彈了一段前奏,開始說唱道,這一家打馬往東奔, 那一家打馬往西行,馬跑疆場三十合,各執兵刃起戰爭,這一家舉 槍迎麵刺,那一家大刀忙擋定,槍碰大刀叮當響,刀碰長槍冒火星…… 吳夢湘和高靖遠衝進高坡的房間,高良正坐在床上邊彈邊唱,高坡 在自己的床上捂著被子。夜深人靜,高良的三弦聲活蹦亂跳,吳夢 湘大叫了一聲說,別彈了!高良沒理,高靖遠盡量壓了壓聲音叫了 聲,高良!高良停了說書,手上仍彈著弦,高靖遠隻好放低聲音說, 高良,你看,現在都很晚了,你弟弟妹妹明天要上學,我們也要上班, 你能不能先別彈了?高良說,我這不是給你們助陣嘛。高靖遠無奈, 不知道再說什麼,吳夢湘卻不客氣地說,你看他這是什麼態度,吵 了別人不道歉反過來還說是助陣,他到底想幹什麼?高良沒理會, 仍舊撩撥著弦,弦聲就像一群興致勃勃的小蝌蚪唏哩嘩啦地攪醒了 一池塘的水。高良撥完過門兒,張口就說,這位大嫂你聽好,你的 頭發黃蠟蠟,左眼有個肉疙瘩,右眼有個蘿卜花,鼻子插蔥裝大象, 嘴裏頭還有顆老鼠牙!高良的每個字都吐得很清楚,字正腔圓,這 是說書人的基本功,高坡聽清楚了,噗嗤一聲笑了。吳夢湘衝著高 靖遠喊,高靖遠,你聽到沒有,他居然罵我!高靖遠隻得問高良, 你怎麼能罵人呢?高良瞟了吳夢湘一眼說,我說我的書,又沒指名
道姓,怎麼就是罵你呢?吳夢湘的臉再也撐不住了,突然地伸手要 奪高良的三弦,高良就在這時站了起來,雙手抱著三弦,怒視著吳 夢湘,就那麼直昂昂地高出吳夢湘半個頭來。吳夢湘再沒動手,高 靖遠為難地想勸兩人,站在中間不知道怎麼開口下手,高良又彈了 一把說,我又彈了,怎麼樣?高良的目標對準了吳夢湘,吳夢湘被 動地脫口就說,這是我家,不許你彈,不然就滾蛋!吳夢湘一說出 口,高良的腦門霍地升起一股熱氣說,這是高靖遠的家吧,你憑什 麼讓我滾蛋?這兒除了你,大家都姓高,你算老幾?高良的話戳中 了吳夢湘的要害,給自己和吳夢湘甚至高靖遠都沒留有餘地。吳夢 湘的尊嚴被一個破小孩蔑視,她的驕傲被肆意地踐踏。她沒法向這 個野孩子撒氣,隻能衝高靖遠,高靖遠,這就是你兒子?接著又說, 高靖遠,你告訴他,我是誰?高靖遠手忙腳亂地解釋,想和稀泥, 卻把自己攪和的一臉泥巴……這場戰爭,最終以吳夢湘搬去單位住 宿而告一段落。
夜,恢複了寧靜。高靖遠再次走進兒子的房間,高良已經躺下了, 三弦就放在床頭,高靖遠還沒說話,高良倒先開口問,你什麼時候 送我回去?高靖遠一愣,用力壓住自己的怒火,定定地看著高良, 這孩子,骨子裏很像蘭花,高靖遠想起蘭花,覺得自己更不能不管 高良,就說,這兒才是你的家,其他的想都別想,早點睡吧。
高良睡不著就想起自己的師父,陝北的老百姓都叫他師父韓司 令。韓司令是陝北有名的說書人,他給毛主席說過“古朝”,還得 到過毛主席的表揚。延安時期,韓司令用說書宣傳抗日,宣傳革命 道理,宣傳勞動英雄,報紙上說,韓司令說書能頂一支部隊,他就 是部隊的司令,韓司令就這麼叫出了名。韓司令有三個徒弟,大徒 弟王鐵錘,二徒弟張滿炕,三徒弟孫改改,個個都是有本事的能人, 高良是後來硬貼上去的。高良認識韓司令的時候,韓司令正帶著他 的三個徒弟在公社門口說書,說的是《楊公案》。高良從公社門口 經過,突然看到聚集了一大堆人,韓司令的三弦就在這時響了起來,
高良被三弦聲吸引,鑽進了人堆,這一鑽,他的命運改變了。
按石頭隊長的話說,高良就是個小混蛋。長工爺爺死後,生產 隊把放羊的活兒交給了他,一來高良不喜歡讀書;二來自從蘭花去 世後,生產隊規定每家輪流負擔高良三天夥食,讓高良放羊,是讓 他為自己掙口飯吃,免得生產隊裏有些人說閑話。高良吃不飽飯就 把眼睛盯在了羊身上,羊是生產隊的集體財產,不能私自亂殺亂賣, 那是犯罪。高良動趕著羊往山崖邊走,如果羊摔下去準得死,羊死 了自然能吃羊肉。可到了山崖邊,羊在小道上穩穩當當,傲視著高 良。高良不服氣想推它下去,羊“咩”地叫了一聲,對高良充滿了 嘲弄和鄙視。高良閉著眼睛使勁往前一推,幾乎用上了全部的力氣。 他設想,羊撐不住力就會掉下去摔死。可羊順著高良的力道偏向了 一邊,這一偏,高良就像是使勁推開了一扇虛掩的門,門後是懸崖, 自己一頭栽了下去,羊滑到山崖邊的小道上,慢慢又爬上去了。
石頭和生產隊的社員把他救上來的時候,高良渾身是傷,人已 經昏迷,這時候高靖遠給轉戰延安時負傷被留在延安的老部下牛排 長寫了一封信,讓他幫忙把高良帶回北京。牛排長得到信那是當成 軍令來執行。牛排長找到石頭要接高良,石頭實在瞞不過去了,這 才告訴他高良摔傷了,在公社的衛生院縫了三十多針,把醫生嚇壞 了,把石頭也嚇得半死。高良剛剛在醫院住了兩天,牛排長就找來了, 拿著高靖遠的信,像拿著一張軍令狀。高良不肯跟他走,他拿出繩 子當場把高良連同被子一起捆了,扛起就走。牛排長是個急性子, 這一捆一扛,再加上高良一直喊救命,拚命掙紮呼救,醫院的醫生 護士就把他當成了壞人,幾個醫生護士一邊攔他一邊通知了公社, 石頭趕到時,公社主任已經把他羈押在辦公室。石頭趕到公社趕緊 解釋說,哎呀,主任,誤會了,牛排長是戰鬥英雄,怎麼會做拐賣 兒童的事啊,誤會了,誤會了!石頭作證,公社主任給牛排長的公 社掛了電話,這才證實了他確實是戰鬥英雄。
牛排長從公社出來就守在了醫院外,想著既然傷沒好,那就等
傷好了再帶他走,於是天天像門神一樣杵在醫院門口。高良的傷好 得差不多時看到他,一轉念就來一招調虎離山,牛排長跑進了病房, 高良早就跑出醫院了。跟著高靖遠打了近十年的遊擊排長,竟然被 一個小孩耍了,他直罵自己粗心大意。
高良從醫院出來路過公社門口,突然聽到了韓司令的三弦聲。 那三弦聲吸引著高良駐足,可沒聽幾句牛排長就找來了,牛排長在 人堆裏邊擠邊找邊喊高良,高良一激靈鑽到了韓司令的說書桌子下, 牛排長在人堆裏找了一圈高良沒找到,隻得往其他地方去了。高良 就縮在桌子下自自在在聽了一回書,聽著聽著,倒睡著了,直到曲 終人散。韓司令的三個徒弟收拾桌子,這才發現了他。大徒弟王鐵 錘在高良屁股上踢了一腳,高良醒來,看到韓司令和他的三個徒弟, 倒也不驚不詫。三徒弟孫改改以為找他的牛排長是他大,還幫他擋 了一下,聽說不是,小姑娘眉眼一彎,笑了。
說書這行當應該算是手藝,靠的是一張嘴一雙手,手到嘴到, 聽眾才到。說書人說得高興,觀眾跟著樂嗬,說書人說得傷心,觀 眾也陪著灑一把淚。韓司令坐在公社的食堂,公社主任打開了話匣子, 說書這活兒,都是韓司令說他們聽著,現在總算輪到他說他們聽了。 一大盆餄餎擺在桌上,公社主任從他們鄉的文化扯到了群眾的熱情, 扯到了人多力量大、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韓司令師徒在鄉公社 吃飯不是請客,那是送文化下鄉,鄉公社屬於派飯,如果到了生產隊, 就到社員家裏派飯,他們要完成縣裏的文化指標,說書就成了義務。 兩個徒弟覺得,吃口飯還得看別人的臉色,半天不許動筷子,先聽 公社主任講,徒弟們說了一天的書,早餓得前心貼後背了。三個人 盯著餄餎吃不成,一個個都心不在焉,王鐵錘不住地擦拭那把三弦, 張滿炕不住地咳嗽,改改趴在桌上休息。就在這時她看到了高良, 高良從灶房窗戶探了半個腦袋上來,瘦猴子似的,一雙眼睛倒明亮 得很,改改看著他偷偷地笑了,他看著桌子上的餄餎直咽口水。
公社主任終於吩咐大師傅把羊肉湯端上桌,這就意味著可以吃
了,王鐵錘趕緊給師父先盛了一碗,然後才和師弟師妹吃起來。高 良等韓司令師徒吃完一出門,他便衝了進去,桌上還剩一碗,他早 看見了,那是公社主任的碗。韓司令是無冕之王,他隻顧做彙報, 公社主任滿嘴是公社的各種工作,韓司令不聽也得聽,韓司令他們 吃完了,公社主任又忙著送他們出門,等他回來,高良已經吃了 一 大半了。公社主任傻眼了, 這點羊肉是他們鄉得了全縣先進的獎品, 本想著招待韓司令自己也能落一碗,沒想到竟讓高良吃了。公社主 任叫來大師傅一問,大師傅也懵了說,這不是韓司令的徒弟麼!高 良搶著說,是哩,是哩。說話間, 已經把最後一點餄餎撥拉進了嘴裏。 公社主任哪能不知道,韓司令從不輕易收徒,這是全縣都知道的事。 高良急了,嘴上倒一點不露怯說,哎呀,主任,韓司令前天就收我 做徒弟了,你不信我給你說一段……高良說著還真給公社主任說了 一段,就是下午他聽到的《楊公案》的開場白,說得還真像那麼回事, 公社主任一聽愣了,也分不清楚高良說的是真是假,一分神高良跑了。 跑出公社,高良又盤算就這麼回了生產隊,還得餓肚子,不如追上 韓司令,說不準能收他做個徒弟。於是一直尾隨著韓司令的說書隊伍。 天盡黑了,走在最後麵的改改突然有些害怕,蹭蹭地往前竄,緊接 著落在最後麵的張滿炕腳步一緊,又撲在了王鐵錘身上,王鐵錘一 掌推開他,臉上不高興地罵道,滿炕,你跟上鬼了?跑甚了?張滿 炕臉紅通通地說,師哥,我咋老覺得今天身後有甚東西跟著呢?不 會真是鬼吧?張滿炕一說,孫改改更怕,直往韓司令跟前湊,王鐵 錘也怕,看師父一臉正氣,又暗自穩住了,幾個人往身後一看,什 麼也沒有。王鐵錘說,師父,是不是咱今天吃了羊肉讓臟東西聞到了? 韓司令濃眉一擰,先把改改攬到跟前說,改改別怕!師父走了一輩 子夜路,還沒有聽說有鬼!說完,韓司令讓三個徒弟先走,自己一 閃身鑽進了旁邊的小樹林。
高良從樹後露出頭看到前麵人影綽綽,以為韓司令師徒已經走 遠了,趕緊追,韓司令一閃就擋住了他的去路,反倒把高良嚇了一跳。
韓司令說,娃娃,你是趕路呢還是鬧甚呢?高良一急說,幹爺爺師父, 我這趕路哩。這咋叫的呢?這時,王鐵錘帶著張滿炕和孫改改也跑 了回來,王鐵錘一看是個孩子,抓起來要打,被韓司令攔住了。張 滿炕眼尖,認出是下午躲在桌子下的孩子,改改也認了出來說,你 要到哪裏去?高良說,你們到哪裏去我就到哪裏去。韓司令說,你 跟著我們做甚?高良說,聽書,聽會了,我也說書。十一二歲的孩子, 口氣倒不小,韓司令的三個徒弟聽他這麼說都笑了,也沒當回事兒, 高良卻不服氣說,笑甚了?你們說了一天書我都記住了,我說給你 們聽聽,看我記得對不對。高良也不露怯,又說起了《楊公案》的 開場,可還沒說完,韓司令已經帶著徒弟們往前走了。
這是他第一次見師父韓司令和師妹孫改改。想著想著就迷糊著 睡著了,他夢到綿延無垠的山山峁峁和大片紫色的蕎麥花,改改喘 著氣,跑到了蕎麥地旁的山崖邊上,看著漸漸遠去的長途客車,她 眼淚婆娑地望著長途客車遠去的方向放聲唱著——
哥哥走了不來了,妹妹放聲哭開了。 一對對沙燕向南飛,撂下 妹子誰來配。一個枕頭一條氈,一個人睡覺有多難。飛起一對鴿子 落下一對對鷹,什麼人害得你離這村。南雲一發下雨呀,哭哭啼啼 扔我呀。鳳凰落在梧桐樹,哥哥沒走我箍住。石榴榴花 石榴榴樹, 把哥哥哭得難留住。上個灣灣下道坡,大睜兩眼撂下我。哥哥走來 妹妹照,眼淚溜在大門道。叫一聲哥哥你走呀,撂下妹妹誰管呀。 騾子走頭馬走後,擱下妹子誰照應……
高良夢著改改的歌聲就突然醒來了。他索然無味地走出來,看 到高靖遠正準備早飯,他不願意落座,剛要再走,高媛笑吟吟地捏 著一個雞蛋給他。高良心裏突然一熱,接過來……
衝著高媛笑了笑吃了。高靖遠看在眼裏,默默高興。
吃過早飯,高靖遠先把高坡高媛送到學校,然後帶著高良出了門。 父子倆遊了天安門、頤和園、長城, 還吃了小吃,照高靖遠的想法, 北京的名勝古跡,他想帶著高良都去看看。高良第一天來就想著要
回去,高靖遠當時很生氣,可回到屋裏一想,又覺得不能怪高良, 怪誰呢?誰也怪不著,高良有高良的理由,吳夢湘有吳夢湘的理由, 高靖遠也有高靖遠的理由。高靖遠漸漸看出來了,高良雖然頑劣, 但明事理,不愛看書,但學習能力、適應能力都極強,比如高良學 騎自行車,不到半個小時就會了,下象棋,幾天的時間就和老首長 不相上下。高良在幹休所的院子裏學著騎自行車。高靖遠遠遠地看著, 眉眼裏藏不住的幸福,黃戴恩看他高興就問,這兩天沒聽到你吼叫, 家裏都安撫好了?黃戴恩嘴裏的“家裏”自然是指吳夢湘,高靖遠 一愣,臉上的笑容散去了說,哪兒呀,我是看著這邊高興,忘了那 邊著火,還讓您老惦記著。黃戴恩又說起將高良帶在身邊的想法, 高靖遠回去跟高良一說,高良沒同意,非要在家裏住,否則就立刻 回陝北。黃戴恩一聽,恍然了,心裏想,這小子門兒清,這哪裏是鬧, 高良顯然是要爭家裏的地位,爭的是尊嚴,而吳夢湘顯然爭的也是 這個東西!黃戴恩又問高靖遠,既然這樣,你打算怎麼安置高良? 高良的年齡介於讀書太大當兵工作太小的階段。高靖遠打聽了幾所 學校,都不願意接收高良這麼大的孩子,高良也不願意去。高靖遠 隻能說,先這麼養著唄,誰叫我欠他呢。黃戴恩說,這就是你的問 題了,他是個孩子,不早點為他打算,怕是要出問題哩。
黃戴恩的話說過沒兩天,高良真出了問題。周末,高坡想出去 放風箏,高媛拍著手直叫好,趁著高靖遠去廠裏尋吳夢湘的機會, 高良騎著剛學會的自行車,就帶著兄妹倆晃晃悠悠出去了。郊區的 風有點大,風箏被纏在了電話線上,怎麼拽都拽不下來,高媛急說, 哥哥,你能把它弄下來嗎?高良又拽了拽風箏線,還是拽不下來, 三兩下爬上了電線杆,抓著電線一使勁,風箏落了下來,電線也斷了。 這事導致幾條街上的機關單位電話突然都沒了聲,往小了說是破壞 國家的公用設施,往大了說是間諜罪,很快三個人就被帶進了公安 局。高靖遠和吳夢湘兩個人匆匆趕來, 一進門就一邊道歉一邊解釋, 好說歹說,央告了半天,才罷了。
從公安局出來,吳夢湘一句話不說,自己先衝回了家,一路上 憋的火都有了釋放的空間,吵架的聲浪比上次有過之而無不及。焦 點還是高良,吳夢湘的理由是,高良今天敢把兩個孩子偷偷帶出去, 明天說不準就帶到他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高靖遠認為這件事情沒 那麼嚴重,高良也是為了帶弟弟妹妹玩,不能判斷一個人總用好壞 來區分!吳夢湘據此認為高靖遠是牆頭草,黑白不分,是非不辨! 這個過程中,高坡始終一言不發,高良也不願意多做解釋,所有的 責任他都默認了。這事在高媛心裏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直到後來長 大,仍然念念不忘,後果是高媛和高坡到牆角罰站。高靖遠則在努 力說服教育高良,但是高良冥頑不化地瞪著高靖遠不說話,反而讓 高靖遠再次心軟了。吳夢湘看到高靖遠敗下陣來, 再次對準高靖遠, 追根溯源,認為這件事情決不能這麼簡單地不了了之!吳夢湘是廠 裏的工會副主席,她認為高靖遠的思想意識出現了滑坡——這並不 是簡單的家庭問題,不是感情問題,是原則問題、政治問題!吳夢 湘要讓高靖遠從根本上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不能直麵問題,是機會 主義在作祟,封建家長作風,官僚主義!到處抹稀泥打哈哈,不認 真批評教育,草率地應付,得過且過,那是形式主義!又說,家裏 的錢少了,意思是高良出現,錢才少了,自然是高良拿走了。高靖 遠氣得發抖,論吵架,他不是吳夢湘的對手,論氣勢,他也不如吳 夢湘,但在這件事上,他第一次跟吳夢湘拍了桌子大吼,吼得有了 高團長的氣勢,你無非就是嫌這個孩子來家裏了,我告訴你,別想 美事,除非我死了,孩子必須在這個家呆著,還有,你是一個大人, 不要血口噴人,誣蔑一個孩子!
誣不誣蔑的,高良不在乎,高靖遠兩口子的爭吵於他有種說不 出的快感,高坡已經回屋做作業去了,高良拿著三弦出了屋,身後, 高媛拉著他的衣襟跟了出來。院子裏有些蕭瑟,高良坐在石階上, 撩撥著三弦,弦聲悠揚。高媛問,哥哥,這個樂器叫什麼呀?你怎 麼老彈著它?高良說,叫三弦,好聽嗎?高媛說,好聽!高良說,
好聽哥哥就給你彈。高良打起精神重新彈起三弦。沒多久,吳夢湘 背著一大包行李從他們麵前走了過去,暮色濃重。爭吵再次以吳夢 湘離家出走告終,對這個結果,高靖遠似乎已有思想準備,屋子裏 靜得出奇,高靖遠看著屋子,突然有種四處都在漏風的淒涼感。弦 聲就在這時再次傳了進來,高靖遠的火騰地被逗了起來,高靖遠走 出屋,要發脾氣,可看著兩個孩子的背影,一股心酸和疲累由然而起, 火就那麼一搖曳又熄滅了。高靖遠走到兩個孩子的身後,輕聲說, 都回去吧。高媛乖乖走了進去,高良收起三弦說,你還是送我回去吧, 在這裏,我不痛快,你們全家都不痛快,何必大家都不痛快呢?高 良的話讓高靖遠心裏疼了一下,然而下一秒,他的臉上又堅定而倔強, 高靖遠說,誰鬧誰不痛快,我沒什麼不痛快的!
上學的去上學,上班的去上班,高良突然覺得這也不是他想要 的結果。周末,高良騎著自行車載著高坡高媛出了城,三個孩子在 城外的一處小山崗後麵停了下來,公路上隨時有過往的大卡車,高 良想爬卡車回去,這樣就不用買火車票了。高良要走,高坡和高媛 都舍不得,但是高坡突然改口說,你回去,天下就太平了!我媽也 就能回來了!高良很清楚,高坡說的是對的。高坡和高媛決定送一 下高良,也算這段時間的情誼,倆人看著高良跳下山崗,爬上一輛 大卡車,高媛嘴一癟,哭了,舍不得了。高坡不服氣說,我才是你 親哥哥。高媛說,才不是呢,你有好吃的都自己藏著,你偷了媽媽 的錢還賴在高良哥哥身上。高媛說得沒錯,偷錢的是高坡,高坡故 意偷了吳夢湘的錢想讓吳夢湘以為是高良,逼走高良,因為高良來 了後,他這個學校、家裏最受重視的好孩子被忽視了。
高良怎麼走的?哪條路?哪輛車?兩個小孩子誰都說不清楚, 天又黑了,高靖遠心裏著急,怕嚇著孩子,也不敢過於表現出來。 尋到半夜,隻好先回家,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某部隊打來的電話, 高良爬上的卡車是城郊某部隊的軍車,汽車開進了營區。高良鑽在 軍車的蔬菜堆裏,美美睡了一覺,醒來一撩篷布,幾把黑洞洞的槍
對準了他。
高良被當成間諜抓進了營區的值班室,高靖遠趕到時,高良還 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有多嚴重,還直嚷嚷著自己是劉洪隊長,高靖遠 氣得恨不得扇他兩耳光,部隊的規矩他知道,高良的性質在當時備 戰備荒的特殊時期,沒直接槍斃已經算幸運了。高靖遠想帶走高良 被拒絕了,想找營區的守備首長也被拒絕了,想用一下電話也被拒 絕了。高靖遠隻好騎著自行車跑到幾十裏外找電話。給黃戴恩打完 電話又匆匆趕回了營區,就在值班室門外守著等著,那種揪心與煎熬, 高良自然也不知道,直到高靖遠把他接回家,直到高靖遠一個耳光 扇在他臉上,他才懵了。
高靖遠這一巴掌讓高良感到了一個男人的憤怒,一個總覺得虧 欠了他的男人的忍無可忍的憤怒,還有說不清楚的失望。高良摸著 自己火辣辣的臉,心裏雖愧疚得很、懊悔得很, 但嘴上卻較著勁說, 我就是想回去!高靖遠本來正喘氣,一聽要回去就嘴上狠著說,想 回去是吧?想回去,好,老子讓你回,滾,滾——高靖遠一把掏出 包裏的錢和糧票,扔了一桌子。高良頭也不回,衝進房間,開始收 拾東西。東西還沒收拾完,吳夢湘回來了,她一手拉著高坡一手拉 著高媛,隻冷著臉看著高靖遠。高靖遠想起來了, 今天忙高良的事, 竟忘了接孩子。高靖遠趕緊拉過孩子,讓他們回房做作業去,回頭 看吳夢湘正從挎包裏掏出一張紙,放在桌上說,簽字吧。高靖遠一 時沒反應過來,拿起紙就看了個開頭,嘩地把紙撕了個粉碎。吳夢 湘也很平靜,但眼神冷峻,看著高靖遠鄙夷地說,請你也尊重我的 選擇,離婚對我們倆來說都是解脫。吳夢湘的意思很明確,兒子和 妻子,隻能選一個,高靖遠的心裏萬馬奔騰,馬蹄子每一下都踩在 他心上,最後踩碎的是他作為男人的尊嚴,高靖遠憤怒地說,吳夢湘, 你沒有權利跟我離婚!
高良的手顫了一下,房間的門都敞開著,他聽到了兩人的吵鬧。 接著,吳夢湘說,高靖遠,我不想與你爭吵,我說過我的眼裏絕對
容不下一粒沙子!我的家也一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要麼最好, 要麼最壞!高靖遠的語氣裏似乎帶著委曲求全的溫和說,你為什麼 要這樣咄咄逼人?高良隻是個孩子,他有什麼錯?你和一個孩子爭 來爭去,有意思嗎?難道你要眼睜睜看他像個孤兒一樣嗎?就算是 街道上的孤兒,我們也該伸出手拉他一把不是嗎?這場離婚事件的 結果仍然是吳夢湘離去,但是,她給了高靖遠一個月期限考慮。
當天夜裏,高良翻來覆去睡不著了,他的耳邊不停地響著高靖 遠和吳夢湘的爭吵,不斷地思索著,或許這也不是他的初衷。天快 亮的時候,高良抱著三弦出了門。街上行人不少,匆匆忙忙,他走 著走著天就大亮了,一路打聽一路走,嘈雜的聲音漸漸稠密起來, 他站在西站南邊的十字街頭,突然地猶豫了,就這麼走,似乎不夠 光明磊落?他還沒想明白。
高靖遠一起床看到高良不見了,頓時慌了。高良要是真回去了, 他這個做父親的,怎麼對得起蘭花?怎麼對得起韓司令?他迅速騎 上自行車舍命地往火車站追去,追到十字街道,看到高良果然站在 人行橫道的口子上,孤單地,想往前走又想往後走,躊躇不已。高 靖遠叫了一聲“高良”,高良沒聽到,高靖遠又叫了一聲,騎著車 子衝了過去,車流聲人聲交織濃密,高良還是沒聽到。這時,一輛 卡車從街口飛速地衝了過來,高靖遠正好騎到了人行橫道,巨大的 刹車聲傳來,高良隻覺得被用力一推,一個踉蹌,再回頭,高靖遠 已被拋到了很遠的地方,他的自行車倒在地上轉動著輪子,高良突 然意識到了什麼,從地上爬起,衝進了人堆大喊,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