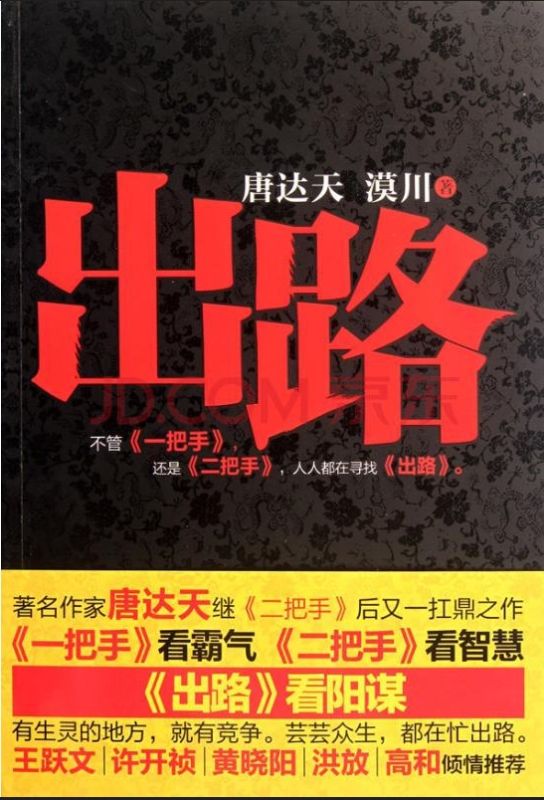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一章 複員了,父親卻退休了
1. 一聲長歎
葉飛永遠忘不了那個遠離城市的小所,那個被黃沙半淹著的小所。事過多年之後,他常常想起,如果當時不去那個小所,也許他的初戀不至於被葬送,也許雲雲還活在人世,也許他的命運將會被重新改寫。但是,現實就是現實,不是假定。他去了,這就注定了他從此邁上了一條曲折複雜的人生道路。
葉飛清晰地記得,那是一個飄落著塵土的初冬,空氣中彌漫了一種嗆人的幹塵味,整個天空混沌一片。這是一個令人情緒糟糕的日子,就在這個日子裏,他懷揣著分配通知書,在雲雲淒淒的目光中上了班車。
他當了四年兵,複員後滿以為能夠分到一份好的工作,跟他的雲雲日夜相守地度過他的一生。沒想到他的父親從局長的位子上退下來了,父親的權力落到了他的副手胡紅國的手中,葉飛就被分到了那個遠離城市的沙梁小所。
當他拿到分配通知書的刹那間,他的心仿佛被針刺一般的難受。雲雲偎在他懷裏,輕輕地說:“飛子,能不能想個法子,不去沙梁?”
他咬了咬嘴唇說:“我還是去吧,好賴也是份工作。”他知道,父親大權旁落之後,就意味著他失去了選擇的可能,他不願意為此而增加父親的負擔。
雲雲揚起頭說:“我等著你。”說著淚就溢出了她的眼眶。
他用手指輕輕揩著雲雲的淚水,苦笑了一下說:“又讓你受委屈了,等以後調回來,我要加倍地償還你。”
雲雲說:“誰讓你償還,隻要能夠在一起,我就滿足了。”
他拍了拍雲雲的背,說:“好,我先欠著。”
葉飛坐的是一輛早被其他路線拋棄了的“駝鈴”牌老客車,空蕩蕩的車廂裏沒幾個乘客,越發使得這個早晨變得冷清。“老爺班車”用了近五個小時才把一百公裏的沙路走完。葉飛下了車就像一件剛出土的文物,用手揉揉眼,找到那個他將要駐紮青春的小所。
小所的圍牆都長在沙丘中,幾間低矮的土坯房坐西朝東地孤立著,院子大得像片戈壁,每間的門都鎖著,牆根處滿是東倒西歪的枯草,好像到了一處被廢棄了的荒舍。葉飛從門口的木牌上確認這兒就是小所,仰起頭,閉起雙目……好大一會兒,他才長歎一聲,睜開雙眼。
拍拍到處是沙的衣服,他有點痛惜雲雲為他買的這身西服。葉飛從掛包裏拿出張報紙,找了一塊被太陽照射得暖和的沙坡坐下來。他點了一根煙,掏出書來,看了一會兒,什麼也看不下去,就把書扣在臉上,不一會兒就進了夢鄉。
他夢見一張薄薄的紙片不抵風力,隨風忽東忽西地在天地間不停地旋轉。又夢見和雲雲挽著手,在沙洲的大街上歡快地追逐……
醒來時,四周能見度已經很低了,偶爾傳來野貓野狗的叫聲,令人有點生畏。葉飛吸了幾口冷氣,抖抖身子,拎著包又朝幾間低矮的平房走去。來到房前,他看到靠邊一間的玻璃窗上映出些燈光,腳好似踩到了彈簧,特興奮地跳上去敲門。屋裏邊的人聽到敲門聲問了一句:“誰呀?”接著傳來連續不斷的咳嗽聲。
葉飛應了一聲,門打開了,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張皺得找不到眼睛的臉。
昨天晚上,葉飛聽了父親對這個小所人員的介紹,但看到這張臉,他心裏仍感覺對不上號,隻得堆上滿臉的微笑問:“大爺,您好!”
老頭點了一下頭問:“你是誰?有啥事嗎?”話沒說完,老頭又開始咳嗽,扭曲的臉讓葉飛的心提起很難放下。
終於找了個機會,葉飛舒展眉頭,趕忙說:“我叫葉飛,新分配到這兒來工作的。”
“噢!”老頭點了點頭,盯著葉飛的臉打量了一下,閃了閃身子說,“進來吧,早聽說你要來的。”
葉飛進了房,把背包放在地下,老頭示意讓他坐在小床上。小床上鋪著一塊不知什麼顏色的床單,葉飛用手摸了摸,滿是沙塵,心頓了幾下,還是坐下了。
房間裏沒什麼擺設。靠牆邊一座火爐燒得旺旺的,葉飛感覺暖和了許多。老頭坐在另一張床上,床頭有一個和床麵齊平的小方凳,上麵放著一盞油燈和一些散形的紅柳小條,火苗昏昏的,伴著一束束竄不完的青煙,空氣中彌漫著嗆人的煙味。葉飛掏出香煙,遞給老頭,老頭擺擺手,拿起一支黑中透黃的煙杆朝他搖了搖說:“我吸這個,那個沒勁。”
老頭說完從垂在煙杆上的黑煙袋裏摸出一點煙絲,放在大拇指和中拇指上下揉搓,揉搓成一個小煙蛋兒放進煙鍋裏。又拿起一根紅柳條對著油燈的火苗點著,然後點燃煙鍋裏的旱煙,大大吸了一口,還來不及感受,濃煙伴著起伏的咳嗽全噴了出來。於是,咳嗽聲又斷斷續續地在房間裏彌漫開來。
葉飛的耳膜艱難地承受著,他終於理解了吸煙為了咳嗽這句話的含意。但他還是深情地看著老頭,看著他深深的皺紋和他的衰弱。老頭雖然拒絕了他的香煙,但老頭的旱煙驅散了他的困意。
老頭過足了煙癮,放下煙杆,把吐在地麵上的濃痰用腳抹開,兩人才開始交談。葉飛知道了老頭叫王援朝,快六十歲了,年末就要退休。葉飛有點不相信,老頭的這張臉才經過了五十九個年頭。
葉飛說以後我就稱您王爺吧!老頭臉上映出層紅光說:“稱爺也差不多。孫子都兩個了。”
“那您老可幸福了,兒孫滿堂!”葉飛不失時機地恭維了一句,王援朝哈哈地笑了起來。笑完,王援朝說:“我記得,你父親比我大三歲,他身體還好嗎?”
“心臟不太好,每天都靠藥養著。”葉飛說。
“你爸呀!人太要強了。那病還是大躍進修水庫時得的。”王援朝說著停了停,仿佛沉浸到了遙遠的回憶之中,兩眼木木地看著空氣說,“大躍進修水庫那陣,你爸是工段長,領著我們沒白天沒黑夜地幹。那時生活很苦,每天吃供應糧,沒法吃飽,餓著肚子還吼著學大寨的歌,推著架子車一路小跑。那時沒有太多的機器,全靠人力。可幾千號人,渾身都勁蛋蛋,苦不覺得苦,累不覺得累。我還記得那個雨夜,沙洲多少年都沒下那麼大的雨了,庫岸被雨水泡塌了,你爸領著我們整整一個晚上在雨地裏打樁、壘壩,渾身沒一塊兒幹的地方,像是剛從水裏撈出來一樣。第二天,你爸就病倒了,你爸那個人啊!”王爺沒再說話,又拿起了旱煙袋,深深地歎了口氣,情緒很是激動。
父親的這段光榮業績,葉飛清楚得都能幫母親記起地點和日期。打小母親就是以此為教材教他憶苦思甜。葉母看著兒子長發披肩,嶄新的牛仔褲磨出洞,流裏流氣地和石磊、虎子在大街上東逛西竄,心裏那個急啊!她對兒子一次次講,不厭其煩地講葉局長的偉績。可葉飛呢,自認為整個沙洲都被自己踏在腳下,自我感覺特好,根本感覺不到父親業績的優秀。
父親的這段業績已好久沒有人講起了,如今聽王援朝講起,葉飛第一次感到自豪的同時,又有了一絲對往昔白白糟蹋了的歲月的惋惜。王爺抽了陣煙,又咳嗽了一陣子,繼續描述起了葉飛不曾經曆的那段物質匱乏、精神亢奮的歲月……
整個晚上,葉飛也沒怎麼睡踏實。聊了大半夜,又被王援朝長一聲短一聲的咳嗽伴著。天已微明,葉飛才感覺入了夢。醒來已至中午,王援朝拾掇好掛包,準備回家吃飯。他邀請葉飛,葉飛仍想睡一會兒,沒去。王援朝告訴葉飛出大門右拐不遠處有家羊肉饅頭店。
葉飛其實早就餓了,隻是覺得剛來,不好意思。王援朝走後,他按王援朝所指來到羊肉店,狠狠吃了一大碗。然後回到小所,倒頭大睡。
不知過了多久,院內的嘈雜吵醒了葉飛。小所裏的最高長官韓興民所長和會計田軍來了。葉飛拉開門,作了自我介紹,並和韓興民、田會計握了手。韓興民指給葉飛一間宿舍,田軍拿給他一把鑰匙。葉飛開門的聲音和突進的一束強光驚動了一群小老鼠,它們四下奪路而逃,竄進東倒西歪的雜物深處。室內彌漫著股股黴氣,很是嗆鼻。葉飛用手在臉前扇扇,一手捂住鼻子,將破鞋爛襪、紙灰酒瓶清掃了出去,又打來一桶水把牆角的老鼠洞澆了個透。
房間裏原本就有床、桌子等物品,葉飛一一擺置好,擦幹淨,並把火爐生起。不一會兒,小所的其他人都進了屋,韓興民看著幹幹淨淨的屋子,挺高興地給了些鼓勵。
就這樣,葉飛的工作就從打掃自己的宿舍開始了。
日子過得很無聊。小所的冬天基本上沒什麼事可幹,葉飛除了睡覺就是自己擺弄著飯吃。他其實挺怕做飯,但身處小所,也就談不上喜歡不喜歡。日子總得過,他如此安慰著自己,每天看著太陽移動,便成了他最費時的工作。到了這個時候他才明白,小所的其他人為什麼對他心懷感激。小所裏其他的人都不遠不近地散落在周圍的村莊,葉飛沒來之前,他們的工作就是排個班輪流在小所睡覺,以防門窗玻璃什麼的被“好心人”拿走了。葉飛的到來,徹底解脫了他們,葉飛十天八天見不上他們的影兒也很正常。於是,空蕩蕩的大院,讓葉飛對王援朝的咳嗽都忍不住產生思念。
直到帶來的書被一本本翻透了,葉飛才理解了雲雲送他上車時說的那句話:“飛子,去那種地方上班,跟坐牢有什麼兩樣?”
“毛主席不鑽延安窯洞能住進中南海嗎?越是艱苦的地方,才越能鍛煉人。”葉飛不知是安慰雲雲還是安慰自己,但雲雲卻背過身流出了眼淚。
雲雲打小和葉飛在一起。雲雲有個不幸的家,母親在雲雲兩歲時因難產隨沒見天日的弟弟同去了另一個世界,雲雲對母親的感覺全是從葉飛媽媽那兒得知的。父親李建國在車站搬運處工作,喜歡麻將和酒。也許是壯年喪妻,人們對他的行為也寄予了同情。葉飛臨來沙梁前去看過雲雲的父親一次,李建國依舊老樣,葉飛去時帶了兩瓶老酒,兩人相對無言卻喝光了一瓶。
李建國一直對葉飛的態度很是冷漠。他總以為是葉飛耽誤了雲雲,可女兒對葉飛一往情深,便也隻好聽之任之了。
雲雲天生就很美,楊柳般的身材透射出萬種風情,很討人憐愛。特殊的家庭給了雲雲特殊的性格,她很孤僻,也對生活有著過高的期望,這大概是漂亮女孩的天性吧!雲雲有著很聰慧的頭腦,打小學習挺好的,可就是高考差了那麼幾分。葉飛學習成績忽好忽壞,不是腦子笨,而是根本就靜不下心來。也許有了這定格的因素,許多許多的故事才有了根源。雲雲後來被招工,進了沙洲市農具廠,與生鐵鋼條為伴,毫無趣味的工作使她像一棵焦枯了的樹苗期盼著雨露的滋潤。直到葉飛從部隊回來,他們天天泡在一起,生活才像播滿希望的種子,有了生機,也有了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