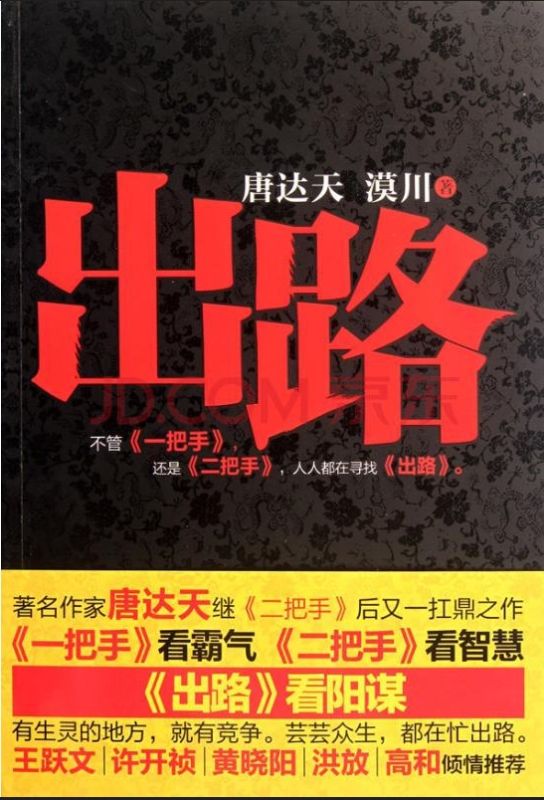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2. 愛情危機
冬眠在黑糊糊的小所裏,時間過得很慢。葉飛感到連生理的需求也得靠最原始的動作才能得到安慰,他很悲涼,卻又無法不忍耐。
熬到了年根,葉飛告假回到沙洲,他對母親流露了不想去那個連人影都看不到的小所的想法。母親聽了看著他,沒有言語,隻扭頭長長地歎了一聲。
葉飛去找雲雲,卻沒見人。李建國一人在家做飯,他抬頭看了看葉飛,沒作什麼理會,仍回到廚房將碗勺碰得叮當作響。葉飛跟上去問雲雲去哪兒了,李建國回答不知道。葉飛有點不自在,呆立了一會兒說:“李叔叔,雲雲回來你告訴她,我在家等著她!”
廚房仍是叮當聲,葉飛走了出來,很尷尬,也很無奈。
葉飛心裏有點不踏實,自去沙梁上班,再沒和雲雲相見,也沒她的音訊。他不知是怎麼了,點了根煙,騎上自行車回到家中。
天漸漸黑了,還不見雲雲的影子。葉飛吃過晚飯,坐不住了,又騎上自行車來雲雲家找。
雲雲仍舊不在,李建國仍回答不知道,神情依然冷漠得令人寒栗。
葉飛軟塌塌地出了門,推上自行車沿路獨個兒朝前走。他心裏很亂,甚至有點苦悶沮喪,他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大街上人群車流來來往往,他就一個人走著,越走越覺得心煩意亂。
其實,雲雲就在他後麵,一直注視著他。自從葉飛去了沙梁,她成天覺得心裏慌,班組師傅的訓斥更使她丟三落四。她想葉飛,但更多的是憂慮,她覺得整個世界殘酷得如一把尖刀。她以為四年的癡情能喚回一個美滿的相守,沒想現實與想象有著很大的距離,一切是那麼無力,那麼地摸不著邊。她有點怯了,過早經曆家庭的不幸,過多的貧困,已使她的心失去了韌勁。她不願踏在原地,她同樣需要美好,需要和別人一樣的東西。她覺得女人天生是菜籽命,撒到好土出好苗,撒到瘦土出瘦苗。可自己呢?眼前呢?一切顯得那麼遙不可及。
下班回來,父親告訴她飛子來過了,她的心頓時慌了起來。這些日子,她在努力讓自己忘記飛子,努力讓自己下決心告別過去的一切。可一聽飛子來找她,飛子的身影就越來越強烈地占據她的整個心房。她坐不住了,耳朵在搜尋著門的響動。她盼飛子來找她,又怕飛子的到來會動搖她的決心。可她實在無法躲開浮現在腦海中飛子的眼睛,那雙打小就熟悉的眼睛。她默默地坐在梳妝台前,精心地打扮著自己。
到了葉飛家樓下,她的腳步又挪不動了,熟悉的路線今天卻怎麼也邁不開腳。她躲在角落裏,一次次將目光定格在飛子的窗戶上,一次次鼓勵自己的腳步,可腳步似有千斤,怎麼也抬不起來。就在這痛苦的煎熬中,她看見飛子出來了,心忽地加速了跳動。就在她幾乎要衝過去的同時,飛子上了自行車。
她急忙悄悄地跟在後麵,她看見飛子進了自己的家,看見飛子出了自己的家,看見飛子狠命吸煙的樣了。她的心碎了。終於,她走了過去,兩人久久地相擁……
一切仿佛都沒有發生,一切又開始繼續。雲雲沒法阻擋對葉飛的依戀,複雜的感情化作相思的淚水湧出眼眶。
葉飛也感覺有些傷感,喉嚨像卡了根魚刺。他拍拍雲雲的肩說:“好了,別哭了。”雲雲沒動,仍伏在葉飛胸前輕輕地抽泣。葉飛雙手捧起雲雲的臉,兩人含情地相視了一會兒,雲雲撲哧一聲笑了,又竄進葉飛懷中,像隻白兔。
許久,雲雲才仰起頭來說:“飛子,我真的好想你。”
葉飛深有同感地說:“我也想你。雲雲,你也許很難想象,在沙梁那個如牢一般的小所裏,我幾乎是度日如年呀。他們十天半月都不來一次,我就一個人待著,那種寂寞是可想而知的。白天還算好打發,可以到村舍裏去遛一遛,尤其到了晚上,我實在難以承受那種無邊無際的孤獨。半夜裏猛然醒來,我就再也睡不住,就想你,想你小的時候,我們一塊兒上學下學,想你給予我的一切溫柔……”
雲雲說:“飛子,你說,相愛為什麼這麼苦呢?我苦苦地等了你四年,好不容易等你回來了,可又被分開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我們的盡頭。飛子,你調吧,想辦法調到沙洲來,調回來我們就結婚。”
葉飛何嘗不想調回沙洲?何嘗不想同雲雲在一起?可是他知道調動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自父親從局長的位子上退下來之後,他已不是昔日的葉飛了,頂替了父親位子的胡紅國也不再是那個唯唯諾諾的胡副局長了。上次胡紅國到小所裏來視察工作,他像以往一樣熱情地管他叫胡叔叔,未料熱臉對了個冷屁股,當著那麼多人的麵,胡紅國理都不理他一下,搞得他滿麵通紅。到後來飯桌上敬酒的時候,他叫了一聲胡局長,胡紅國才勉勉強強應了一聲。
這事兒雖然過去了,但留給葉飛的印象卻是非常深刻的。人他媽的怎麼是這個德行?過去胡紅國當辦公室主任那會兒,在他父親葉局長麵前就像一條哈巴狗,讓人看著都肉麻,現在當了局長,竟像換了個人似的,這真是“子係中山狼,得誌更張狂”。麵對這樣一個得誌小人,要想從基層小所調到沙洲,你首先必須要把自己變成一條哈巴狗,像當年的他一樣,這或許有所指望,否則,你就別想回城。他雖然還不清楚胡紅國把他分到小所裏來的真正原因,但他卻從父母的表情中看出,他們兩家肯定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如果真的是這樣,他就在胡紅國的手裏死定了。
一次,王援朝跟他提起了這樁事,就感歎道:“你爸是個好人啦,可就是太直了。”
葉飛問他爸是不是得罪了胡紅國?
王援朝就含糊其辭地說:“我一直在基層待著,有些事兒我也不清楚。不過,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你要想改變一下你的處境,調到沙洲去,該上的香還得上,該拜的佛還得拜。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送小禮辦小事,送大禮辦大事,不送禮難辦事,禮數到了,事兒也就解決了。”
事後,葉飛想了很久,覺得王援朝說的很有道理,但是讓他去做又覺得十分困難。人往往就是這樣,明明知道該怎麼做,卻又無法去那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