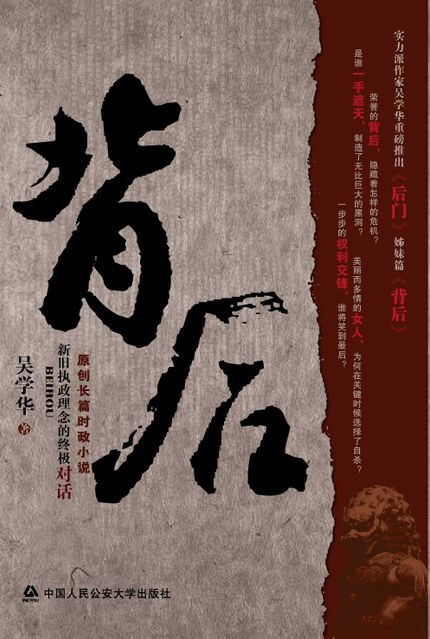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第4章
由於昨天晚上的及時處理,鑫達公司職工的情緒穩定下來,死者的家屬也表示聽候政府的處理,一夜沒合眼的金琳喘過氣來後。回到了縣委,她對馬超興說:“馬縣長,鑫達公司的事現在一定要及時處理,不然,還會出事。”
馬超興心事重重,趙德凱出事後,縣委縣政府的兩套領導班子都垮了,他和潘武偉是是幾個月前從南水市調到源頭縣來的。在南水市,他是經貿委主任。來到源頭縣,首先碰到的是鑫達公司幾十名職工中毒與死亡的善後處理問題,兩個人的工作風格幾乎一致,處理了不少棘手的問題。
潘武偉調走後,本想大幹一番事業的馬超興,被接踵而來的問題搞得筋疲力盡。雖說上麵很快派來了金琳,可兩人的工作搭不到一塊去。他從心底裏瞧不起金琳,認為金琳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依靠她母親程春愛。他的工作作風也與金琳完全不同,金琳辦事小心,處處以求穩妥,事事得先向母親彙報,好像不是她在當縣委書記,反而是她母親程春愛。
對鑫達公司的態度,馬超興同潘武偉的態度完全是一樣的,主張不與查奇打疲勞戰,立即拍賣鑫達公司。但是,在拍賣鑫達的時候,他與金琳卻發生了分歧。金琳主張在評估鑫達公司的固定資產原值後,再在此基礎上確定下浮基數,就是說低於鑫達公司資產原價的數不能超過百分之二十,說是要保障外商的利益。畢竟這是一起涉外事件,一定要慎重處理,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馬超興主張在拍賣前,不能定下這個基數。隻要有人買,出多少錢都可以賣。事情都過去幾個月了,那個外資老板遲遲不露麵,等於自動放棄和政府的協調機會,現在政府這麼做,完全有理由說得過去。管它是不是外資企業,賣了再說,按照國際有關法則,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政府部門有權單方麵處理。
由於兩人的分歧,鑫達公司遲遲不能賣出去,查奇正是抓住了這一點,遲遲不肯露麵。這個時候,金琳才慌張起來,感到這個事不能再拖了。馬超興知道金琳急了,於是說:“幹脆快刀斬亂麻,處理就處理掉!”
金琳知道自己比不得馬超興,上麵有個位高權重的父親,如果她稍有差池,潘武偉就是她的榜樣:“馬縣長,在處理鑫達公司的問題上,也許我的做法錯了,但現在不是討論誰對誰錯的時候,這兩天市裏有領導要下來,我們總得有個具體措施對他們交待。”
馬超興見金琳這麼說,略一思索說:“我們這裏情況可比市裏好多了,金書記,你說現在該怎麼辦呢?”
金琳說:“我們兩人商量一下,你先把你的想法說說看。”
馬超興不再客氣:“首先,中毒的工人繼續住院治療,醫藥費暫由政府墊付,安撫死者家屬的費用,也可以暫時由政府墊付,到時候再從拍賣鑫達公司的款項中抽回來;第二,立即組織有關人員對鑫達公司拍賣,迫使查奇出麵。第三,由政府組織公司職工向縣勞動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必要時,向法院提出起訴,追究查奇的刑事責任。”
金琳說:“好,就按你的三條辦,這些工作你馬上組織有關人員去落實實施。”
馬超興點了點頭,想起另外一件事:“金書記,南星製藥廠的事也很麻煩啊!”
南星製藥廠是源頭縣的一家國有企業,興建於70年代中期,2003年關門停產,到2005年3月由一個姓戴的外資老板承包經營,生產不到兩年,虧損400多萬元,外資老板見勢不妙,丟下一個爛攤子跑了。現在全廠400多職工都成了沒娘的孤兒,每人每月由政府發160元的生活費。被拖欠的職工工資高達幾十萬,這些錢,都成了一筆死帳,將由政府來買單。現在,發了快一年的生活費了,縣政府也覺得不是條好路,政府不能長期地發生活費下去,況且,生活費的發放也很不合理。生活困難的靠100多元錢根本不能生活,而有的人卻開著小車來領生活費,鮮明的反差說明了生活費的發放有許多不妥之處。
但是怎麼辦呢?國家又沒有明確的法規,自己製定一套吧,又怕出什麼亂子。金琳眉頭緊鎖,無奈地說:“是很麻煩啊!但我們能怎麼辦呢?我看還是先拖一拖,去請示市委,看吳書記能不能想個好法子出來。”
馬超興說:“縣企改辦也要想辦法,我這就去找企改辦鄧主任,要他們好好相想辦法。隻要可實施,就同時解決南星製藥廠的問題。”
馬超興剛走,金琳的手機就響了,她一看丈夫楊兵打來的,摁下了接聽鍵,裏麵傳來很急的聲音:“金琳,小娟病了,發燒39度,你是不是回來一下?”
金琳有些惱火:“你也不看是什麼時候,我現在有空嗎?縣裏的事這麼多,昨晚一夜都沒睡覺,要不你帶小娟去醫院看一下,過兩天有空的時候,我再回去。”
楊兵耐心說:“金琳,小娟哭著在要媽媽呢。”
金琳不耐煩地說:“你這個爸爸怎麼做的?告訴小娟,說媽媽沒空。”
“那……”
金琳掛了電話,流下了兩行淚水,心裏卻為女兒的病擔心,可是眼下又有什麼辦法呢?縣裏除了這麼多事,想走也走不開呀!心疼女兒的同時,又惱恨著丈夫楊兵。楊兵雖說畢業於名牌大學,在市裏一家事業單位上班,可混到現在還是一個副科級幹部,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不夠圓滑,不懂得怎麼做人。套句時髦的話說,就是不懂得遊戲規則。
她隻是一個財經類學院的專科生,作為一個女人,30多歲就當上了縣委書記,算是不錯的了,這裏麵有她母親的汗水和功勞。
有時候,她確實感到了深深的滿足,但滿足的背後,又是深深的失落。她怕回家,怕和丈夫躺在那張大床上。丈夫的年紀並不大,才40歲不到,按道理正值男人英姿勃發的時候,不知道怎麼竟然早泄,夫妻間的性生活每次都不盡人意。去了好幾次醫院,藥也吃了不少,可一道關鍵時刻,就是出問題。
她雖算不上是年輕漂亮,但也不醜,有著職業女性特有的氣質和風韻,本可以象別的女人那樣追逐時尚,但作為一個縣委書記,她的衣著不能太華麗,她的舉止也必須十分端莊。一次開會時聽了吳永平的批評後,她處處在約束自己,時時在掩飾自己,掩飾自己的感情,掩飾自己的生活。有時她真想丟掉頭上的烏紗帽,盡情地表現自己,自由自在實實在在地生活。可是她不能,因為她是縣委書記。
想到這裏,她無奈地歎了口氣。
×××××××××××××××××××××××××××××××××××××××
卻說朱永林要劉剛和小宋去大橋那邊采集標本,交代說這事需暗中進行,不要打草驚蛇。他們兩人來到橋頭,見原先在這裏維持次序的公安幹警都已經離開了,倒是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堵著,不讓人靠近。兩人想了一下,最後小宋仗著自己的水性,遊泳到倒塌的地方,采集回來了一些鋼筋和水泥的樣本。
劉剛回到家裏,已是傍晚時分了,妻子苗雨正在替女兒輔導功課。苗雨一見丈夫滿身泥水地進了家門,吃驚地問:“怎麼了你,掉到水裏了?”
劉剛笑了笑:“是掉進水裏了,不過是故意掉下去的。”
苗雨不知詳情,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劉剛放下手中的東西,一頭衝進浴室,說:“先別問了,快去給我拿衣服。”
苗雨見丈夫放在地上的東西是一些碎水泥塊、爛鋼筋,更加奇怪:“你怎麼拾起這些東西來了。”
劉剛揶揄地說:“是呀,現在經濟不好,咱家缺錢花,隻有靠撿破爛添補了。”見苗雨還愣在那裏,接著說:“你怎麼還不去拿衣服呀?”
苗雨滿臉霧水地走進臥室替劉剛拿來了衣服。劉剛洗完澡換了衣服,剛要說話,卻聽見門外響起了聲音:“哥、嫂,在家嗎?”
劉剛一聽就知道是妹妹劉瑤來了。苗雨趕緊去開門,劉瑤進了房,叫道:“哥,今天你到哪裏去了,我打了好幾次電話到你辦公室,都沒有人接。”
她的右手用繃帶綁著吊在胸前,醫院的床位緊張,她主動將自己的床位讓了出來,回到學校的單人宿舍調養。
苗雨指著地上的破爛東西說:“你看看就知道了,你哥不在研究所好好上班,去撿這些東西回來。”
劉瑤也不明白,問:“哥,你這是幹什麼啊?”
劉剛這才娓娓道出了事情的原由,苗雨卻擔心的說:“我看這可不是一件好差事。”
劉剛問:“你這話怎麼說?”
苗雨說:“這不是明擺著嗎?大橋垮了,肯定有黑幕,如果有人偏要去掀開這張黑幕,另外一些人不是恨死你了嗎? 以前的那個王書記就是榜樣。”
劉剛說:“這個我不怕,反正上麵有吳書記和朱書記撐著。”
劉瑤說:“哥,我支持你,自古邪不勝正,怕什麼?”
正說著,傳來了敲門聲,隨之,又傳來了敲門聲:“劉工程師在家嗎?”
劉剛忙去開門,一看,是市委書記吳永平,頓時愣住了,他實在想不到吳永平會來到他家裏。
原來吳永平吃過晚飯後,獨自在市委大院裏溜達,突然想起劉剛寄到市委的那封信。在此之前,他也了解到劉剛曾經因為那封信的問題,被有關部門帶走,後經設計院領導保釋,才放回家的。信肯定是寄到了市委,至於程春愛有沒有收到,那是另一回事。劉剛隻是區區一個工程師,他有什麼膽量去觸怒市裏的領導呢?
想到這裏,他便叫司機開車來到設計院,問了劉剛的住處,想找劉剛聊一聊,看對方對大橋質量的問題,知道多少。可惜他並沒有察覺,當他的車離開市委大院後,後麵跟著一輛麵包車,一直尾隨著他的車子進了設計院。
吳永平笑著說:“怎麼?不歡迎嗎?”
劉剛回過神來,忙說:“哪裏,哪裏,吳書記,請坐,請坐。”
吳永平進了屋一看,是間普通的二室一廳套房,屋內的燈光有些昏暗,擺設的家具也較陳舊,看得出房子主人的清貧。
劉瑤對走進屋來的吳永平說:“吳書記,還認識我嗎?”
吳永平這才看到屋內的劉瑤和苗雨,忙說:“認識,怎麼不認識?劉老師,我還欠你一個問題呢?怎麼,傷好了嗎?出院了?”
劉瑤說:“不礙事的,早出院了。在家裏調養也一樣。”
苗雨怕劉瑤說話不知高低,忙說:“瑤瑤,你坐吧,我去給吳書記倒茶。”
吳永平看著苗雨說:“這就是劉工的愛人吧?”
苗雨忙點了點頭說:“吳書記,您坐,您坐,您看我們家屋子小,也沒有個好地方讓您坐。”
吳永平見她說話得體,笑了笑說:“你原來在哪個單位?”
苗雨歎了一口氣說:“原來在市毛紡織廠,後來調到南水絲綢廠,這不,還沒有上過一天班,原來每月還有一點生活費可以拿,現在連生活費也沒有了,人到中年下崗真是難啊。”
吳永平知道市毛紡織廠也是個困難企業,倒閉好幾年了。於是同情地說:“是啊!都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讓你們吃苦了。”
劉剛說:“怎麼能怪你呢?那時候你還沒來呢!再說這經濟改革,有些企業該倒閉的還是得倒閉。”
吳永平在劉瑤的身邊坐了下來,接過苗雨端來的茶水,問:“劉工,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劉剛說:“我看到了事故現場,對大橋的情況進行了詳細檢查,拿回來一些樣品,初步看了,大橋主體鋼材嚴重不合格,水泥也有不符合標號的,其他方麵,施工過程也存在問題。當然,具體結論要待化驗結果出來後才能確定。”
吳永平點頭說:“劉工,你帶上這些東西去省裏,找相關的單位化驗一下,一定要拿到有力的證據,我們好開展下一步的工作。車子我會為你安排的,最好馬上就走!”
劉剛提起那一袋東西說:“好的,吳書記,我馬上走。”
苗雨看著他們兩個人說:“剛回來,連飯都不吃就走呀?”
吳永平有些歉意地說:“車上有些東西,可以給他在路上吃。等問題處理好了,我請你們一家好好吃一餐!”
兩人起身,正準備離去,劉瑤起身笑著說:“吳書記,那我呢,不請我嗎?”
吳永平笑了笑:“當然包括你,我還欠你一個問題的答案呢!”
他說完,和劉剛一同急急出了門,上車離開了設計院。
那輛麵包車從樹影中緩緩駛出來,車上一個消瘦的男人正在打電話:“……老板,吳書記和設計院的一個人一同上了車,我們怎麼辦?”
手機裏傳來低沉的聲音,“……以前好像有個設計院的家夥,給市委寫過信,先弄清楚是不是同一個人……記著,不要急著動手……”
×××××××××××××××××××××××××××××××××××××××
在車上,吳永平給朱永林打了一個電話,要朱永林臨時抽調一個人,和劉剛一同去省裏,針對采集的樣品進行化驗。
掛上電話後,他想起去劉剛家中的目的,問道:“你怎麼想到要給市委寫信反應情況呢?”
劉剛憤憤地說:“實在看不過去了,他們是在拿老百姓的生命當兒戲。那封信寫出後,如石沉大海,我又找到幾個大橋的集資人,對他們說了。他們去找過市領導,可也沒有什麼用。在你沒有來之前,整個南水都是他們的天下,想怎麼搞就怎麼搞!”
吳永平問:“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劉剛笑了一下:“還能是什麼人?就是拿著國家的工資,掌握著人民賦予的權利,被稱為公仆的人唄!唉,還真應了那句話呀!”
吳永平問:“什麼話?”
劉剛說:“趙孟一家人,公仆忘姓公;親戚與裙帶,拉幫結弟兄;利用手中權,有無互相通;你給我封官,我把錢你用;吃喝嫖賭舞,朝暮同輕鬆;民眾呼聲裏,不辨西與東;黨紀和國法,當我耳邊風;市縣各部門,全是大蛀蟲;每年江兩岸,任隨大水衝;高樓平地起,下麵全掏空;財政十幾億,鑽個大窟窿;南水經濟好,全入口袋中……”
他頓了一下,接著說,“後麵還有一些,我不記得了。是一個退休老教師用手機發給朋友的,那個信息被轉來轉去,後來有關部門查到他的頭上,60多歲的人了,還被關了幾個月,出來後連氣帶病,沒有多久就死了。”
吳永平默默地望著窗外,沒有說話,細細品位著劉剛說的這首順口溜。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隻知道利用手中的職權,做著損公肥私的事情,卻不知老百姓已經看在眼裏。區區一首順口溜,已經將南水官場中的醜態描繪得淋漓盡致。可憐的老教師,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他的心情變得異常沉重起來,也終於明白,他所麵對的,並不是一兩個貪官,而是一張由利益關係結成的大網。
×××××××××××××××××××××××××××××××××××××××
孟楚庭穿著睡衣躺在寬大的沙發上,他根本沒有心思看電視,腦海中盡是想著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雖然有市新聞辦的人周旋著,但是這起特大的事故,還是以最快的速度傳播了出去,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市裏有不少流言蜚語傳到了他耳中,說省委領導來了,因跨海大橋倒塌之事,嚴厲地批評了孟楚庭,甚至要撤他的職。又有傳言說,吳永平組織的事故調查委員會,主要是針對他和趙衛國的。更有甚者,說那兩筆寄自南水的贓款是他孟楚庭寄的,這不明擺著分化他和趙衛國的那層關係嗎?
他心裏窩著火,可是氣歸氣,隻能窩在心裏,不能表露出來。昨天到吳永平的辦公室後,兩個人針對如今南水目前的問題和形勢,談了一些各自的想法,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他思索了良久,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處理好和吳永平的工作關係。
昨天省委書記張明華看了事故現場後,和吳永平單獨談了一陣子,雖然沒有人知道他們談的是什麼內容,可就是再笨的人也猜得出來,張明華要吳永平下來的目的是什麼。按上麵的意思,南水的蓋子遲早是要揭開的。
今天一早趙衛國明明離開了南水,卻在半路上殺了一個回馬槍,這內中的含義,用膝蓋想一下都會明白。
他想起了趙衛國臨上車前,拉著他說的那幾句話,似乎是在暗示著什麼。他略一思索,拿出手機,撥通了趙衛國的手機:“喂,趙書記嗎?是我,是楚庭啊。趙書記,聽說你舍不得南水,這是好事,是好事呀!當初你離開南水的時候,我可是真舍不得。我們搭檔那麼久,在工作上是相互配合的……趙書記,前段時間處理的那幾個人,都是你一手提拔的呀!都說人走茶涼,我也是沒有辦法……姓吳的那麼做,都是衝著你和我來的呀。我們南水的改革成果,難道就因為一座橋而全盤否定嗎?趙書記,我心裏不服呀……你不要勸我了,你說,全國哪裏沒有重大事故發生,但這能否定全國的大好形勢嗎?現在我們這些辛辛苦苦的老黃牛,反倒一個個成了罪人了。趙書記,你不清楚,外麵的傳聞說得多難聽啊!趙書記,你別激動,別激動,功過是非自有人們評說,我們一身正氣也不怕別人胡說,可是我這心裏委屈啊。趙書記,吳永平到南水才半年多,就把南水搞得一團烏煙瘴氣,再這樣下去,南水市會毀在他手裏的。”
對於孟楚庭的心理,趙衛國不是不清楚,他聽了這樣的話,血壓突然竄高了,但他表現得還很冷靜,在電話裏一再強調:“不管別人說什麼,你要做的,就是配合好他的工作。”
除了這些話之外,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了。和孟楚庭搭檔的那幾年,關係確實很融洽,每個人主持各自的工作,很少有矛盾發生。在大問題上,兩人也是事先商量好,統一思想後開會施行。南水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一條繩上的蚱蜢。
孟楚庭聽了趙衛國說的話後,呐呐地又說了一陣,就把電話掛了。
他的妻子華姿走過來,說道:“楚庭,你這樣也不是事呀?姓吳的要查,就讓他查去,反正南水又不是……”
孟楚庭生氣地吼道:“你懂什麼?就知道給我添麻煩!”
華姿驚呆了,自他們結婚來,丈夫還從來沒有在她麵前發過這麼大的火,她愣了一下,低聲抽泣道:“我給你添什麼麻煩了?你受了別人的氣,就往我身上撒,算什麼英雄。外麵傳聞我也聽了不少,論年紀,你比他大那麼多,論資曆,他吳永平算哪根蔥?你堂堂一個市長,為什麼要怕他?”
孟楚庭也覺得自己失態了,放低了聲音說:“華姿,這段時間我心裏的壓力很大,很多事情你都不懂的!”
華姿說:“我當然不懂,那是你們男人的事,人家趙書記都不急,你急什麼?”
孟楚庭說:“我能和他比嗎?他不在南水,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主要責任人是我!”
華姿也坐了下來,低聲說:“楚庭,我也知道你心裏難受,但這也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人家怎麼說你,讓他們說去,天塌下來不是你一個人去撐。再說他不也在南水嗎?”
孟楚庭皺著眉頭說:“以後我的事你少管,叫華意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這樣下去,終有一天要出事的。”
外麵傳來了門鈴聲,華姿打開門一看是華意,說曹操,曹操就到。華意叫了聲姐,見孟楚庭躺在那裏,叫了聲姐夫。
孟楚庭對這小舅子沒什麼好感,整天無所事事像個花花公子,見華意叫他,嘴裏也隻是“嗯”了一聲。孟楚庭看了看表說:“你們聊,我去院裏走走!”
說完後,看也不看華意一眼,便起身慢慢踱著走了出去。來到院子裏,看著那棵枝葉茂盛的海棠樹,走上前扶著樹幹,輕輕歎了一口氣。
這棵海棠樹是他當年調入市政府任副市長時,舉家搬進市政府後院這棟獨門獨院的兩層樓後栽下的,這一住就是上10年,他由副市長升為市長。樹大了,人卻老了。
他和吳永平的市委宿舍相距並沒有多遠,吳永平上任以來,到他這裏上門拜訪過兩次,而他卻沒有去過吳永平的宿舍。
以前趙衛國當書記的時候,南水的經濟確實輝煌過一陣子,市委市政府也多次開會討論新建辦公大樓的事情。縱觀國內的一些城市,有些經濟不怎麼樣的城市,將辦公大樓修建得如美國白宮一樣的奢華。雖然引來眾多的非議,但人總在新的地方辦公了。
最終敲定的時候,都是因為趙衛國的一句話,將事情擱置了下來。到今天,市委市政府兩套領導班子,仍在一個地方的兩棟樓裏辦公。
妻子多次勸他搬出這個大院,可他似乎對這棟小樓有了感情,執意住在這裏。當然,他有他的想法,住在這裏有多少好處,是外人無法得知的。
幾十年的官場沉浮,讓他感到心力疲憊,特別是這半年來,整個人顯得很憔悴,蒼老了不少。究竟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隻有他心裏清楚了。
自從上麵調吳永平來市裏當書記後,他就知道南水的蓋子遲早要揭開,隻是時間的問題。跨江大橋的倒塌,加速了南水蓋子揭開的步伐。一旦蓋子被揭開,其震撼程度不亞於一場8級以上的大地震,結果是無法想象的。
華意見孟楚庭走了出去,才低聲說:“姐,姐夫好像不高興呢!”
華姿說:“現在南水出了這麼大的事,姓吳的抓著不放,他能高興得起來嗎?”
華意說:“為什麼?”
華姿解釋說:“還不是為了那些事,聽到許多流言蜚語,氣壞了。”
華意低聲說:“姐,現在南水可是人人自危呀。”
華姿緊張地問:“你也聽到了什麼嗎?”
華意說:“當然聽到了,很多版本的呢,反正對姐夫不利。人家趙書記現在成了人大主任,位高權重,再說已經離開南水了,就是負責,主要責任不在他的手上。目前處境最難的就是姐夫了,不怕一萬,隻怕萬一,就怕有人找他做替罪羊。”
華姿不無擔心地說:“是呀,現在吳永平正大刀闊斧地查這查那,和你姐夫對著幹,還有省裏的人在背後撐腰,我怕到時連趙書記都落井下石呀!”
華意冷笑著:“若是別人,我可不敢打包票,可是他,我認為不會,不說姐夫和他的關係怎麼樣,就說他老婆收了那200萬的事,那是……”
華姿打斷了華意的話,說:“噓!不要說了,給你姐夫聽到不好,那種事他可不知道的,你托我辦的事,我已跟有關部門打過招呼了,蔣仁的問題不久就可以解決。”
“姐,你真好。”他接著說,“明天我那個娛樂城就開張了,姐,你可千萬要來,順便把雷市長和徐市長他們的老婆都叫來。”
“一定,一定。”華姿笑著說。
“那我走了。”華意說。
見華意要走,華姿又說:“你要留意有關你姐夫的傳聞,聽到什麼,一定要來告訴我。如今的小道消息比正規文件來得還要快得多。”
華意答應著走了。華姿來到院子裏,見孟楚庭仍扶著那棵海棠樹,忙上前攙著他,低聲道:“楚庭,事情臨到頭上來了,擔心也沒用,我知道你就怕趙書記落井下石,把責任都推給你,放心吧,沒事的!”
孟楚庭歪過頭望著妻子,見那張他熟悉的臉上,充滿著高深莫測的表情,他愣了一下,問道:“你怎麼知道沒事?”
華姿微笑著:“我是你老婆,我說的話你還不信呀,我打包票,他沒事你就沒事,要不然,大家都有事,南水大大小小那麼多幹部,他吳永平動得過來嗎?自古還有法不責眾的道理呢?要是南水的蓋子揭開了,在國內來說,這可是大案,傳出去省裏也臉上無光不是?到時候誰也討不著好,吳永平是明白人,他不是不知道這內中的厲害關係,他那麼做,也是做做樣子,處理幾個人,是給上麵看的。”
老婆的這番話,猶如一針強心劑注入了孟楚庭的動脈,他頓時精神起來,深深吸了一口氣,望著頭頂上的枝葉,說道:“這海棠果,我已經吃了好幾年了,就算別人要摘,也得我同意呀!”
回到屋內,他走進了兩個多月沒有進去過的書房,提起毛筆,飽蘸了墨汁,寫了一個兩尺見寬的“忍”字。
他從小就喜歡書法,隻是由於時間有限,而沒有經常練習。當上副市長後,在一次文藝工作者會議上,被逼著寫了幾個字,不料當場有人叫好,說他的字銀鉤鐵劃,卻不乏剛柔相濟,具有魏晉之風,雖國內書法大家也不過如此。自那以後,向他來求字的人絡繹不絕,剛開始,他也隻是象征性的收個幾百塊錢的潤筆費,到如今,他的字已經上漲到每個字一到兩萬。
兩個多月沒有進書房,也就是說,已經有兩個多月沒有人來找他寫字了。
他望著這個“忍”字,嘴角慢慢浮現出一絲難得的笑意。
×××××××××××××××××××××××××××××××××××××××
聽了孟楚庭打來的電話,趙衛國當時血壓升高,人差點暈了過去。所幸秘書在旁邊,喂他吃了幾粒降壓藥,才逐漸平緩下來。他後悔沒聽張明華的話回省城,留在南水有什麼用呢?除了麵對流言蜚語,還能得到什麼呢?吳永平他們的做法是無可指責的,大橋垮了,當然要進行調查,要進行處理,但傳出來這麼多的流言蜚語,難道就與他沒有關係嗎?他感覺吳永平又在玩一張牌,如同幾個月前在玩南水絲綢廠那張牌一樣,這次他在玩大橋這張牌。口口聲聲說不能否定南水十幾年改革的成績,但在具體做法上卻在一點一點地否定南水的改革成果。
他趙衛國時代所創造的輝煌,像一座巍峨的豐碑,吳永平不能跨越,隻有打碎這塊豐碑,才能從豐碑的廢墟上爬過去。趙衛國自信地想,這塊豐碑能被打碎嗎?絕對不能,他必須想辦法讓吳永平在這塊豐碑麵前做一個心懷敬仰的瞻仰者。吳永平繼任南水市委書記後又做了哪些具體的工作呢?幾乎什麼也沒有,每天就知道廉政建設,查這查那,得了一個“整人書記”的外號。這半年來,南水的國民生產總值比自己在位時降低了30%,南水絲綢廠和上海方麵的合作失敗了,全市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人數在增加,各種社會矛盾、經濟矛盾在加劇,種種問題層出不窮。
孟楚庭來電話之前,南水市下屬的兩個縣級市,天馬市和桃湖市的市委書記相繼來看望他,說是來拜訪趙書記,請趙書記多指導指導工作。桃湖市委書記鄭成海臨走時提醒他,要警惕有人在大橋和南水絲綢廠的問題上做別有用心的文章。
這兩個市委書記都是他一手培養的,對他可以說是忠心耿耿。在這些人的麵前,他才感到了自己的威嚴,感到了自己的權力,感到了他在南水不可動搖的地位。
想到這裏,趙衛國才略感欣慰,精神重新振作起來。他不能倒下,他也不會倒下,這棵紮根在南水極深的老樹,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推倒的。
×××××××××××××××××××××××××××××××××××××××
金琳一早從源頭縣來到南水市,要向市裏報告源頭的工作情況,和母親程春愛通過電話後,得知趙衛國留在了湖濱賓館,她想起能夠當上源頭縣委書記,是趙書記推薦的。看看時間還早,便在街上買了一點東西,要司機直奔湖濱賓館。
在南水這場即將到來的風暴中,她必須保持自己的中間立場,才不被卷入,這也是母親在電話中要她去看望趙衛國的意思。
來到湖濱賓館,打聽到趙衛國住的房間後,到房間前輕輕敲了敲門,一個秘書模樣的男人開了門,她連忙說:“你好,我是源頭縣委書記金琳,是來看望趙書記的。”
進屋後,她見趙衛國躺在沙發上,樣子有些憔悴,忙向他畢恭畢敬地行彎了一下腰,上前握住他的手說:“趙書記,您好!”
“哦,是小金呀,這麼一大早來看我,有什麼事嗎?”趙衛國指著身旁的沙發招呼金琳坐下。站在旁邊的秘書馬上給金琳倒了茶水。
金琳坐了下來,拘謹地說:“我今天到市裏來彙報工作,知道趙書記在這裏,就過來看看。”
趙衛國點了點頭,笑著說:“小金,你在源頭縣工作得還順利吧?”
金琳說:“趙書記,不瞞您說,光一個鑫達公司就弄得我筋疲力盡,還有南星製藥廠的事。”
趙衛國說:“你怎麼就不能果斷地處理好那些事呢?小金,當初我推薦你去源頭縣,可是看中了你的工作能力,給你一個自我體現的機會,你可不要辜負我的期望啊!”
金琳對趙衛國是心存感激的,沒有趙衛國,就沒有她今天這個源頭縣委書記。聽了趙衛國的話,她委屈地說:“趙書記,這事本該早處理好了,可是馬縣長和我的工作分歧很大,使事情拖到今天也沒解決。
趙衛國表情陰鬱下來:“工作有分歧是無法避免的,那就要看你怎麼去處理了?”
金琳歎了口氣:“我主要考慮班子的團結問題,如果兩人鬧意見,那就什麼工作都做不成了。”
趙衛國揮了揮手:“原則還是要講的,不能和稀泥。你們對鑫達公司職工中毒事件處理的方案我看過了,你們可以按相關的方法去做,但在具體做法上,要講究實際的方式與方法,畢竟是一起涉外事件,要考慮到對其他外資、外商的負麵影響,可不能整死了一條魚,把其他魚都嚇跑了。”
金琳點了點頭:“趙書記,您說得很對,我就是在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做得更好一些。”見趙衛國心情不好,知道他還在為大橋的事而煩惱,於是說:“趙書記,我知道您到南水看了這裏發生的事,心情不好。不要太難過,責任不是您一個人的,您的功勞,您的成績,您對南水市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
趙衛國歎了口氣:“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麼想就好了。可是我擔心……”見自己說遠了,忙轉換話題說:“小金,你工作忙,忙你的事去吧!”
金琳知道他有些話不便說,隻得起身告辭:“趙書記,那我就走了,改天我還會來看您的。”
她出了趙衛國的房間,離開了湖濱賓館,要司機開車在前麵的路口等她,她想走一走。
她沿著街道向前走去,一路上仔細品味著剛才聽到的那些話,看樣子,趙衛國對她的工作好像不太滿意,最起碼在處理鑫達公司的問題上,似乎在告訴她不要輕舉妄動。她一邊走,一邊想著,該如何向吳永平彙報鑫達公司和南星製藥廠的事,順便聽聽吳永平的想法,如何開展下一步的工作。剛走過一處拐角,聽到背後傳來幾聲小車的喇叭聲,一輛黑色的奔馳在她的身邊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一個人,對她喊叫聲:“金琳!”
金琳轉身一看,隻見一個高大英俊的男人站在自己麵前,微笑地望著她。她愣住了,驚訝地望著對方良久,認出是一位失去聯係很久的故人,叫道:“呀!常明,怎麼是你?你怎麼在這裏?”
常明依舊微笑:“人生何處不相逢呢,金琳,我們好像有十幾年沒有見麵了吧?”
常明是她高中時的同學,那時這個帥氣十足的男孩深深地吸引著她。她暗戀著他,夢想著小說中男女主人公的浪漫情節在他們的身上重演,盡管那時班上有幾對公開的情侶,可由於母親的嚴厲管束,她不敢和男孩子過多的交往,更不敢公開戀愛,隻能偷偷地寫情書。高中畢業後,她考上了大學,他卻名落孫山。讀大學期間,他們還有書信來往,就在她大學快畢業的時候,他突然寫來了一封絕交信,之後便再也沒有信來。她畢業後回市裏工作,得知他已經與當地的一個女人結了婚,並去了北方做生意,一直都沒有回來,兩人也就失去了聯係。她知道他刻意的在躲她,便等他回來,一等就是好幾年。
後來她經母親介紹嫁給了老實巴交的楊兵,十幾年過去了,埋藏在她心底的那份情感已被歲月悄悄地淡化了。
現在的常明比過去多了一份成熟與穩健,更顯得有男人味了。穿著一身休閑西裝,梳著大背頭,一副成功男士的模樣。她從見到他的那一刻起,心裏感覺突然被什麼東西狠揪了一些下,回憶起中學時代偷偷寫情書的情景,還有那一頁頁紙張上的誓言,心中的那扇塵封已久的感情,突然被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衝開了。她的臉在發燒,心在跳,這是她這十多年來未曾出現過的事,她覺得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時代,憧憬著小說中的浪漫情節。
常明望著她說:“你和當年讀書的時候沒有什麼變化呀!眉毛是那眉毛,眼睛還是那眼睛,隻不過一頭披肩長發變成短發了……”
金琳想起了高中時候隱藏在心裏的那份情感,臉上立即一片緋紅,嗔道:“我都半老徐娘了,你還拿我開心?當我是10幾歲的小女孩麼?”
常明忙賠笑:“不敢,不敢,你如今是堂堂的縣委書記,縣太爺頭上動土,小民不敢!”
金琳詫異地問:“你怎麼知道我的情況?”
常明微笑著說:“早就聽人說了,源頭縣去了一個女書記!”
金琳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默默地望了常明一會,柔聲問:“常明,這些年你到哪裏去了,你……還好吧?”
常明的眼中掠過一抹不易察覺的神色,有些痛苦地說:“一言難盡啊,金琳,久別重逢,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你還沒吃飯吧,走!我們吃飯去。”
金琳看了看手表,見還有些時間,再說從源頭到南水,肚子也餓了,於是點了點頭,拿出手機打電話給前麵等她的司機,要那個司機直接去市政府,她晚一點再去。掛上電話,她上了常明的車子,來到一家湘菜館,兩人坐在一處靠窗的角落裏。
常明拿起菜單要金琳點,她拘泥了一下,隻點了一個剁辣椒蒸魚頭,以前和別人去吃湘菜,總有人點這道菜,說什麼紅通通的鋪了一層,兆頭好。
常明點了一個幹辣椒炒雞雜,一個油淋辣椒。他合上菜單,低聲說:“自從當年前吃過那一次你做的油淋辣椒後,我每到湘菜館必點這道菜,可怎麼吃都感覺不出你做的味道!”
金琳的心一動,不敢去看常明那有些憂鬱的眼神,忙將目光投向外麵,剛說出“為什麼”三個字,眼睛立刻模糊了。還記得那是高三上學期的時候,有一次她趁父母不在家,偷偷把他帶回家,當時家裏也沒有什麼菜,她就做了一個油淋辣椒。兩人就著那一個油淋辣椒的盤子,吃了個稀裏嘩啦,辣得直吐舌頭。想不到這麼多年,他還記得那道菜。
常明叫服務員上來幾支青島純生,他望著金琳,聲音有些沙啞地說:“中國自古講究門當戶對,我也是沒有辦法,那封信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仰頭喝下一大杯酒。
金琳見狀,也不客氣,連續喝了好幾杯。菜都沒有端上來,幾瓶酒就空了。
常明又叫服務員端上來幾支,放在旁邊,他痛苦地說道:“我知道你怪我寫那封信,怪我不和你聯係,可是你想過沒有,我為什麼要那麼做?”
金琳搖了搖頭。
常明苦笑著說:“我們兩個人的事,其實你母親早就知道,她為了不影響你考大學,才沒有對你說,她暗地警告我不要碰你。你應該知道,一旦惹火了你的母親,她隻要動一根小指頭,我們全家就不得安寧……”
金琳漸漸想起,那時候母親經常在她耳邊叨念著要努力讀書,少跟男孩子接觸什麼的。原來她和常明的事情,母親早就已經知曉了。中學時候談戀愛,確實早了一點,母親之所以容忍,是從長遠的利益考慮。
常明接著說:“她後來知道你上大學後我們還在通信,於是找到我家裏,給了我家裏3萬塊錢,要我盡快和別人結婚並且離開南水……”
金琳驚呆了,她怎麼都沒有想到,那一段純潔的戀情,就這樣毀在母親的手裏。
當他們離開餐館的時候,桌上的菜沒怎麼動,但桌下的酒瓶卻堆了一大堆。常明要開車送她,被她拒絕了。她也沒有叫縣裏來的車,而是直接打了一個的士,來到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