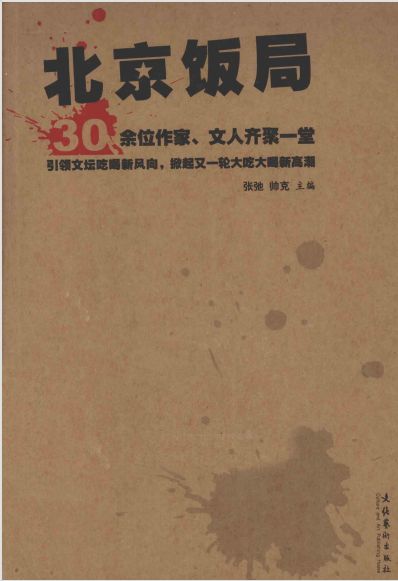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閉關
上海進入梅雨期,空氣很潮濕,我的筆記本軟遝遝的。又到了傍晚時分,我枯坐台燈下,麵對紙筆發呆。據說傍晚是各路神魔出來活動的時候,此時人心最容易惑亂。
在北京,此時多是赴酒局的時候,我總說“躲酒”,為此找各種理由去外地,但回想每次在北京赴酒局的路上,我的心裏還是很踏實的,有時還飽含期待,也就是說,對北京酒局,我骨子裏有一部分是喜歡的,我遠離北京,也是遠離那部分自我。
不是沒有想過在北京生抗。比如去年的這個時候吧,大約有一個月,我曾試圖在北京“”,關手機拔電話線不見朋友,但每到傍晚時分,心情便開始浮躁惑亂起來,我知道分別不同的幾撥朋友正在幾個不同的地方喝了起來。記得當時的想法是:就這麼浮躁著什麼都不幹,也不去喝!
但在家幹坐著實在難熬,我的抵抗方式就是大範圍遛彎。從我航天橋的家出來,一直奔東,經阜成門、白塔寺至西四往南奔西單,至長安街西單十字路口往西,經電報大樓、南禮士路至木樨地往北,至甘家口往西,至家,全程至少十公裏吧,反正我走的幾回都是兩個多小時。然而這樣完整或說完滿走下來的次數要遠低於我走著走著就岔到酒桌上的次數。
在北京遛彎我是邊遛邊進行思想鬥爭,在某些路口,鬥爭會尤為激烈。比如遛到西單十字路口,往西是奔家的方向,往南是奔宣武門,那是阿堅小招的巢穴,於是,往西還是往南便成為一個問題。……印象中我往南的次數要多於往西,而往南時我是這麼給自己做思想工作的:先到宣武門我們常喝酒的那幾家排檔,倘撞上他們了,算我命中該著,同時也給他們個小驚喜(又在以飯局明星自居了);倘撞不上,全當我多遛了點路,而且撞不上的話彼時我的思想鬥爭會更激烈,那豈不是對我更大的考驗?要考驗就來最激烈的!往南!
實際情況是,我一次都沒撞上他們,但我一次都沒有就此罷休掉頭回家,每次當我遍尋宣武門大排檔而一無所獲時,我通常會找個台階坐下來抽根煙(是不是也在為思想找個台階呢?),在給他們打電話還是回家這二者之間做二選一的激烈思考,但半根煙之後我的腦子似乎就喪失了思考功能,它開始發暈發脹,理智此時基本失效了,一種強大的引力(可說是鬼使神差或著了魔)讓我狂囁幾口煙起身掉頭直奔身後小賣部的公用電話……這幫孫子還真夠朋友,那幾次他們都沒有讓那個著了魔的我失望,他們就在附近喝呢。於是我飛身前往,似乎還曾一溜小跑來著。
回想我那一個月的“閉關”,讓我常有進一步退兩步之感,我的 “閉關”成了我喝大酒的休止,是喝大酒的一種調節,這哪裏是什麼“進一步退兩步”,分明是墮落過程中的一種緩衝,以保障我那墮落更和諧更有節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