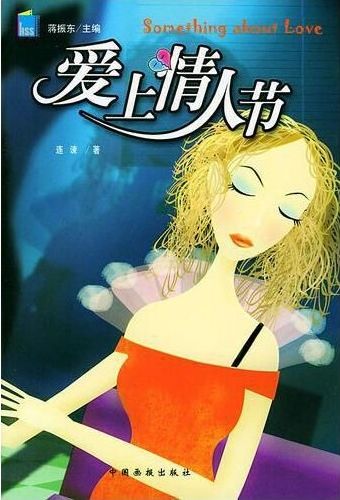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誘餌
文:連諫
一
陽光安好的中午,我叉起一塊牛扒說:靜蓉,你說,林子軒真的是每個夜晚都忙碌著和他的當事人打交道麼?
靜蓉反詰:林子軒是你老公又不是我老公,再者,有訴訟請求的人自然喜歡找個好律師了,他是十佳律師麼,哪有不忙的道理?
我笑,給牛扒加胡椒,內心的酸澀沒人看得見。
靜蓉看著我在牛扒上沒命地蘸黑胡椒,隱忍地笑:想辣死自己?
我倒想,就怕辣不死。把牛扒塞進嘴巴,辛辣的黑胡椒使我的眼裏充盈滿了眼淚。她塞給我一張餐巾紙:沒本事吃就不要逞能麼。
我不擦眼淚,流淚的感覺好極了,至少黑胡椒是我流淚的借口。穿過淚水,我望著靜蓉這個安好寧靜的女子,消瘦淡雅,從容不迫是她習慣的表情,她永遠不會看見,我這樣一個大咧咧的女子,內心張張開細密而堅硬的牙齒。
我狠狠的咀嚼著牛扒,內心冰冷地響著她的名字靜蓉靜蓉……
這個坐在我寫字桌對麵的從容不迫女子,與我親密無隙,而她含而不露的手指,悄悄擰疼了我的心。
二
一個電話就出賣了他們。
我的夜晚,大多是寂寞的,林子軒周旋在他的當事人之間,取證,做出庭答辯材料,當事人是他的上帝,稍有不周他們會投到其他律師手上,而我,用一紙婚約,他契約了我一生。
那晚的寂寥稠密,無比地想告訴林子軒,我不需要他如此拚命賺錢,隻要給我幾個完整而溫暖的夜晚。
他的電話占線,轉而打靜蓉的電話,亦是占線,隻好,我把自己丟給電視。
這是我第三遍看《激情燃燒歲月》,每一次看到結尾,我會淚流滿麵。
關上電視,繼續給林子軒打電話,沒人接,手機關掉了,給靜蓉打,電話沒人接,手機關掉了,除卻林子軒,靜蓉是我唯一的傾訴對象,為此,林子軒每每看見我和靜蓉褒電話粥時就會笑,說我們這兩個女人在寫字間整天對桌膩著還膩不夠,回家還要繼續謀殺電話費。
這是我最親近的兩個人,在這個夜,卻以同樣的方式拒絕我的聲音。
舉著話筒,很快,模糊的不祥就漂浮而來,女人是天生的直覺動物,這種感覺從未騙過我。
想象的細節揮之不去,擁擠而來,它們相互碰撞著,帶著瘋狂的殺傷力,一路刺殺進心裏。
幾乎是跳起來,上街攔車,到了靜蓉的樓下,窗口朦朧著曖昧的光線,我仰著頭一直望著,不停地告訴自己幻覺,這不過是個幻覺。
然而,林子軒下樓,高高的窗口,有靜蓉睡衣微裸的身體,她蓬鬆的長發飄揚在夜裏,宛如繩索,捆紮住我掙紮著不肯相信的心。
林子軒高高的身體隱沒在夜色裏,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
走走停停的路上,我多麼渴望這時的自己在夢裏,擰了胳膊,痛疼尖利,疼的不止身體。
看見在樓下徘徊的林子軒,我已是不動聲色。他迎著我走過來,眼裏有恐慌以及淺淺的譴責:彎彎,夜裏一個單身女子上街是危險的。
他不會知道,對於一個已婚女子,危險不在黑夜的街上,而在被她所愛者的心裏。
三
我流著眼淚麵目猙獰地消滅掉了那份牛扒,然後說:靜蓉,我要考驗一下林子軒對愛情的忠誠?靜蓉靜止了輕笑,淡定地盯著我:怎麼說?
我要送給他一個美麗的。
你還是得了吧,林子軒整天忙得像奔命的兔子,你給他下誘餌他都未必有時間去吞哩。
靜蓉一動不動地看著我,明明滅滅的惶惑淺淺閃爍一下,飛快隱沒,她總能以最快的速度隱藏起自己。
我盯著她,一直盯下去,一直盯到她眼裏浮出毛骨悚然的味道,然後,我得意非凡地笑,如同洞悉了隱藏在她心裏的所有秘密。
靜蓉的臉尷尬著,淺紅一下:彎彎,你究竟怎麼了?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我目不轉睛。
靜蓉惶惑著搖頭,然後緩緩說:該不會是讓我做誘餌吧?
算你聰明,除你求誰?林子軒經常誇你呢,說女人就應該像你,波瀾不驚,寧靜宜人。
靜蓉漲紅著臉,突兀地一甩手:你們夫妻間的事,不準拿我開涮。
她起身走人,她始終懂得該怎樣回避尷尬,她不想讓表情出賣掉自己。而我,已是漸然敞朗,她和林子軒千辛萬苦試圖藏匿起來的軟肋,終於被擊中。
我追在後麵喊:靜蓉,那我去找個年輕漂亮的美眉,好不好?
這是你自己的事,隨便你了。靜蓉修長的身影,疾步搖晃在前麵,弋地的長裙容裹在腿上,牽絆之下,徹底丟落了往日從容。
四
晚上,林子軒回來陪我吃晚飯,他極盡的溫和裏,我內心一片荒涼,他不在家吃晚飯已經很久了,這次例外,我知道,應該歸功於靜蓉。她定然是泄露了誘餌計劃,男人隻有在還在乎時才會欲蓋彌彰,向來細密的靜蓉疏忽掉了,這其實泄露了林子軒作為男人的真實,男人的婚外情像女人吃零食,偶爾吃一點零食是消遣,但要讓其為零食喪失掉主食沒太有可能,這是成熟男人的明智。
隻是,我要用這樣不動聲色的形式,讓靜蓉看清男人的本質,將她耽於林子軒的幻想淹沒徹底。
收拾桌子時,我若無其事說:子軒,知道麼,靜蓉28歲了?
林子軒手裏的杯子漸漸歪斜,水緩緩地落在沙發上,我扶了一下他的手:水灑出來了。
林子軒哦,淡定:她28歲怎麼了?
你接觸人多,有合適的幫她留意一下,不知道她是心有所屬還是怎麼了?這樣拖下去會坑了她自己的。
林子軒爽朗一笑:你真是,皇上不急急了太監。
我轉身去廚房,這點時間,他可以用來從容回旋表情。
五
一段日子,當寫字間裏人煙稀落時,我便抱著電話,哼哼哈哈地跟一個女孩子,談計劃,以及進展。
靜蓉要麼趴在桌上睡覺,她不停閃動的長長睫毛告訴我,她醒著,午睡是她掩飾自己的唯一方式,要麼,迷離著眼睛看窗外,眼神迷離在遠處的浩淼天空,無邊無際的哀怨蔓延在臉上,極少跟我說話。
而我,打完電話,就立馬拽起她,哪怕逼迫,亦要讓她聽我的計劃進展,從怎樣找到甘願做誘餌的女孩,然後是怎樣讓她假做當事人接觸林子軒,到怎樣一步步實施色誘然後是我給女孩子的報酬。
靜蓉張著茫然的眼神,看著我:有必要麼,憑林子軒做律師的職業敏銳,他可能上當麼?
我黯然:我比你更希望這個計劃落空。
我明白而作為情人,靜蓉是絕對排斥另一個情人的,作為林子軒的妻子我對於她不過是即定的事實,另外一個女子才是她真正的天敵。
我和靜蓉,有了漫長漫長的沉默,兩個女子,用表麵的稔熟相知遮掩了內心的撕殺。
而我和靜蓉是不同的,在這場戰爭中,她隻能隱藏在角落裏祈禱,而我卻是從容的指揮者。
靜蓉的從容漸漸失去,漸漸的,她已是按捺不住,沒事時,湊到我的身邊,玩笑著打探進行程度。
每次,我故做莫測狀:正在進行之中。
她眼裏,有渴望謎底的焦灼以及淺顯的慌張,我要的,就是她的慌張,慌張的患得患失會讓她對林子軒步步緊逼,而我要讓她在林子軒的步步後退中,一路綿延失落到絕望。
七
林子軒滯留在外得到夜晚,明顯少了。除了整理卷宗就是陪我看電視,或許,是我那個隱晦的提醒使他明白,靜蓉的愛情耽於岸上,亦是他不想承擔的責任。
夜晚的電話,大多是靜蓉的,我讓林子軒先接,我知道的,靜蓉想聽到的根本不是我的聲音。林子軒接電話,便打哈哈說:你們又要開始褒電話粥。然後衝我喊:彎彎,靜蓉找你。
我瞅他:你們先聊一會。
林子軒依舊玩笑著:靜蓉才不跟我聊呢。說著,放下話筒,逃一樣離開。
那邊的靜蓉就笑,飄蕩著掩藏不住的失落,懶洋洋跟我說話,她想聽的,不是我的聲音。
八
靜蓉越來越消瘦了,像一陣風就能吹跑的剪紙。
看我時有些恍惚,或者當我提到林子軒的名字,她眼裏便有東西快速墜落如沙礫。
每當這時,我便感覺到女人在捍衛愛情時的殘忍,即使如此,我依舊不能讓這場戰爭停止。
現在,林子軒在家時,電話響,即使他正在電話旁邊亦不接,高聲喊:彎彎,電話。
常常是我喂一聲,電話就斷掉了,不必問,是靜蓉的。
我舉著話筒對林子軒說:莫名其妙。林子軒的眼神躲躲閃閃。
在第N次接到莫名其妙的電話後,我握著話筒,莫名其妙還沒說出口,林子軒忽然做大悟狀:有個明天要用的卷宗忘記在辦公室了。拎起外套衝出門去。
我的心,冷冷地笑了一下,眼淚刷拉滑下來。
九
第二天,靜蓉生病請假。
昨晚,林子軒很晚回來,進房間後一聲不吭,與靜蓉的最後攤牌,想必不會太從容。
我的戲,該收尾了。
一周後,靜蓉上班的中午,我們在找了一家幽靜的餐廳吃飯,吃著吃著,靜蓉看著我,眼淚刷拉刷拉地落下來。
我知道為什麼卻不能說,而她亦不會告訴我,這時,堅韌了很久的疼,終於沒能隱忍,我哭了,這是我最親密的女子,另一個是我最愛的男人,他們隱秘的傷害尖銳而犀利。
靜蓉,林子軒吞掉了我的誘餌?
靜蓉的哭泣嘎然而止,張著迷蒙的眼睛望著我:怎麼可能?
真的,畢竟林子軒還是優秀的,誘餌怎麼會放棄這樣一條大魚?
靜蓉的哭泣,終於停止,她癡癡地望著我:你打算怎麼辦?
我茫然:不知道,我是愛林子軒的,我落在了自己挖的陷阱裏,我寧肯被陌生人而不是被自己信任的人傷,連憤怒都失去了底氣,是信任和愛情被傷的雙重絕望。
漫長漫長的沉默,我們望著別處,這是我一直想讓靜蓉聽到的話。
她無話可說無處安慰,因為,這個女孩亦是曾經的她自己相同。
十
靜蓉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了我們,遠嫁上海,據說那個男子辛苦追了她六年。
靜蓉走得決絕,拒絕任何人去送,好象要把這個傷心之城徹底遺忘。
她去上海的那個晚上,我對林子軒說:我有一個秘密。
他望著我,我緘默地笑而不語,默默地我鑽進他懷裏,這是林子軒和我心照不宣,因為我們需要維係一樁表麵上看不見裂縫的婚姻。
秘密是關於誘餌的故事,靜蓉永遠不會知道,我在寫字間撥打的電話號碼,是個空號,我隻是對著電話的交流聲自言自語而已。
我隻想用這樣的方式,讓靜蓉看見,她並不是這個男人婚姻之外的唯一,隻是男人可以順手撚來隨便就可丟棄的玩具而已,我知道林子軒曾經試圖向她解釋,而她不可能相信。
這一次,是我唯一的一次,利用了她對我的信任。
有一種朋友是用來享受人生的,還有一種朋友是用來利用的,是你們的貪婪把前者誘蛻到了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