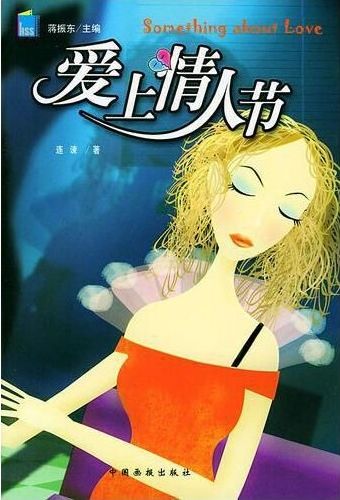閱讀更多精彩小說內容
一場蓄謀已久的外遇
文:連諫
一
早晨,仲天把一張俱樂部會員卡放在桌上說:有時間出去看看,不要總呆在家裏。
望著他匆匆出門的背影,好妤笑了一下,仲天做事,從來都有他自己明了卻不喜歡被追問的理由,就如當年,僅幾麵之緣,仿佛愛情還沒來得及被談起,他便勝券在握地站在好妤麵前說:嫁給我吧。婚後,好妤不隻一次問他:你憑什麼那般有把握我會嫁給你。
他隱忍地笑著反問:憑什麼你會不嫁給我?
好妤就隻剩了眨眼睛的份,是啊,那時,銳利的眼神中透露著霸道的仲天,曾蠢蠢欲動了多少女孩子的春心哦,自己又憑什麼推卻呢?
白駒過隙般的刹那,已是七年,女兒去寄宿幼兒園了,春天原野般生機勃勃的是仲天的事業,惟有做了閑婦的好妤停留在原地,生活的全部意義就是等仲天回家,燒一些精致的菜,看他吃的沉默,如同所有的話很久以前早已說完,連床第之事都是疏離,仿佛街坊間的相遇,需要彼此笑臉相迎的客氣。
這張會員卡像一隻緘默的釣鉤,垂釣起了好妤的諸多心思,她終於懂了,婚姻中的彼此客氣,是愛進入疲憊期的標誌,鏡子裏的女人,時光殘忍地抹掉了那個曾經眼波流轉、婀娜多姿的好妤,生育過後的身材,有些臃腫地失掉了比例。仲天有越來越多的借口不帶自己出入一些場合以及回家後的疏淡,或許就是因此。
所有的安寧的幸福感,被一張會員卡給遮蓋成為過去式,仲天用它暗示了好妤:她現在的樣子已不是他的喜歡,需要改變一下。
很久不知淚水滋味的好妤,哭了。
二
每當仲天的目光像掠過一件陳舊的擺設從自己身上掠過,卻不願多做片刻停留時,好妤的心就一揪一揪地疼,繁華似錦的青春拋給這個男人後她卻成了他眼中的雞肋。
夜裏,好妤聽著他均勻的呼吸,默默攬過他的腰,臉貼在他背上,無聲無息的流淚。
當仲天被眼淚弄醒後,好妤閉上眼睛假寐,溫熱的呼吸在她臉上停留片刻,然後是下床聲,開衣櫥聲,好妤半張開眼睛,黑暗中的仲天,正在換掉粘著眼淚的睡衣。
居然不問眼淚的來處,倒下,繼續睡覺。
隻在吃早餐時,他淡淡問:昨天夜裏做夢了吧?
他終於問了,好妤眼含希冀望著他,期望聽到他關切的聲音繼續下去,卻沒了。
白天,好妤的眼淚,差點淹死自己。
三
好妤試探著減肥時,才發現,脂肪的消滅要比囤積艱難得多,她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健身俱樂部或者約老同學以及朋友喝茶聊天,順便看能不能找到一份體麵的工作,其實,她完全可以去仲天的公司,隻是,好妤卻咬著牙,一定要自己動手活出一份精彩給仲天看,借以撿回正在丟落的自尊。
一天,在街上遇見了雪荔,在大學雪荔是曾是叱吒風雲,現在卻是混在一間沒啥起色的公司做事,進了路邊的茶樓,好妤叫了上好的台灣茶,雪荔看著好妤指上精致的戒指和質地良好的衣服,唏噓自己眼高命惡,好妤始終端著矜持的微笑,聽她對自己的羨慕,莫名地就想掀落掛在自己臉上的幸福粉飾,女人骨子裏天性的虛榮還是讓她忍住了。
末了,雪荔神秘兮兮地說:你還記的逸舟麼?
好妤的心,嘩地盛開了,臉上的矜持被生動稀哩嘩啦地瀉落了。
在大學時的逸舟,是個靦腆的男生,隻會暗暗喜歡卻不知霸道能更直接占據女孩子的芳心。轉瞬,成為他人婦的好妤,依舊記得畢業前的聯歡會上,瘦瘦的逸舟握著麥克唱〈同桌的你〉時始終望著自己的方向,一直一直盈出水汪汪的淚光。
他現在怎樣了?許久,好妤努力用恬淡的口氣問,內心卻奔跑起忽忽的風,因生活寂靜,很久沒有這樣的感覺了。
雪荔掃了她一眼:前一陣子,他還在電話裏問起你呢。
很想聽雪荔繼續講逸舟的生活工作以及婚姻,雪荔卻像評書先生樣在吊起她的胃口後三緘其口,而一貫的矜持讓好妤張不開詢問的口,畢竟,誰都知道逸舟當年是多麼隱忍地愛過她。
回家的路上,好妤就有了些怏怏。
四
忍過許多天後,還是用歡快的聲音給雪荔打了電話,東扯西扯一一扯起舊時的同學,話題終於扯到了逸舟身上,雪荔嗬嗬傻樂著問她:要不要逸舟的電話?
好妤忍了忍,說:算了吧,說不準他連我的名字都忘記了。
那端的笑聲就叵測地曖昧起來。
幸好是打電話,她看不見好妤臉上漸漸暈開的紅。
以後,如果逸舟再給我打電話,我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啊。
好妤外強中幹地說:別別……
雪荔放浪地笑一下,仿佛已隔著電話線把好妤給洞穿了。
放下電話,好妤的心情出奇地好,熨衣服時,哼起了多年前的老歌。
五
逸舟的電話,當天就打過來了,好妤握著電話,遲疑了半天,看著黃昏的夕照明晃晃地灑在腳上,才相信這是真的。
逸舟說:好妤,你好嗎?
好妤就有了流淚的欲望,搖搖晃晃地盈在眼裏,用歡快的聲音說:好哦,你呢?
逸舟卻淡淡地繞過了她的問,說一些遙遠的話題,具體說了什麼,好妤就記不住了,一直有暈眩的感覺在眼前晃著,最後彼此留了電話,手機以及電子信箱。
收線後,好妤抬頭,望著鏡子裏的自己,豐滿的臉上,紅霞飛舞,仲天跟她求婚時,她臉上就飛著這樣的顏色。
深夜裏,仲天回來,和往常一樣,喝一杯她泡好的茶水,洗澡,上床,好妤不知怎的,有了一些淡然的愧疚,竟像是自己做了對不起他的苟且之事,言行中多了小心的溫存。
這些細微的變化,仲天並無覺察,均勻的呼吸響起來,墜入沉沉的睡眠,好妤卻張滿眼的興奮,一直到天亮。
早晨,好容易捱到仲天離開家,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好妤打點電腦,果然,有逸舟的郵件。
幾年的時間逸舟已是學會了怎樣向女人表達自己的喜歡,深情款款告訴好妤,多年過去,一次次的戀愛無疾而終都因好妤的影子在作梗。
好妤的眼睛就濕了,在青春的尾巴正在悄悄淹沒,連丈夫都在倦殆時,還有什麼能夠比聽到某個男子對自己的心儀更能令無處可安的心萌生複雜的感動呢?
六
好妤的手機,若不是怕被仲天問了為什麼,怕是連睡覺時都要開著的,惟恐漏掉了逸舟的任何一個音符,早晨,仲天出門後,好妤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看逸舟的郵件以及回複郵件,那段日子,戀愛中女人特有的紅暈回到了好妤的臉上,眼睛裏閃著熠熠的光彩,偶爾仲天看她一眼,會輕輕一笑說:還是出去轉轉好吧?你臉上的氣色好多了。
好妤嘴裏說著是麼,偷偷掃一眼鏡子裏的自己,那時,她才知道,女人是天生的愛情動物,每個女人的心裏都藏著一隻九尾小狐狸,每當愛情來臨,它便張開了女人所有的嫵媚。
從淺淺的暗示到言語曖昧,逸舟說無論時光怎樣流走,好妤都是他唯一鐘情的女子,有什麼能比被某個男人始終如一地心儀著更能鼓舞女人的自信呢,當好妤幽幽說我變了老了時,逸舟說:可,你還是好妤啊。
是啊,除了相貌上略微變化,自己還是好妤啊,仲天怎會就倦殆了呢,憑空的,好妤滋生了遇人不淑的恨恨。
恨恨地,就想用這場外遇打爛死水般寂寥的生活,用有人七年如一日地牽掛著對自己的喜歡證明給仲天看,不是我不可愛了,而是你的心變了。
後來,逸舟說到了見麵,想著見麵可能帶來的種種後果,好妤矜持著不肯鬆口,和仲天,畢竟還沒惡劣到要徹底打碎原有生活的份上。
糾纏到最後,逸舟很是霸道地摔過一句話:再不答應,我馬上就去看你。
好妤慌了一下,忙忙說:我去。
隔著話筒,聽見逸舟幾乎要跳起來的聲音,好妤選擇去,有她的道理,畢竟逸舟依舊單身,在他的城市可以肆無忌憚,不必有來自己所在城市的諸多顧忌。
七
隨著行期漸漸逼近,好妤越來越是恍惚,對於仲天,她該編造一個什麼樣的理由去從無瓜葛的蘇州?
好妤心煩意亂地翻報紙,一則旅行社的廣告,在她眼前刷拉撕開了一道明亮的縫隙。
夜裏,仲天上床時,好妤閉了燈,在黑暗中說:我想去一趟蘇州。
本以為仲天會問去蘇州做什麼,好妤便順著解釋一番,仲天卻沒有,好妤隻好自言自語般說:旅行社組織了一個購物旅行團,我想跟團去買些我們這裏少見的東西。
仲天說了一聲:跟團去玩兩天行了,別買東西拎回來了,太累。
好妤虛虛地反駁,不買東西有什麼意思?
看著很快進入夢鄉的仲天,即將到來的背叛讓好妤的心越來越忐忑,隻是她已是這個男人不屑於傾注熱情的舊愛,令她像恐慌在季節末梢的花朵,逸舟充滿讚美的愛慕,是多麼值得珍惜的誘惑。
八
遠遠的,好妤看見逸舟抱著大束的玫瑰,略微有些緊張地東張西望,對近在咫尺處徘徊著的好妤,竟視而不見。
好妤忍著笑看他,想看他究竟要把燈下黑演繹到什麼時候。
時間滴答而過,好妤終還是忍不住了,張著璀璨的笑,衝他嗨了一聲。
逸舟把玫瑰放低,一直一直看著她,喃喃說:好妤,真的是你麼?
好妤本以為他會連同玫瑰一起把自己擁抱在懷裏,逸舟除了有些拘謹地笑著,卻沒有任何親昵的舉止,種種設計過千萬次的擁抱以及流淚場景,統統沒有發生。
若即若離的走在街上,仿佛又回到了大學時代,那些熱烈的郵件以及迫切的電話,仿佛皆不是眼前這個男人所為。
好妤試探著把手指塞進逸舟的掌心裏,他的手輕輕驚悸了一下,小心地握了,路過一家黃泥螺門麵時,逸舟突兀說:蘇州的黃泥螺味道是一絕的,你嘗一嘗怎麼樣?
不容好妤說什麼,便飛快地抽了手奔過去。
好妤握著空蕩蕩的空氣,失落漸然彌漫上來,一盞黃泥螺,遠遠比不上在他掌心裏的溫暖,失落一層層地就疊過來。
後來,在菜館吃飯,逸舟的眼神始終有一些躲閃,好妤用唏噓打破有些尷尬的氣氛:過得真快啊,刹那間就七年了。
逸舟搓搓手,笑:是啊。
整個過程是漫長漫長的沉默,很多話,總在啟口之際又閃回去。
兩個人一直坐著,說大學裏的一些事,說到開心時,逸舟爽朗地笑,整個的人就生動起來,好妤看得心酸,時光對於男人太寬容了,七年除了讓逸舟看起來更具有男性魅力之外,其他幾乎是了無痕跡,而對於自己,就苛刻了些。
菜館裏響起了服務生收拾桌子的聲音,整個餐廳隻剩了他們兩個,好妤終是沒忍住,用浩淼的聲音叫了逸舟,用萬般的柔情籠罩住他的眼神,任是個男人,應該不會不懂這樣的暗示吧?
果然,逸舟抬起手腕說:你看,我們老同學多年不見,一見就忘記了時間。
好妤的心沉了一下,卻沒說什麼,拎起包起身,默默地走在街上,比失落更重的憤恨疊壓過來,像饑餓的貓奔著吊在線上魚兒上躥下跳,好容易捕到了,卻發現是一條惡作劇的木魚。
好妤有萬分的把握,如果自己還保持了七年前的青春瀲灩,逸舟的態度決不至如此,或許,在街上相見的那一刻,逸舟才明白是記憶讓他犯了一個致命的低級錯誤,現在,他正彷徨著不知該怎樣彌補。
眼淚慢慢滑下來,好妤終於痛挫了自尊去問:逸舟,你總喜歡跟女人開曖昧的玩笑麼?
逸舟喃喃著,欲言又止始終是他的表情。
好妤冷笑了一下:不必怕傷了我的自尊,是不是我和你記憶中的好妤相差太遠了?
逸舟有些瞠目結舌:好妤,聽雪荔說你的婚姻還是不錯的,如果你悔了,會怨我的……
好妤用鼻子冷笑一下:你給我寫熱情洋溢的郵件,煲火熱的電話粥時怎麼就沒想過我會悔的會怨你的?因為,那時你想著的是記憶中的好妤,婀娜,青春……而是現在這個又胖又被歲月摧殘了的好妤,讓你感覺已不值得為她做什麼了吧?
逸舟望著她:好妤,你怎麼變成這樣子?我無話可說了。
怕是我說中了事實,你找不到辯解的理由了吧?
說完,好妤招手攔了一輛出租車,在陌生城市的氣息裏,眼淚嘩啦嘩啦地落下來,逸舟愛的,是記憶中瀲灩如花的好妤,而現在,好妤千裏迢迢跑來,呈現給他的,卻是花朵的頹敗……
這場蓄謀已久的外遇,如一塊尖銳的石頭,冷丁紮醒了好妤,這世上,原本就不存在永恒的童話,而自己,為什麼一定一定要一相情願地固守在這些飄渺的希冀上呢?
踏著淩晨的微光,好妤回旅行團訂好的房間,趴在窗子上,一直看到滿街熙熙攘攘起來,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熱情的光芒奔向自己的方向,那些朝氣蓬勃的臉,令好妤想到自己,也曾有過美好的理想,它們歡快地奔跑在青春長路上……
好妤揩了揩頰上的淚光,給仲天撥了一個電話,遲疑問:親愛,幫我留意一份工作好麼?
仲天頓了一下,爾後,聲音裏有了逐漸上揚的喜悅:怎麼忽然想到出去工作呢?
好妤羞澀道:我要抓回正在逃跑的理想……
收線後,陽光安好裏,好妤拍了拍映在鏡子裏的臉:嗬,你神采飛揚了。